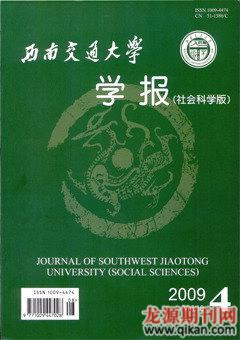光影记忆:新中国女性电影60年
高 力
关键词:女性电影;男性中心;遮蔽;张扬
摘要:从权主义电影批评角度审视,新中国的电影在女性伸展与解放的体貌下,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潜抑力与整合力。在这两种合力的遮蔽下,女权的内蕴、女性的意识和独立的女性品格却缺损到几乎无可辨认的境地。新时期主流电影通过女性表象的复位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拨乱反正”的过程,然而,这一时期电影叙事中的女性、母亲、地母形象仍是沉重的、超负荷的或多元决定的历史存在。新时期的电影语言仍然是男性的传播方式,在男性的、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遮蔽和扭曲下,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依然是缺损的。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4-001-04
伴随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而诞生的新中国电影在成功消解了好莱坞电影经典叙事中特定的男权意识形态话语后,女性形象在不再作为男性欲望客体而存在的同时,她们也同样不曾作为独立于男性的性别群体而存在,却呈现出非性别化的状态。在新中国电影政治象征化的经典叙事中,引人注目的是女性的“新人”形象,这就是世纪变革中翻身、获救的女性和由这些女性成长而来的女战士、女英雄。新中国最早的两部同摄于1950年的影片《白毛女》(水华、王滨导演)、《中华女儿》(凌子风导演)成就了两种女性类型形象,并成为中国当代电影中关于女性叙事(1949—1979年)的基本叙事原型。在旧社会她们注定历经苦难,被侮辱、被损害,直到获得一个男性共产党人的救赎,摩有了一个解放的妇女、一个新女性的自由与权力。然而,获得是为了再度奉献,她将成为一个巨大群体中非性化的一员,一个消融在群体中的个体而成长、凸现为一个男性化的“女”英雄(《红色娘子军》,谢晋导演,1959年;《青春之歌》,崔嵬导演,1959年)。这一革命的经典叙事模式,在其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发展为一个不知性别为何物的女性的政治与社会象征。在女性伸展与解放的体貌下,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潜抑力与整合力,在这两种合力的遮蔽下,女权的内蕴、女性的意识和独立的女性品格却缺损到几乎无可辨认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新中国电影中,一个始终被沿用的经典女性原型是母亲、地母形象。诚如戴锦华所言:母亲形象“作为‘人民的指称,她是历史的原动力与拯救力,她是安泰、共产党人的大地母亲(《母亲》,凌子风导演,1956年;《革命家庭》,水华导演,1964年)。她是传统美德——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呈现者……正是母亲形象成了一座浮桥,连接起当代中国两个历史时期(1949~1976年,1976至今)关于女性的电影叙事。
新时期主流电影通过女性表象的复位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拨乱反正”的过程。然而在电影叙事中的女性、母亲、地母形象仍是沉重的、超负荷的或多元决定的历史存在,她们分别或同时承担着历史控诉、历史清算、历史的拯救与想象性的抚慰、不堪重负的忏悔、历史的蒙难者与祭品等多重编码。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电影塑造的众多女性,如谢晋电影中的系列女性:冯晴岚、宋薇(《天云山传奇》,1979年)、李秀芝(《牧马人》,1981年)、胡玉音(《芙蓉镇》,1987年)等就是这多重编码的承载体和指认物。
在第四代导演最初的影像表征中,女性形象成了历史的剥夺与主人公内在匮乏的指称,成了那些断念式的爱情故事中一去不返的美丽幻影(黄建中《如意》,1982年;藤文骥《苏醒》,1981年)。在那些凄楚的、柏拉图或乌托邦的爱情叙事中的女性甚至不曾被指认(杨延晋《小街》,1980年)。在第四代导演共有的转型时代的“文明与愚昧”的主题中,女人成了愚昧的牺牲、文明的献祭、历史的沉井与拯救,成了第四代文化死结的背负者。《逆光》、《都市里的村庄》、《海滩》、《乡情》、《乡音》、《老井》、《野山》等莫不如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四代导演将欲望与压抑的故事、将典型的男性文化困境移置于女性形象中,如谢飞的《湘女萧萧》,黄建中的《良家妇女》、《贞女》……女人又一次成为男人的假面。
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是以拒绝叙事、拒绝女性形象而出现的,因而被人称为“子一代的艺术。”然而,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末解体的同时,仍然必须借助女性表象来重新加入历史、文化与叙事中。于是在第五代导演的部分作品中,女性在男人欲望的视域中再度浮现,成为好莱坞经典叙事镜语中“男人欲望的客体”。男人之于女人的欲望视域首先呈现在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1987年)之中,女人的进入,不仅为第五代导演提供了悬置已久的成人祭礼,解脱了其“子一代”无名、无语的状态,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叙事复归的契机。继而在周晓文的《疯狂的代价》(1988年)中,女人出现在男人窥视、渴欲而又恐惧的视域之中。《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男主角的视觉缺席、多重四合院、古典建筑博物馆式的空间构成,成群妻妾间的争风吃醋作为中国式的“内耗”与权力斗争的象喻,负荷着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反思内涵;然而在女性主义的视域中,影片中的女性却依然是缺损的“他者”,或为“男人欲望的客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中出现了众多的女导演(诸如黄蜀芹、张暖忻、李少红、胡玫、宁瀛、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刘苗苗等),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她们的作品中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却是凤毛麟角。她们的影片常以一个不“规范”的、反秩序的女性形象、女性故事开始,以一个经典的、规范的情境为结局;常在逃离一种男性话语、男权规范的同时,采用了另一套男性话语,因而失落于另一规范。在这类影片中,王君正在《山林中头一个女人》的前半部讲述了一个叫小白鞋的、美丽、病弱的妓女的故事,这是一个传统的、又熟悉的关于女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而在后半部分,则讲述了另一个女人、一个名叫大力神的妓女的故事。她身强力壮、心直口快、刚烈果敢,敢与男人对抗。但她的故事迅速转入了一个经典的、女性慷慨的自我牺牲的格局之中,成为了“山林中头一个女人”。这无疑是又一个熟悉的形象:一位大地母亲。她的全部意义与价值在于贡奉、牺牲,以成全男人的生命与价值。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取材于一位女性报告文学作者向娅的纪实作品《女十人谈》,然而在这部女人的影片中女性成了具有某种色情观看价值的银幕表象。张暖忻在《沙鸥》中,将第四代导演的电影的共同主题:关于历史的剥夺、关于丧失、关于“一切都离我而去”演绎为一个“我爱荣誉甚于生命”的女人的故事。而在这部影片中,女主人公沙鸥甚至没有得到机会来实现主流文化中女性的二项对立或者二难处境,便被历史和灾难永远地夺去了一切。在一个废墟般的生命中便无所谓“女人”。而她的《青春祭》(1986年)则通过影片的镜语设置,剖析女性的分裂心理,渗透着女性的主体意识。然而其女性意识的表现
还只是不自觉的初萌阶段。
在当代中国影坛,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女性电影”的唯一作品是女导演黄蜀芹的作品《人·鬼·情》(1987年)。这并不是一部“激进的、毁灭快感的影片。它只是借助一个特殊的女艺术家——扮演男性的京剧女演员的生活,象喻式地揭示、呈现了一个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女主人公秋芸童年不幸失母、青年爱情受阻、中年婚姻痛苦的命运发展史,生动细腻地展示了一个女人的心态、情感与呐喊,是一部女性生活寓言。片中坦率地对其历史命运提出质询:已经功成名就的秋芸今天的一切是有幸抑或是不幸?作为女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就从深层次反思了当代女性谋求发展所面临的文化话题。女性面临的困境正像克里斯蒂娃所说,“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苍穹下创造出另一种语言系统来”。于是就存在着所谓“花木兰式境遇”,女性如秋芸者只能以改变性别而获取成功。批评家认为这是“现代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喻,一个拒绝并试图逃脱女性而终未获救”的形象。
在影片中,女艺术家秋芸的生活被呈现为一个绝望地试图逃离女性命运与女性悲剧的挣扎;然而她的每一次逃离都只能是对这一性别宿命的遭遇或直面。她为了逃脱女性命运的选择:“演男的”,这不仅成为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指称与象喻,而且更为微妙地揭示并颠覆着经典的男权文化与男性话语。但由女人出演的男人,除加深了女性扮演者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性别指认的困惑之外,还由于角色与其扮演者不能同在而构成了女性的欲望、男性的对象、女性的被拯救者、男性的拯救者的轮番缺席;一个经典的文化情境便因之永远缺损,成为女人的一个永远难圆满之梦。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了影片片头,秋芸曾在镜子面前仔细地审度自己,直到把自己完全变成为男性角色。镜子在此出色地发挥了反向作用。秋芸在镜中完成蜕变过程,观众从镜外端详她的行为,当她与男性角色完全融为一体,镜子便把她彻底吞没,暗示她与角色彼此的置换。在影片结尾,男女参半的意象再次出现,它和片头的影像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揭示性的结语。
进入20世纪90年代,第五代女导演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大胆创新,用女性独有的语言去表现作为现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感受。彭小莲有表现女中学生追求个性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我和我的同学们》,还有反映改革后农村妇女觉醒与抗争的《女人的故事》;李少红有反映妓女在新中国改造过程中复杂个性的《红粉》……这些影片的艺术追求不同、审美意趣迥异,但在反思女性价值,揭示女性意识上却异曲同工。刘苗苗的《马蹄声碎》真实地表述出女红军作为女人、作为特定环境中的女人的性别弱点和七情六欲。在其他一些表现战争与女人的影片中,我们也窥视到了这种女性意识的强化。对比一下相隔30多年的两部同是表现“八女投江”题材的影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嬗变。20世纪50年代的《中华儿女》中的八个女抗联战士,个个都是女中丈夫、巾帼英雄。而80年代的《八女投江》写的却是“战争中的女性”,她们的爱情、婚姻、家庭在战火中的煎熬和丧夫别子的痛苦,就连最男性化的女战士也会在牺牲前在头发上别一朵野花。
进入21世纪,在近几年的中国银幕上我们看到了众多的女性镜像。在李少红《恋爱中的宝贝》中,从周迅扮演的行为乖张的“宝贝”身上,我们看到了对女性主义的另类阐释:对爱情、希望的梦想和执著,对周遭世界的无法把握和排斥以及对自己无根状态的恐惧,这一切都使“宝贝”面目模糊、行为乖张。“她”无法与世界融合,只能用结束生命的方式以求爱的永恒。在霍建起的《暖》中,我们看到那个瘸了一条腿却仍然美丽的女人在不停的挣扎、反抗,一次次逃遁世俗强加给女性的命运之后,身体和头脑终于完全陷入世俗的泥沼。侯咏的《茉莉花开》展示三个女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表现了女性从单纯走向幻灭,再从幻灭中重生并走向成熟的过程。在贾樟柯的《世界》中,赵涛扮演的舞蹈演员辗转在华丽光彩的虚幻世界和无奈困苦的现实世界之间。人生的无奈,爱情的无奈都表现出一个边缘女性的现实困境。顾长卫《孔雀》中张静初扮演的“姐姐”身上表现出女性意识的某种张扬:姐姐脱裤子是为了取回自己的降落伞,降落伞对她来说,成为了一个梦想的残余,精神的慰藉。而《立春》却展示出女性知识分子对自我意识的坚持、希冀和对命运的忍受。孙周的《周渔的火车》中的周渔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一个性的亢奋者,她与两个男人的关系,最终都是以性的方式为终极巅峰的。在这部电影中女性再一次成为男性的欲望的载体和投射的对象。
在娄烨的《苏州河》中,我们却看到了女性意识的后倾。电影强调的是男人寻找的执著和女人对这种执著的感动,在这个感动中,一切欺骗和摧残都得以化解,明明是未成年少女牡丹是一场诈骗中的受害者,但在电影里却被表现为主动的性诱惑者。女性在这个男主角寻找爱的历程中,分别扮演诱惑者、启蒙者、被认同和被寻找的目标物等角色,女性再一次成为男性的附庸和“欲望的客体”,完成了向男权社会的又一次皈依。这种皈依还体现在徐静蕾导演的《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尽管徐静蕾这两部电影都是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的独白来推进情节的发展,但塑造的并不是真实的、完整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形象仍然是缺损的。《我和爸爸》中的小鱼和《一个陌生女人来信》中的陌生女人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是不具备独立人格的“他者”。男性导演王全安拍摄的三部电影都以女性为叙事主体。雅男(《月蚀》)和毛女(《惊蛰》)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她们都是在男性的“保护”下才得以有了现在的生活,可以说她们是作为“他者”存在的。而关二妹(《月蚀》)因为不喜欢父亲为自己挑选的结婚对象而逃到了城市,实现了经济的独立和恋爱的自由。佳娘(《惊蛰》)则是通过对梦想的追求和对作为男性欲望客体的反抗来展现自我个性的。她们是以女性意识的觉醒者的形象呈现的。而从图雅(《图雅的婚事》)性格的坚忍和女性柔情以及对男性的“救赎者”的角色中,我们却窥见到一种早已熟悉的银幕形象——大地母亲。
事实上21世纪初的女性影像离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依旧相去甚远。迄今为止,黄蜀芹的《人·鬼·情》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电影,它以套层叙事的方式对当代女性发展所面临的文化难题进行了历史的透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它突破了以往一般女性电影所建构的表叙框架。《人·鬼·情》的出现使人们对女性电影的热情显得不那么唐突,它不仅印证了中国女性意识的现实存在,而且还预示了它不同凡响的未来发展。
参考文献:
[1]戴锦华,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J/OL],(2004-06-05)[2009-05-06],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3/1。
[2]劳拉·莫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J],周传基,译,世界电影,1996,(5):25。
[3]戴锦华,电影批评手册[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21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