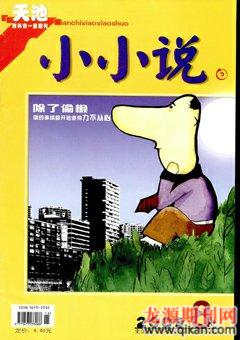绝版的青春往事
郑 啸
毕业那年,与寝室的三个兄弟一块儿租房住。那时候就业形式已不乐观,离校时我们都还没找到工作。
一间房,挤了两张床,中间只余半米过道。两张一米宽的小床,每一张都要挤两条汉子。睡觉需要卧如弓,里面那个梦中翻个身,另一个就得滚到地上去。刷牙洗脸在楼道里的公用水池,做饭用的煤炉便放在门口。吃饭基本上都是下面条。毕业之后的几个月我们就这样以部落同居的形式凑合。
找工作的过程是焦虑而毫无诗意的。前半个月还乐观,面对人才市场眼花缭乱的岗位,挑挑拣拣,信心百倍地投简历,用手蘸凉水梳理头发迎接面试。城市不大,很快,好点的企业就被过滤一遍。我们以为工作就是一条鱼,在等待着把它捞到网里去。但终于没有一家公司与我们眉目传情。心冷了,本来就空的钱包更是即将山穷水尽。
这时,瘦瘦小小的老六找到了工作。每日早早起床,晚上很晚才回来。谁也不知道小六干的是什么工作,他没告诉我们,但我们能看得出他的疲惫,肤色被晒得像黑炭,躺在床上就打呼噜,怎么推都不醒。半个月后他领了600元薪水,我们很是羡慕。老三、老五加上我纷纷要求他帮我们引荐一下。他只是说,这活你们不会干。我们仨很是气愤,但小六虽然在这点上自私,他挣的钱却是大家一起花的。这状况一直持续到秋深风冷时。小六一个人干活,养活了我们四个人。他的勤劳让我这会想起来都有点汗颜。他工作回来,放下买回来的面条、鸡蛋,把锅放到火上,抓起地上扔的衣服便洗。
老五是最早颓废下来的人,父母时而接济一点儿,他整天窝在房间里租了成摞的武侠书看,沉迷在江湖恩怨的世界里。他最热衷的事,就是晚上吃了饭拉着大家打牌。他悄悄告诉过我:工作的事,家里人正在跑,有了眉目他就回去。
老三则白天跟我一块儿跑人才市场,晚上就去附近的广场跳交谊舞。他的舞技很出众,太空步、霹雳舞都跳得像模像样。一个晚上,老三整夜未归,次日清晨,他告诉我们他艳遇了。那女人离异,有房子,她迷恋他的青春气息。于是,老三就成了最先搬出去住的人,从此我睡的床就空了一半。老三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兄弟们,我这算不算卖身求荣啊。
以后的夜里,老五哗啦哗啦玩着扑克,很黯然地嘟哝:真没意思,连打牌的人都凑不齐了。老六在过道里下面条,黑暗随着淡淡的雾气飘落下来。天气越发冷了,我拿着电话本翻看白天投过的岗位记录,心里空落落的。
老六失业时,我和老五才知道,他干的活儿是送水工,为了多挣点钱,他往往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老六说,不多挣点,兄弟们连饭都吃不上了。他挣下的血汗钱大多变成了面条,有时候还有点小酒,都装进了我们的肚子里。
那年的雪来得很早,刚进了十一月,风就刀片一样割耳朵,晶莹的雪粒飘荡而下,薄薄的被子无法御寒。我和老六最先送走了喜滋滋的老五,他父亲打来电话,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帮他进了县里的电业局。看着老五踌躇满志地坐在长途车上朝我们挥手,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落下来。我和老六都属于没有退路的人,退一步就是脸朝黄土。
后来,老六找了家销售公司做业务,并被外派到别的城市开拓市场,而我则有幸进了一家小公司的策划部。将他送上火车的那天,雪仍然在下。老六拉开了车窗喊道:哥,你要保重呀。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悲凉。
回到曾人声鼎沸的小屋,我呆呆坐了很久,却在枕头下发现一叠零零碎碎的钱,是老六留给我的。
那个晚上,我冒着雪走到街上,找到一个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我家是没有电话的,打到邻居家,邻居再去叫我妈。妈妈过来听电话时,我的牙齿已经在激烈战斗了。我强忍着心底的辛酸对母亲说:妈,我找到工作了,别操心我的事了。泪水却止不住地流下来。
如今,小六已经在江城买房定居,老三的孩子已经会叫我叔叔了,老五已经在单位成为骨干,而我,也已在这个城市衣食无忧。
时间的尘埃掩埋了许多过往,可我还是会想起那时候的情景,整个人都被一种叫友谊的光芒炙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