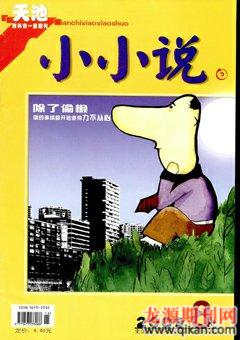象牙色毛衣
裘山山
他是丈夫的老朋友。
她和他相识也有些年头了。
谈恋爱时,他是他们的“保镖”、“信使”乃至闹矛盾以后的“说客”;结婚时,他为他们布置新房——他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连出门旅行,都是他接送。
她很感激他,总是对丈夫说,在众多的朋友里,他是最热心帮助他们,并不求回报的一个。丈夫亦点头称是。
然而,这么一个活活泼泼、乐于助人的人,自己的感情生活却十分不幸。他谈了一次又一次恋爱,都以失败告终。偏偏他又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所以每次败下来,都要沮丧许久。
他没有姐妹,母亲也早已故去,这使他的生活在缺少女性的温情和抚爱下,显露出一种十分明显的窘迫。
在又一次和一个女朋友闹僵后,他来到她家。她并不劝慰他——那没用,她只是静静地织着毛衣,听他有一句无一句地讲着他和那个女孩子的事。他忽然苦笑着举起双肘说,你瞧,我毛衣破成这样了,她也不肯替我织。你知道我这个人,感情上总希望别人更多的给予。我孤独得太久了。
她心中生出无限怜悯,但依旧什么也没说。后来他走了,胳膊肘毛衣磨破的地方露出红运动衣的颜色,十分刺眼。
晚上,她对丈夫说起这些,丈夫也叹气。于是她说:我给他织一件毛衣吧?
丈夫沉吟半晌,说,以后吧。
她便不再提。
终于有一天,他结婚了。
那是很神速的。他几个月没来,她还以为他外出了。然而突然的一天,他便带了一个女孩子来,进门就说:这是我爱人。
她由衷地为他高兴。丈夫也乐呵呵地跟他开心。她赶紧上街购回一块非常漂亮的挂毯送给他,补作结婚礼物。
新房布置得很漂亮,一看就出自他的设计,那块挂毯挂在客厅里,很有点艺术家的味道。
然而,挂毯还没落上灰,他们又离异了。
这一回他彻底绝望了。他对她和丈夫说:看来我只能过单身生活了。他没有说那女孩子一个不是。
他依旧穿着那件旧毛衣,只是两只破袖子被拆掉后补织了一段不伦不类的颜色。
这是她留给我的惟一纪念。他苦笑着走了。
她决意要为他织一件毛衣。
丈夫说:这家伙对色彩挑剔得很,你得先问问。
她就去问他。他呆呆地怔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给我织毛衣?
怎么啦?她尽量把口气放平淡:不相信我的手艺?
不不不。他笑了,我哪能挑剔你的手艺。我只是……其实也没什么。
那就告诉我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他认认真真地想了很久,说,象牙色。
她想不出象牙色是什么样的颜色,但还是点点头。打这以后,她见商店就进去问,但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
这样一耽搁,三个月过去了。
后来她终于托人从上海买到了,那是一种似淡黄又似浅灰的颜色,透出几丝温馨。
她设计了几种样式,去问丈夫。丈夫说:我怎么都行。
又不是给你织。她嗔怪道,但心却莫名地忽悠了一下: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丈夫噢噢地应着,随便指了个花样。
不知怎的,她把已经绕成团的线又塞进了箱子,重新买线给丈夫织了一件,尽管丈夫早已有了好几件。
这样一耽搁,三个月又过去了。
到了秋天。她觉得他已经有很久没有来了。她想织好毛衣后再和丈夫一起去看他。
起了头,但总是织织停停,进展很慢。并且丈夫晚上在家时,她会自然而然将“象牙色”放下,拿起别的毛活儿。那时她已有了身孕。
织到一半时,她生产了。
孩子一掉下地,便有千万件事情从地下冒出来。她和丈夫都忙得不可开交,丈夫胡子拉碴,头发如乱草,让她看着心疼。
光阴似箭似弹指似流水。
孩子已经蹒跚学步了。有一次,那只小手不知从哪里扯出一团线来,越拉越长,最后带出了那件织了一半的象牙色毛衣。
她顿生歉疚。同时也想起,他已经有很久没来过了。她赶紧拿出来织,又赶紧向朋友打听他的近况。朋友说,他早于几个月前申请调到甘肃敦煌去了。
她惊愕,他居然不辞而别。问丈夫,丈夫说,他曾到他单位上来告别过。
为什么不跟她说?
这家伙,是不是误会了?你给他织毛衣?丈夫半开玩笑地说。
于是她和丈夫很久不再谈到他。
突然有一天,他死了。丈夫告诉她时,眼睛红红的,连续抽了两包烟。
他夜里行路时,掉进了荒原上的一口枯井里。
在他留下的遗物中,有一封写给她和丈夫的信。其中有一段是专门写给她的——
我知道你一定早已将毛衣织好,可我不愿来拿,每次见到你,我最怕的就是你告诉我:毛衣织好了,拿去吧!为了这个,我索性不再来;也为了这个,我才不辞而别。自从你对我说,你要为我织一件毛衣,我就一直感到一种温情萦绕在心头。我总是想,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人在为我织毛衣。我不愿让这温暖的感觉中断。我最需要的不是毛衣……
她和丈夫赶去参加他的葬礼,带着那件不再能温暖他的象牙色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