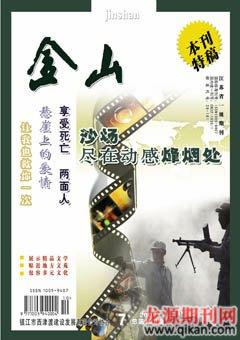影视作品创作中的“形”与“失”
戚伟俊
今天的艺术已经步入“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天人合一才是我们追求的真谛。
一部影视剧作品着重所要表现的一切均是“人”。
人们随着岁月的更替,观念和审美习惯也随之发生由形到神的悟变。文艺作品所要描写的人物必然会从它的面容、发式、形体、动作及服饰形态的“设计”中塑造出来。
而所有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均是在各位编导们的主观意识引导下进行的,往往都带有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即为编导们的创作风格和故事的叙事结构,但这一切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如果形式大于内容,装饰大于“内核”,就会给人们以“脱壳”和“空洞”的感觉。看了部分公示的新《红楼梦》剧照,在众多方面还是具有可取,可借鉴的探索经验,但该剧的人物造型方面还是给人产生了较大的“距离感”和“陌生感”,给人一种人与景,头与面相脱节的印象,它较大程度地突破了人们心里上的造型底线。
如果该剧是一部舞台剧,由于观众的视觉“主观蒙太奇”的作用,可以弱化观众的视觉距离。而影视片的镜头恰恰给观众视觉的是“客观蒙太奇”,观众是无法选择视角的。只能被强制在导演和摄影所给的画面中,影视片的造型设计语言要涵而不露。而不是在中国的或世界其他民族的艺术的元素中拼贴出所谓“新创意”。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自然的流露和表现。我想《红》剧的造型上脱节正是人们不予认可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导演受日本导演黑泽民的一些作品及流派的影响,都在努力尝试着所谓“现代主义”风格的创作。如张艺谋的《英雄》、《满城尽戴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和冯小刚的《夜宴》等。以上几部大片的故事都是虚构或者移植其他名著的框架而来的。强调了视觉性,弱化了文学性,突出了现时的商业性。通过较强烈的主观装饰手法、唯美的视觉效果来表现创作者的精神意识,当然这样的探索也是未尝不可,但是《红》剧恰恰有所不同,它不是诗歌和散文的叙事结构,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剧中的人物是鲜活的,生动的,生活的和可信的。他们的情,义,反叛,命运深深地感动着所有读者和观众。而我们的影视片中所有的景、衣、饰,道具等元素均是对剧中人物的陪衬和烘托,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如果造型设计上越过了那个宝贵的“度”,观众就会有一种压抑感,隔膜感和生涩感,从而失去作品和的亲和力及可信度。这恰恰就失去了一部作品最本质的“内核”——“神”。
87版《红楼梦》至所以被人们肯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诸多的“设计”藏起来。尽可能地突出人物,而不是用过多的外加上的造型包装同剧中人物“抢戏”。
所有高水平的表演都是没有任何“表演”痕迹的表演。所有高水准的设计都是没有任何“设计”痕迹的设计。
主观意识和作者个性最强的艺术表现形式是绘画,音乐,诗歌和摄影等。但影视创作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导演最重要的职能是把握好一部影片的总体艺术风格和拍摄走向,整合好导、摄、美、服、化、道,演员和制作班子的所有资源。就如同琴键盘上的十个手指要调整好各个旋律,节奏的轻与重、弱与强和长与短,控制好各个艺术专业的环节,使它归纳到导演所要的风格上等。就如同演员的身、台、形、表也要高度的统一。这才能体现一个个剧中的“鲜活”人物,而不是演员“无戏”的自我。所以乐队的指挥不能让任何一个“音符”、“音节”冲出整部乐章,产生喧宾夺主,极不和谐的高音。
《大明宫词》、《桔子红了》等几部作品,笔者认为在基本造型上应该是成功的,是能够溶入剧情的一个“统一体”,是在适度中体现。而现在的新《红》剧的设计中过多强调了“符号”语言和造型师的艺术“玩味”。发套给人有头盔面具之感,服饰给人有铠甲之身。使观众产生较强烈的不认同,从而使它冲谈了剧中故事和演员的戏份。
今天的艺术已经步入“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天人合一才是我们追求的真谛。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多多看到那么一点非常非常可贵的“平实”、“真诚”和“朴素”。少一点“浮夸”、“摆谱”和“娇柔”。用《红楼梦》中的禅境去抚慰人们一颗安而不静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