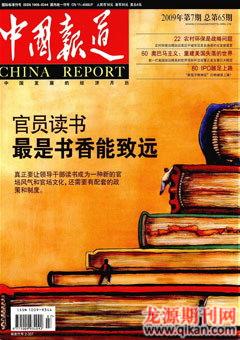“启蒙”背后的历史
季剑青
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早已成为一个经典的阐释范式。然而,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启蒙”到底从何而来?当我们不假思索地把五四运动称为一场“启蒙”运动时,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这一问题似乎仍未得到充分的澄清。
余英时先生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认为,五四运动被界定为一场“启蒙运动”,归因于1936年前后共产党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此前,“五四”新文化人更倾向于将五四运动比作“文艺复兴”。余先生对“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作出某种政治性的区分,指出前者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激进化的阐释,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规划,后者则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的构想,将五四运动的目标设定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余先生的看法自有道理,但对“启蒙”的理解似乎也不无简单化和政治化的嫌疑。他并未充分考察“启蒙”一词在现代中国的生成和流变。事实上,李长之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把五四运动比作“启蒙运动”:“‘五四时的文化运动,与文学上的写实相当,只是一个启蒙运动。”他的用法显然与共产党人不同,毋宁说他是在相对负面的意义上使用“启蒙运动”这一说法。在李长之看来,“启蒙运动”意味着清浅的理智主义和功利主义,体现后者的“文艺复兴”只能期诸将来。
大约同时,周作人也试图发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见于1943年他写的《怀废名》一文。当时,他和俞平伯、废名、林庚“深感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正好有机会接手《世界日报·明珠》副刊。周作人的“启蒙”,意在以“与平民为灰”的态度,借助报纸媒体,将清明的知识灌输于市民阶层。他以为报纸不应该是宣传政见鼓动民众的机关,只需用浅近的通俗语言,把常识性的知识普及给读者,则启蒙之能事已毕。只是周作人并不擅长写通俗的启蒙文章,《明珠》副刊维持了三个月就草草收场。
30年代很多人谈“启蒙”,但对“启蒙”的界定则人言言殊,而且也并非都是在正面的意义上将其与“五四”联系起来。“启蒙”的概念何时进入现代中国,尚未见到从词源学角度对此进行梳理的成果。古代汉语中本来就有“启蒙”一词,但那意思指的是幼童发蒙,后来大概在近代被引中为“开启民智”之义,比如说晚清的《启蒙画报》。一个有意思的材料,19世纪末,最初日语是借用“文明”来翻译英文中Enlightenment。究竟何时“启蒙”成为Enlightenment一词的中译,还有待考察。我看到的比较早的材料,是许寿裳1908年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兴国精神之史曜》一文,其中谈及欧洲的“启明思想”:“启明思想,横溢欧陆,其特色一言蔽之日:以理想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二者,雠君权教權,欲尽举旧有之制度文物而一新之也。”这已经很接近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启蒙运动”了。后来,“五四”时期周作人作《欧洲文学史》,其《十八世纪法国之文学》一章论及狄德罗时,使用了“启蒙运动”的概念,但对译的是Illumination而非Enlightenment。看来这一笔糊涂账要算清楚还并非易事。
当代学者对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否可以和欧洲思想脉络中的Enlightenment等量齐观,也有不同看法。中国学者邓晓芒在他的《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等文章中,认为用“启蒙”来翻译Enlightenment一词并不恰当,用西方特别是康德的“启蒙”概念为尺度来衡量,中国现代启蒙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我并不认同邓晓芒先生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但是他注意到康德的“启蒙”观念诉诸的是普遍性的人类概念,而中国现代启蒙却难以脱离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二元结构,却是有启发性的。知识阶级和民众的关系在中国包括俄国这样一些落后国家,成为一个突出的中心问题,本身便值得重新思考。
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则认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都是一种除魅的规划和行动,她是在肯定两者的相似性一至少是可比较性——的意义上使用“启蒙”这一概念的;如果把“启蒙”看作是一个不断除魅或祛魅的过程。那么厨作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得相当彻底,他不仅致力于祛除传统纲常名教之魅,也致力于祛除一切新名教、新道统之魅,他之强调“清明的理智”、纯粹的智识,乃至于他的笔名“启明”、“开明”、“岂明”。都似乎更接近于Enlightenment一词的本义。但是舒衡哲的书中,对周作人特别是30年代的周作人着墨很少,倒是颇为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