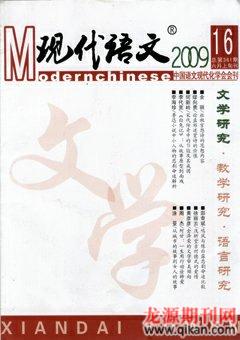抹不去的记忆
摘 要:文革结束以后,文学界面临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转型,“伤痕文学”成为文革后文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宗璞的《三生石》,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及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是伤痕文学中比较优秀的作品。“伤痕文学”在艺术上显得比较单调,但它留下的历史记忆是沉重的,也是抹不掉的。
关键词:伤痕文学 文革 文学转型
文革结束以后,文学界面临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转型,“伤痕文学”成为文革后文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小说以真实的描写显示出在文革劫难过去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代青少年心灵上的深重的创伤。宋宝琦是小说中描写的“坏孩子”形象,在知识无用、造反有理的年代里,宋宝琦走上了打砸抢的歧途。从外表上看,他蛮横粗鲁,身上是“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嘴唇是在斗殴中被打裂又缝上的,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不是他外表的疤痕,而是他空虚变态的内心世界,是他对美与丑、是与非表现出的惊人的无知甚至颠倒。宋宝琦的精神变态并不是因为他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他实际上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等思想一无所知,他之所以走上造反的道路是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和愚民政策的恶果。小说显示出,从宋宝琦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几乎都被打成了“臭老九”,他所学到的知识就是“知识无用”,他所崇拜的英雄是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作品层层揭示了宋宝琦变坏的社会历史根源,深刻暴露了极左时期的文化教育所造成的严重精神遗患。
《班主任》的警世意义不仅限于对宋宝琦一类的“坏孩子”的描写,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对谢惠敏一类的“好孩子”的精神变态的描写。在小说中,谢惠敏与宋宝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从政治意义上看,谢惠敏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那个时代“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个性上看,她纯洁、真诚、品行端正,具有“劳动者后代的气质”和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她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按当时的政治要求去做。如果说宋宝琦的失足在于他的愚昧无知,那么,谢惠敏的失足则在于她不折不扣地接受了一整套极左的政治教条,她的思想和行动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规范,她把穿短袖衫、穿裙子当作“资产阶级作风”,把对宋宝琦的帮助教育看成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对团组织生活用爬山代替念报纸表示无法接受……。这些描写表现出谢惠敏教条、僵化、愚昧、狭隘的内心世界,她思想的苍白和变态显示出极左政治对一代“好孩子”的精神污染和灵魂扭曲。谢惠敏的典型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那些曾经以革命的正统面目出现的“先进”或“红色”青少年的精神特征,暴露了现代迷信和愚民政治给青少年一代留下的精神创伤。小说概括地显示出,作为文革时期的产儿,“坏孩子”宋宝琦和“好孩子”谢惠敏在精神上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宋宝琦作为愚民政策的受害者而走上了打砸枪的歧途,谢惠敏则由于左倾思想的侵蚀而成为极左教条主义政治信仰的牺牲品。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孩子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内伤”,小说为此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喊,从而揭开了后文革时期新启蒙主义运动的序幕。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个小说从人伦亲情的角度控诉和揭露文革中的政治暴力对人的感情的摧残和破坏,“伤痕”作为文革时期精神创伤的标志成为几代人心中抹不去的悲惨记忆。小说叙述的是知青王晓华母女在文革中生离死别的故事。王晓华的母亲早年参加革命,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下救过伤员,并在敌人的监狱中受过折磨。在文革风暴中,王晓华的妈妈却被打成了叛徒,王晓华与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但妈妈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女儿,并为自己连累了女儿感到深深的愧疚。王晓华下乡插队之后,妈妈曾一次又一次给女儿寄去信和包裹,王晓华却一次次将信和包裹退给妈妈。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晓华妈妈的冤案得到平反,但却因为在文革中身心倍受摧残而病逝,她在临终前写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伤痕》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的缩影。
《班主任》和《伤痕》对文革的控诉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敢于正视历史灾难的勇气,这两部作品在社会上所产生的轰动不仅表明人们对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强烈共鸣,而且也表现后文革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继《班主任》之后,刘心武又连续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等作品,从不同侧面显示了文革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内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班主任》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在文学界得到积极的响应。郑义的《枫》以悲剧性的故事告诉人们,卢丹枫、李红钢这样的少男少女在狂热的现代迷信中丧失了正常的感情和理智,由恋人变成仇人,成为武斗场上的牺牲品。宗璞的《弦上的梦》揭示了梁遐既热情又冷漠,既聪敏又空虚的复杂性格,概括地表现了在文革中心灵上受到摧残和伤害的一代青年人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王蒙的《最宝贵的》、金河的《重逢》、张贤亮的《吉普赛人》等作品也从不同侧面揭露了文革所推行的愚民政策的罪恶后果,显示了文革对人的心灵的扭曲与戕害。
文革中的阶级血统论造成了严重的道德混乱和感情危机,对文革时期摧残人性的道德控诉是文革后小说创作中相对集中的主题。晓宫的《没有被面的被子》显示出,在文攻武卫的骚乱中,夫妻之间的温情被冷冰冰的宗派仇视所代替,家庭内部的冷战终于演变为武斗场上的流血惨剧。吴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冯骥才的《啊!》、冯国才,徐培东的《“我的罪过!”?》等大量小说作品向我们揭示了文革中阶级斗争宗派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对家庭、婚姻以及朋友之间人伦亲情关系的摧残与破坏,以血泪的控诉撕开了文革血统论和阶级宗教的帷幕,将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的悲剧性历史本质呈现给人看,暴露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在人们心灵上、感情上刻下的不可磨灭的深刻创痕。
作为文革的一面镜子,后文革时期的小说创作从多角度、多侧面表现了文革的历史悲剧及其发生的根源。宗璞的《三生石》以文革时期学校、医院中的派系斗争为主要背景,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推行封建法西斯政治的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径。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身陷逆境的知识者、普通群众相互之间纯真的同情、友谊、理解和支持的描写,表现了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美和善的力量。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取材于文革武斗风暴的高潮期。小说写道:“刹时间,界限没了,准绳没了,秩序没了。更多的是怀疑而不是信任,更多的是废除而不是保留。存在的一切,都需要重新甄别、判断和划分。一切人都要重新站队。然而,敌人依然不都站在敌人一边。一些人过了时的面具揭去了,另一些人悄悄蒙上更应时的面纱。敌我友、真与假、忠与奸、是非和曲直全纠缠一起。赤诚的战士、政治的赌徒、利欲熏心的冒险家、化了妆的魔鬼,一时混杂不清。”小说中的白慧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忏悔者。她的负罪感表现了她可贵的自责精神。白慧这一形象的悲剧意义显示着文革对那些盲目、热情的青少年而言是一个骗局:“隐身的骗子们在蜜果四边撒下拌了糖的毒粉,在征途的两旁布下铺了花的歧路。分辨它不单需要时间,还免不了经受痛苦的磨难、上当、受害,留下深深的创伤。”《铺花的歧路》的价值在于,呼唤社会救救那些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是重要的,而受害者自身忏悔和觉醒则更为重要。
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文革结束后,一代见证历史的知青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大量作品,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和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在同类作品中具有开拓性的文学史意义。
《蹉跎岁月》通过上海知青柯碧舟与杜见春这对出身不同的青年男女在上山下乡中的坎坷经历,表现了文革社会政治风貌与人间世态炎凉,集中揭露批判了血统论的荒谬及其灾难性后果,表达了“岁月蹉跎,人自沉浮”的人生课题。创作《蹉跎岁月》的直接原因是作者耳闻目睹了文革中血统论偏见对青年人的伤害的许多事例,于是决定写一本反对血统论的书。在创作中,作者没有局限于对血统论本身的批判,而是着重以一批知青的悲剧命运为线索揭示十年浩劫的灾难性后果。以柯碧舟、杜见春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小说塑造了个性不同、归宿各异的知青群像。柯碧舟正直善良,上进心强,虽一度在血统论的偏见面前沮丧消沉,但终于在贫下中农的鼓励和纯洁爱情的感召下振作起来,“把自己的青春与祖国、与人民、与集体利益联系起来”;杜见春直率热情,对“革命”抱有天真的幻想,家庭政治变故最终使她从磨难中体会到了人生的价值和爱情的真谛;唐慧娟勤劳朴实、稳重自强,最终赢得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王连发与孙丽萍对生活采取实惠而又乐观的态度,双双在县办企业安了家;一度堕落为小偷的肖永川曾浑浑噩噩、丧失理想,终于在领导和柯碧舟的帮助下改邪归正;轻浮势利的华雯雯追慕虚荣,在人生海洋里如浮萍一般漂浮不定;纨绔子弟苏道诚一味依赖父亲的政治权势,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支点……这些知青形象从不同侧面概括了一代青年人的追求与迷茫、沉沦与奋进,生动地展示了动乱时期青年人的坎坷经历和精神风貌。
竹林的《生活的路》以下乡知青张梁和谭娟娟的人生遭遇和感情纠葛为主线,一方面揭露了文革时代青年人思想上的混乱、精神上的痛苦和事业上的迷失;一方面揭示了那些“吸人血汗的恶鬼”的卑鄙伎俩和丑恶灵魂。在善与恶的强烈对比中,小说张扬健康的人性、人情之美,鞭挞兴风作浪的鬼蜮行径,对一代知青曾经走过的那段生活的路作出了严肃的思考。小说着力塑造了女知青谭娟娟的悲剧形象。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谭娟娟戴上红袖章、喊口号、作演说、贴标语,宣传“破四旧”、“立四新”,但她的父亲很快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洋奴、走狗、特务,她本人随之由“红五类”变成了“黑六类”。在同学张梁帮助下,谭娟娟选择了与父母划清界限,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下乡期间,她积极向组织靠拢,要求进步,按照党的指示批判走资派,批判下台的老支书,但却始终得不到组织的信任。她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努力上大学,为了一张招生登记表,她甚至承受了出卖贞操的屈辱,而她的希望却最终化为泡影。她终于领会到,自己苦苦追求的“生路”原来是一条“绝路”。谭娟娟是被时代欺骗愚弄的一代人中的一个代表,她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经历是对那个时代的强烈控诉。
在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中,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后文革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75年冬天,通过对普通农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家庭、婚姻、爱情的描写,表现了文革时期的极左路线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深刻创伤,概括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并深刻反映了合作化运动之后农村生活的艰难历程。小说在思想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一方面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再现了政治动乱、经济萧条、人心涣散、世风日下的社会风貌,一方面以满腔热情讴歌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讴歌人民心中不为邪恶所屈服的正义力量,从而揭示了光明战胜黑暗、真理战胜谬误的历史必然趋势。从整体上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开拓意义在于它摆脱了左倾教条理论制约下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那种浮泛地描写农业生产和农业运动的模式,较好地将社会灾难、家庭聚散和个人悲欢相结合,通过个人、家庭的悲剧表现了社会的、历史的悲剧。作品注重揭示人物性格与历史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人物在历史中获得了立体感,历史通过人物得到了形象化的表现。在艺术上,小说善于以细腻抒情的笔触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感情波澜,如对许秀云赶场前前后后的心理剖析,对许茂在干蠢事时充满痛苦自责的心理状态的描摹都极为传神。小说还注意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烘托,如以沱江漫天迷雾渲染葫芦坝的政治阴霾等等……这些描写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
鲁迅所批判的阿Q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健忘——无论多么深刻的痛苦和灾难阿Q都可以淡化而忘记,甚至转化为自己精神上的胜利。但历史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历史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伤痕文学”尽管在艺术上显得比较单调,但它所留下的这份历史记忆是沉重的,也是抹不掉的。
(刘德银 兖州 山东省贸易职工大学基础部 272100)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的其它文章
- 古典诗歌中的绘美二法
- 敦煌文研究综述
- 《惜诵》发微
- 军礼与《诗经》战争诗
- 蝉联对比,因果不爽
- 爱情与婚姻的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