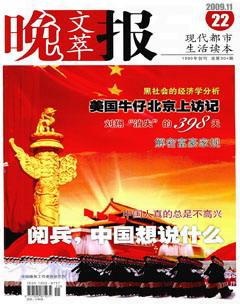刘翔“消失”的398天
万佳欢
奥运退赛和13个月的疗伤,让刘翔从聚光灯下回到一个真实简单的运动员身份,经过一年的蛰伏,他想清楚了自己需要的是找回做自己的心态和勇气,可他身后的人们却未必这么想。
在央视田径专项记者冬日娜眼里,复出后的刘翔有很大的变化。“我能感觉到刘翔是真的放下了,”冬日娜说,“从对他的赛前采访看,以前不大敢多打扰他,会有意识地保持距离;但18日对他的赛前采访,我觉得他的谈话欲望特别强烈,一个问题抛出去他可以说一堆。”这位刘翔最“贴身”的记者感觉是“经过这一年,他现在放松、自信,也淡定了很多”。
过去这一年,刘翔的生活变得很安静,他最主要做的是疗伤和恢复训练。他和师傅孙海平几乎阻绝(或被阻绝)了所有媒体和各种活动的“骚扰”,成为一个普通的正在治疗的运动员;而另—方面,公众对他的期待,以及因期待失落的不满—直包围着他,正在恢复中的刘翔,需要承担的不仅是来自身体和心理的信心重建,同时还必须对抗外界的各种声音,让自己不受干扰。
安静的幸福夹杂着重生的痛苦,大概刘翔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年。这或许是他最坏的一年,也是最好的一年。
最难熬的日子
2008年8月18日,刘翔退赛一个小时后,《解放日报》记者张玮拨通了刘翔爸爸刘学根的电话,想安慰他一下,电话却被对方挂断了。
张玮是刘翔个人传记《我是刘翔》的整理者,也是刘翔一家的好朋友。他给刘学根打过很多次电话,从来没有被挂断过。过了一分钟,刘学根回电过来,这时张玮反倒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气氛一度很僵。“后来还是他先开口说,‘没关系的,下次再来嘛。”张玮说,刘翔的父亲在赛后当天就哭得一塌糊涂。“那段时间他很痛苦,每天晚上都会一个人哭。”
至于好友刘翔,张玮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他——因为肯定关机。他只是发了一条短信过去,大概内容是“大家一样会支持你”。
第二天,刘学根去运动员公寓看刘翔,儿子正趴在那里接受按摩。看见爸爸进来,刘翔抬头看了一眼,又脸朝地趴下了。刘学根没跟他说话,隔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儿子头下的地板湿了,他的眼泪正在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从北京回到上海,刘翔拒绝了所有的媒体和活动。电视里反复重放奥运的精彩画面,他从来都不看。家里基本不敢开电视,所有人都有意地避开“奥运”“08”这样的字眼。10月,张玮和同事去刘翔家问候,那时候他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刘妈妈在家里开玩笑地说,“哎呀,瘸子来啦,瘸子来啦。”刘翔跟平常一样乐呵呵地同他们聊天,但午饭时,大家还都是心照不宣地岔开了有关北京奥运的话题。
“刘翔是那种嘴硬的人,有压力他不会说出来。”张玮说。
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是,退赛之后,拖着一条伤腿的刘翔只怕还来不及调整情绪,就必须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摆在他面前的是两条路:保守疗法和手术。
其实,刘翔的脚伤已经积累了好几年,但迫于比赛压力,他一直选择保守疗法,根本没有办法像普通运动员那样停下来根治。
“刘翔是特别爱惜身体的一个人,”央视田径专项记者冬日娜说。跨栏是最容易摔倒的体育项目之一,几乎所有的职业选手膝盖上都有疤,但刘翔很注意身体的协调性,极少摔跤,身上从来没有动过一个小手术。
与刘翔相熟的冬日娜曾在那时给他发短信说:“你可千万别开刀”。刘翔的回复是:“我才不开刀,开刀就完了,人就伤了元气了。”动过好几次手术的姚明也劝他认真考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手术:“就算做得再成功,一旦开刀,你的脚就不再会像你原来的脚了!”
但是,保守疗法意味着,情况还会跟北京奥运之前一样,只能继续“赌博”。“如果不开刀的话,熬着、养着也可以,但是说不定哪天又崩溃了。”张玮说。
究竟做不做手术?国内没有治疗跟腱病的专科,“会诊的时候,北京上海各处的医生都吵翻了,足足争了三个月,”冬日娜回忆道,“他一直跟他爸说‘你们别担心,我挺好的,但其实等待的那段日子他挺不开心的,也有过退役的念头。”
10月底,刘翔决定去美国休斯敦做一个检查。专家们发现他右脚的几个钙化物已经很大了,靠中药敷是消不掉的。经过跟教练组、田管中心的商议,刘翔终于忐忑不安地做出了手术的决定。
2008年12月5日上午,刘翔在休斯敦接受了跟腱手术。1小时20分钟后,医生成功地从刘翔的脚中一共取出来3个钙化物和1个骨刺。而他迷迷糊糊地醒来时,却问周围的人:“我在哪啊?”
手术顺利结束。但那只是他康复万里长征路上的第一步。
偷来的幸福生活
一直到2009年9月20日,比赛当天的下午,刘翔一边往比赛服上别号码牌,一边还对身旁的冬日娜感慨,“其实我在美国的那段日子还挺舒服的。”
对刘翔来说,休斯敦无异于暂时的桃源。他想在那里把自己过去的事情淡忘。
他与教练、队友一起租了一个不大的房子,在那里,他得以逃开媒体和各种活动,每天很有规律地治疗、训练,吃妈妈做的可口的家乡菜,生活宁静而自由。
2009年2月3日,在刘翔手术后2个月,张玮随孙海平来到休斯敦。他发现刘翔的情绪很好,伤脚恢复得也不错。孙海平给刘翔安排的第一次室外训练是绕着400米跑道的“大步跑”,结果刘翔跑得活蹦乱跳,把孙海平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
训练之余,刘翔拥有大把的休闲时间。他带来了整整一箱子变形金刚和高达模型,一有闲暇就掏出来,一边听音乐哼歌,一边安装。张玮在那一周时间里,看着刘翔拼好了机动战士高达的一只巨大的手臂。
周末,刘翔还可以去城里逛逛街、下顿馆子。张玮跟他去奥特莱斯(outlets)买过一次衣服,他看中了一件,非逼着张玮和谢文骏也一起买,于是三人买走了三件一模一样的。在路上,除了偶尔有一两个留学生,基本上没人能认出来他。
不过,张玮在看刘翔训练时很不解地发现,刘翔居然在一开始的10分钟慢跑热身时就开始跟大夫讨价还价。后来他才明白,美国大夫要求刘翔的恢复训练方式跟我们印象中伸伸腿、动动腰的康复训练完全不同,包括接下来的几组器械训练、“电子游戏”训练都是以动手术的右脚跟腱为支撑点做蹬腿运动,累得刘翔叫苦不迭。张玮亲自试了一下,以他正常脚踝感觉强度的确很大,“那个时侯,他的康复训练已经进行了差不多2个月,刚开始上这个量的时候肯定更难。”“你觉得自己最刻骨铭心的困难会在哪里?”张玮曾这样问刘翔。
刘翔立刻回答他:“我简直怀疑自己连康复训练都不能扛过去。”
继续作为“神话”还是成为“朋友”
但刘翔没有想到,来自外部环境的、不可控的压力和痛苦,会远远超过身体和心理上的——自己原本想在美国彻底放下,但国内舆论并未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停。
2009年3月初,刘翔尚未回国,就因为连续第二年缺席政协会议引来一片劈头盖脸的骂声;3月底,他又接连遭遇凯迪拉克车主索赔事件和身价缩水等一连串的负面
报道。7月,他的事迹进入历史教科书,又挨了不少口水。
北京奥运退赛后,关于刘翔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张玮曾以此为主要案例撰写了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他发现,和以前“铺天盖地”的报道相比,这一年来媒体对刘翔的报道量锐减,“但只要出来一篇,都是重磅,关注度都比以前高。”张玮说。他同时还发现,质疑刘翔、爆出负面新闻的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小的媒体”,但是消息通过网络转载,谩骂、嘲讽和看热闹的声音迅速蔓延(孙海平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有很多诋毁我们的人都是枪手,背后有指使者”),这些声音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全社会质疑刘翔的印象。
那么多不同声音的存在也让刘翔明白,要复出比赛,不仅仅要过自己这一关,还必须跨过许多横在他头顶上的东西——各种被神化的头衔和怀疑的声音,以及13亿人的眼光和期待。
回国后,刘翔—直住在莘庄训练基地最普通的运动员宿舍。训练的日子大都是平静的,直到在他复出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训练课上,媒体蜂拥而至,莘庄训练场的跑道上甚至都拉起了绳子。直到6月,孙海平还表示,他和刘翔对于未来都是心里没底,他告诉外界,“现在的状态和北京奥运会前的状态真的很像,抱着—点幻想,等着一个时间、一个结果。”
7月11日,刘翔从训练基地回家提前庆祝两天后的生日。他主动跟亲戚们合影,吃得也很开心。刘学根发现他开始愿意接近人——退赛以后刘翔是不愿意见人的,一去人多的地方就烦躁。
晚上,刘学根叫住儿子:“聊聊?”刘翔摆摆手上楼,准备睡觉,过了一会儿却又走了下来,把袜子脱了说:“你不是想看伤处吗,给你看。”
这是刘学根第一次在儿子伤后看到他的右脚后跟_之前,刘翔一直抗拒给别人看这个部位。他看完抬起头,发现刘翔躺在沙发上,已经泪流满面。
9月20日比赛这天,刘翔的心态和感觉都十分良好,13秒15的成绩也使大家震惊——媒体随即一面倒地亮出“王者归来”的大标题,网络上的评论恢复了狂热,那些一年前出现的冷静和反思又在瞬间被掩盖了。
这些赛后效应,对于刘翔和身边的人是熟悉的,是他们无力拒绝却未必需要的。
张玮还清楚地记得今年5月,他跟刘翔、孙海平一起从北川灾区回上海时的一件事。当他们三人慢慢走出浦东机场的时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40多岁的中年人斜靠着栏杆,看到他们时,他转过身来看着刘翔。他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很激动地大叫刘翔的名字,或要求合影,只是用上海话对刘翔说:“最近脚恢复得怎么样?”
刘翔答道:“挺好的,谢谢。”然后继续向前走。
张玮觉得,大家都认识刘翔,但也就把他当做一个熟悉的普通人,这恐怕才是刘翔最需要的生存状态。
(摘自《海口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