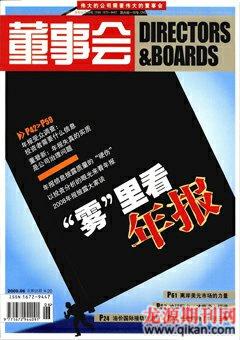纯粹的美
卫西谛
尽管这是一部颓废美学的电影,潮湿、闷热而且缓慢,但它有一种纯粹,有一种纯粹的美,只属于艺术范畴的美
忽然想看维斯康蒂在1971年拍摄的《魂断威尼斯》。是想放下太多包袱,解放眼睛。看电影的时候多了包袱,我们就会把不深刻的电影想深刻了,把不抒情的电影想抒情了。现在能感动自己的电影太少了,但是能感动自己的人越来越多。
而《魂断威尼斯》只需要去“看”。尽管这是一部颓废美学的电影,潮湿、闷热而且缓慢,但它有一种纯粹,有一种纯粹的美,只属于艺术范畴的美。
音乐教授古斯塔夫・阿申巴赫来到威尼斯养病,邂逅美少年塔契奥。这是真正的“邂逅”,没有任何情事发生,有的只是擦身而过、目光偶遇以及幻想中轻轻触摸的发梢。塔契奥之美,犹如古希腊的雕像,且发乎自然,毫无雕琢。但是,除了刚出生的婴儿,没有人会是完全“天然”的,所以这“毫无雕琢”,是维斯康蒂自己没有赋予少年塔契奥任何性格,只让他以美的形式存在,以孱弱的躯体存在,以玩闹和嬉戏存在。
阿申巴赫的目光焦灼在塔契奥的面庞、身体与微笑上,内心翻涌着爱。而这同性之爱、单方面的爱、穿越年龄的爱,让他背负羞耻与恐惧,甚至想迅速逃离威尼斯。结果他甘愿沉沦,因为迷恋这纯粹的美、纯粹的爱,而游荡在这座瘟疫蔓延的水城。在阿申巴赫对塔契奥的凝视中,总是出现与朋友艾弗雷德的谈话,他们探讨着纯精神境界,争论着美是否远在艺术出现之前就存在,以及音乐是不是最暧昧、最含糊的艺术形式。
有位维斯康蒂的传记作者写道:“这部电影所表现的内容几乎仅仅是缓缓走向死亡的进程。如同肉体日渐衰落,丧失了个性,最终化为乌有。”《魂断威尼斯》 似乎就像塔契奥一样,只能凝视,短暂而虚幻。纯粹的美,应该是毫无意义的美,不应被赋予任何理想、任何含义。纯粹的美激发出来的爱,也似乎是“无能为力的爱”。因为这种爱也不被赋予任何性的意味(追求或占有)、任何世俗的意味(诸如结婚、生子)。
古斯塔夫·阿申巴赫这个人物在托马斯・曼的原著中是作家,灵感来源是古斯塔夫・马勒,一位“未来的同时代人”(马勒的一部传记名);而维斯康蒂将其 “还原”成音乐家(和他交谈的朋友艾弗雷德,是以幽灵形式出现的虚幻人物,原型是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里影射的音乐家勋伯格)。《魂断威尼斯》中的音乐几乎都来自马勒的作品,主题是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第三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影像与音乐完美地交织在一起。维斯康蒂本人就是在音乐声中去世的,有个著名的传说是,在反复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之后,他说,“已经足够了……”然后离开这个世界。这是1976年。
阿申巴赫虽然在海滩上死去,遮饰他花白头发的染发剂在烈日下流在他的脸颊上,像蜡像被日光融化。在他的目光中,塔契奥站在海边的霞光里,一手撑着腰,一手指向远方和未来。然而扮演这位绝美少年的演员伯恩・安德森(Bjorn Andresen)的厄运却在银幕之下接踵而至。我读到一个帖子,说维斯康蒂的情人不满塔契奥的角色被抢,多次谣传他死于车祸、空难、滥服药物……在维斯康蒂死去的那年更被卷进一桩谋杀案。多年来,这位主修大提琴的少年只能“靠打零工生存”,“舞台导演,戏剧配乐,灯光,钢琴老师,会计,为了赚钱还洗盘子,清洗剧院,兼职乐队键盘手……”直到中年后他才重返影坛,在一部瑞典电影里扮演一个小角色。据转引的资讯,说从2004年的一次专访里可知“他和两个女儿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一间公寓内,一起生活的还有一只猫,一条狗和一只仓鼠”。
你看,纯粹的美在艺术中多么有感染力,而在现实中是多么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