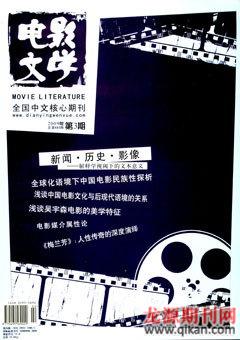论台湾本土电影中的后殖民元素
王 璟
[摘要]《海角七号》在台湾连续上映超过3个月,票房屡创纪录,不但在岛内成为2008年度最具话题性的电影,更可谓台湾影坛近20年来的奇迹。这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电影,其内容从大框架到小细节都充满了后殖民色彩,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新浪潮以来本土电影的传统,却又更为精致并受到大众的欢迎,是研究台湾本土电影中后殖民元素的良好例子。
[关键词]《海角七号》;后殖民电影,台湾本土电影
一、《海角七号》热潮与内容简介
2008年在台湾岛内刮起观影旋风的本土电影《海角七号》,其制作成本耗资台币5000万元(约合人民币l100万元),于8月22日正式在台湾上映。最早经由民众在网络上口耳相传以聚集人气;而后引起媒体关注并大肆报导此波风潮,也更加强了《海角七号》的热度,从政治人物、文艺界人士到普通百姓,进戏院看《海角七号》成了全民运动。上映3个月以来,全台票房已突破台币4.6亿元(约为1亿人民币),不但成为台湾影史上最卖座的本土电影,如今也在香港与新加坡等华语区上映且获得不错的回响,影片中的背景音乐与拍摄景点还大大地带动了台湾音乐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堪称是台湾影坛近20年来的奇迹。
影片叙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结束了对台湾的统治,被遣返回国的日本籍男教师与他的台湾籍爱人就此天人永隔,男教师在船上写下了充满着悔恨与无奈的七封情书,并在封面标示着地址——“台湾恒春郡海角七番地”。但随着两人各自另组家庭,这七封情书始终没有寄出,直到男教师去世后,他的后人才将这些信件寄到台湾。然而经过这么多年,沧海已成桑田,当初称作“海角七号”的地址早就不复存在。另一条线则是六十多年后的现代,男主角阿嘉在台北的音乐圈奋斗了十几年,却仍闯不出个名堂。失意的他只好回到台湾最南端的恒春老家疗伤取暖,并因为继父的关系接下了在当地寄送邮件的工作,这些邮件中便有那来自日本,要寄到“海角七号”的邮包;同时,恒春当地的饭店欲举办活动以宣传自身品牌,经营方打算邀请知名日本歌手赴台表演,此举却被镇民代表会要求必须得用当地乐团负责演唱会的暖场表演,否则没戏。但恒春小镇原本并无乐团,当地年轻人大多离乡打拼事业,人才资源相当有限,要成立一个能拿上台面的乐团具有非常大的难度,镇民代表为了面子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临时在镇上征选了一批稍微会点乐器的杂牌军,硬是凑出了一个摇滚乐团,而较有音乐才华的阿嘉便被委以团长的重任,负责歌曲创作、乐团练习与最后的登台表演。
六十多年前在太平洋上的自白与现今南台湾小镇中的风波,这两条主线蒙太奇式的交互进行,并以七封情书作为跨越时空的连结。
二、《海角七号》中的后殖民元素
作为一部台湾本土电影,《海角七号》的后殖民印记并非是来自国际媒介霸权的意识形态宰制,也不仅仅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如今融入或隐藏在生活中的文化符号。而是更为直接的挑起后殖民时代对于过往殖民历史的回忆,这些精神上的印象、认知以及物质上的文件、资料,不论其影响是好是坏,如今都还深深地存续在台湾社会中。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中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于是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日本在台湾50年间的统治,直接地影响了两到三代的台湾人。据台前期,日本政府遭受台湾居民剧烈地反抗,爆发多次抗日活动,虽然都遭遇日本成功镇压,却也造成日本政府损失惨重。为了协助统治政策的实施,日本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警察制度。当时日本警察的执掌完全涵盖了一般台湾民众的生活,并且动辄粗暴恶劣地干预人民的日常生活。使得台湾人对于警察非常惧怕。到了后期,台湾人的反抗从武装行动转为较为平和的社会运动,争取民主与自治,此时日本也较为注重台湾人的认同,并针对台湾籍儿童实施义务教育。据统计数据显示:1915年以前,台湾籍儿童受教育比例不到10%,而在1920年便跃升至四分之一,到结束统治前的1944年竟高达71.3%。(资料来源:《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第1241页)可见在日本统治下的第二、第三代台湾人。大多受过完整的日本初等教育。也因此,警察与老师两种形象便构成台湾人的殖民记忆:警察代表了负面的、恐惧的符号,而老师则为正面的、友善的符号。
《海角七号》中以日籍老师写的信作为楔子,将正负二元对立的印象天平往温和、柔情的方向倾斜了,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身为战败国公民的老师,怯弱、无助的身影在大海上漂荡。他满怀罪恶感却不是来自于殖民者的占据,也不用承担战败的责任,只是怨恨自己无法信守对于爱人的承诺,既不能留在台湾,也无法让对方跟着自己回到日本,为此他几度潸然泪下。这原本就是大时代投射在个人身上的悲剧映照,相当合于台湾人偏好悲情的胃口。因为台湾本身的命运就是任凭历史洪流一再摆布、捉弄。关于这点,亦可参考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但和《悲情城市》不同的是,《海角七号》用另一条极为诙谐逗趣的现代主线“稀释”了历史悲情的成分,这也是它能受到追捧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导演还试图用现代的浪漫爱情增加影片可看性,并和多年前那段不了恋情相互照应,阿嘉在海滩边抱着日籍女公关友子,说出那句“留下来,或我跟你走”,就是再清楚不过的证明,可惜碍于影片要表达的内容太多,这段现代的激情欠缺深刻的说服力。在后殖民时代中显得相当突兀与苍白无力。不过大众似乎也不计较这么多,片中几处稍嫌牵强与不合理的地方并不妨碍《海角七号》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另外,受日本老师教导的台湾学生,绝对是台湾后殖民电影中,延续殖民记忆最重要的“载体”。昊念真导演的《多桑》便是极佳的佐证,凡是跟电影中多桑同样环境中成长的台湾人,都遭遇了日本皇民化政策的洗礼,他们或多或少会有缅怀日本统治的心理,《多桑》一片中也清楚地看到那些毕生都想到日本“朝圣”的台湾人。他们对于富土山的崇拜不亚于一般日本民众,甚至因为千山万水的阻隔,更增添几分可遥望而不可企及地神秘幻想。当然,这样的崇日心理总会不经意地在日常生活中流露,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乃吴念真这一辈的台湾人。今日在台湾,曾经受过日本教育的老年人大多相当怀念儿时上学的日子,他们还能说几句带有日本九州腔调的日文,也能哼上几段自学校习得的日本童谣。《海角七号》里戏份相当吃重的配角“茂伯”就是这一类人,他能操使简单的日语会话与日本人沟通-平日骑在摩托车上,嘴里唱的是翻译成日文的德国民谣《野玫瑰》。
《野玫瑰》原为德国文豪歌德的诗句,后被大音乐家舒伯特谱上乐曲,广传于世。歌词亦被翻做多种语言以便传唱,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小学教科书内分gU收录了日文版与中文版的《野玫瑰》,所以这是一首被两地人民所熟知的民谣歌曲,也成为《海角七号》剧中富有多重意涵、相当重要的符号。剧情在稍早时就埋下伏笔,茂伯唱着日文版的《野玫瑰》并且在乐团练习时以月琴弹奏,一旁的阿嘉竟然也能跟着一起哼,当然,阿嘉会唱的肯定是中文版本,突显了《野玫瑰》的恒久性及共通性。影片末段的演唱会场景上,本土乐团的团员皆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共同演奏了中文版的《野玫瑰》,此时台下的日本歌手也走上台以日语一起合唱,打破了主客尊卑的界线,颇有尽释前嫌、雨过天晴的况味,爱恨情仇随着彩虹的出现而飘散。
更重要的是,要是深究《野玫瑰》的歌词,其主要构成分为三段:先是男孩看见野玫瑰,再来是想要拥有它,而后是摘折了花朵。此般心路历程竟然与日本从发现、觊觎到占领台湾岛的演进如出一辙。男孩的任性强夺仿佛日本野心勃勃的殖民,野玫瑰则好比台湾,不论怎么挣扎也奈何不了男孩。不过《海角七号》的导演在处理这层“所指”时倒是保留了不少,将最残酷的第三段“能指”巧妙地抽离,并借由画面将前两段歌词的意涵导向1945年基隆港岸的悲情离愁。相信大多数的观众都会在当下将《野玫瑰》里的男孩想做是日籍老师,把野玫瑰比作曾经美艳动人而今锥心刺骨的爱情。但沉淀下来后,却又感到这么比喻有那么一丝丝不对劲,于是将《野玫瑰》的歌词摊开一看,这才惊觉上了导演的当,那不能说的秘密终究还是后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