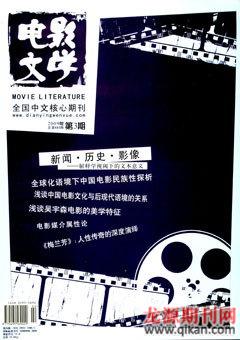“底层”创伤、性别倒置与视觉权力
刘保庆
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自公映以来,褒贬不一。梅兰芳是个伶人,伶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从底层叙事角度分析,这部电影显示出非同一般的视觉潜力。
一、“底层”创伤
电影《梅兰芳》讲述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幼年到少年成年的悲欢离合故事。故事大致选择了梅兰芳一生中死别、生离和聚散三个片断来讲述,把这三个片断贯串起来的是梅兰芳大伯临死前写给梅兰芳的一封信。
在电影中,信件出现了四五次。大伯的信不仅是这部电影的外在线索,把整部故事勾连起来,还是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因素。这封信蕴涵了大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感悟,不同阶段的梅兰芳对这封信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
信件对整部电影以及梅兰芳这个形象形成了一种控制,体现在电影先放映幼年的梅兰芳读大伯的信件,然后才打出字幕“梅兰芳”。信件就好像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前面的“序”一样。对整部影片发挥着不断阐释、控制的作用。
信对幼年的梅兰芳产生了一种“震惊感”,表现在电影中幼年的梅兰芳读到大伯因为戴上纸枷锁时那惊讶和恐惧的镜头。太后的万寿节人人穿红,大伯因为舅母出殡没穿,被“赏赐”一纸枷锁,撕破一点就弄死。纸枷锁事件对幼年的梅兰芳造成创伤,形成辉之不去的阴影,对唱戏产生一种内心深处的恐惧感。纸枷锁事件,在电影中被大伯解释为“记着,唱戏的再红,仍然让人看不起”。
“创伤”是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创伤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当人经历比如死亡、暴力等灾难时,心理上会产生焦虑不安、无助感。为消除这种“痛”,当事人把它压抑进“潜意识”,但创伤并没有消失,时常会冒出来,“侵蚀”人脆弱的自我。弗洛伊德创伤理论揭示了创伤不仅仅是个生物意义的疾病,而且想象和幻想在对付创伤中的作用。”
这种精神创伤是由歧视造成的,摆脱这种创伤的努力是梅兰芳和十三燕演戏的动力。电影《梅兰芳》讲述的不仅是梅兰芳面对精神创伤的心灵史,而且是作为“底层”的伶人反抗命运的抗争史。纸枷锁不仅笼罩在梅兰芳心灵上,而且笼罩在所有伶人身上。如邱如白所说纸枷锁可怕在于它是薄薄的,易撕开。可是如果可以撕开,那么梅兰芳的爷爷、大伯早就撕开了。
二、循环逻辑
提高伶人地位,改变伶人被歧视的现状,是梅兰芳和十三燕共同面临的问题。
十三燕对自身地位有清醒认识“因为我们是下九流啊”。对于自己出神入化的戏剧表演,十三燕极其自负,同时又深深感受到了自己从事职业的卑微。在十三燕观念中,要提高伶人地位,必须改变社会对伶人的印象。要改变社会对伶人的印象,就必须唱好戏,而且要按规矩唱戏。十三燕的观念是传统专制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也就是认同现实秩序,如同启蒙者邱如白所说“只能申诉,不能反抗”。这就注定了十三燕反抗命运、争取地位的人生是个悲剧。这集中在梅兰芳和十三燕对待“改戏”态度上的区别。
启蒙者邱如自批判京戏处处都是规矩,戏中的人是死的人,而真正的好戏应该是带人打破规矩的。邱如自代表当时启蒙者对大众的启蒙,因此要求改戏。梅兰芳深表赞同,这和他内心深处的纸枷锁创伤分不开。要想消除或弥合纸枷锁创伤,要么不把它当作纸枷锁,完全和戏中人物合一-要么就是打破纸枷锁,彻底消除可能戴上纸枷锁的恐惧。因此,梅兰芳坚持改戏,也是为了消除歧视带来的创伤。
十三燕认为,改了戏会被别人看做是朝三暮四,会加深别人对伶人身份的歧视:伶人是下九流啊。马三认为改变被歧视的命运就是认同现实专制秩序,演好戏,唱红了才能获得别人尊重。他遵循的是个循环逻辑:要提高伶人地位就要唱好戏,把庄重而高贵的京戏人物演活,这样才显得庄重和体面。但是现实是,他越唱得好,越无法改变伶人被歧视的现状,也越符合伶人的身份,越被人歧视。
第二场比赛十三燕失败,马三把瓜子皮吐在戏台上。这在十三燕看来简直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这台上这么尊贵的地方,容你这么糟蹋啊?”戏台是体现其生命价值的地方,糟蹋戏台就如同糟蹋十三燕。为了希望马三不要糟蹋戏台,十三燕甚至向马三鞠躬。但当十三燕要求十三燕低三下四给他再次鞠躬时,他高声拒绝“那得爷乐意”,这在十三燕看来是人格的侮辱。但是十三燕明知必败仍然要唱,他并非想要通过第三场来获得座儿的认可,而是要赢得人格和尊严。
马三的侮辱使得十三燕从梦中惊醒,让他认识到,作为伶人再唱得好也被人歧视。所以他告诉梅兰芳“等你大成了,一定要大大方方地提拔提拔咱伶人的地位”。
从清末到民国这段传统和西方思想交融中,伶人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十三燕的悲剧暗示出处于底层伶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他为了争取人的尊严而付出了生命,让人体会到老一代伶人高贵的人格,同样对社会歧视产生一种批判。
三、看与被看:性别倒置
大伯的纸枷锁创伤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梅兰芳同样并没有因为战胜十三燕而克服纸枷锁创伤。纸枷锁的阴影还时刻让他感到焦虑、不安、无助,体现在他怕输上。
邱如白留过洋,思想激进,反对京戏中存在的规矩,反对专制、压迫和歧视,主张好戏应该启蒙大众,打破束缚人的规范,从而解放人。邱如白是启蒙者。影片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示出底层伶人的精神痛苦和创伤,而且对现代启蒙思想同样进行了批判。
视觉文化一个重要发现是,思想的形成并非仅仅是观念,而是和人的视觉分不开的。脚弗洛伊德认为窥视癖是人的心理本能,窥视癖满足了人内心潜意识的需要,人们通过看来得到性的满足感。
看与被看构成了电影的内在结构。戏院不仅让观众欣赏艺术,提供艺术欣赏的对象,而且在布局安排上体现了一种等级制度。看戏已经被性别化了。梅兰芳扮演旦角。在戏中,梅兰芳不仅是京戏故事的一个人物,更主要的是成为观众欲望投射的客体,承载着观众的欲望。被看的是女性,看的观众是男性。男性的观众正是在看戏中女性的梅兰芳,从而获得一种性的欲望满足。这种观看机制不仅存在封建专制的被启蒙者看戏上,作为启蒙者的邱如白第一次看戏时,也获得了欲望投射的快感。影片中邱如白讲自己不知道该把梅兰芳当作男人,还是当作女人。实际上,作为启蒙者的邱如白、胡适等和被启蒙的大众对梅兰芳的观看都是一样的:男性看女性。戏台给观看的人戴上一层“艺术”的光环,让看者可以光明正大地来释放自己的性欲。
视觉文化认为看与被看还存在一种权力关系。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是不平等的一种关系。这种不平等和歧视不仅表现在观众对伶人梅兰芳的欲望观看;而且还体现在梅兰芳自己看待自己的态度上:观众把梅兰芳当女性看,梅兰芳习得这种观看方式,并内化于自己观看自己的方式。
现实中,梅兰芳把自己看作男性,在戏台上,他又必须把自己看作女性。出于理性的考虑,在现实中,梅兰芳必须把戏台上的自我观看方式压抑进潜意识中去,才能成为一个
“正常人”,即男性。但这两种观看方式必然发生冲突,造成人格的分裂。这就是性别倒置,通过刺客刘锡长间接表现r出来。
刘锡长是梅兰芳的另一面,是梅兰芳自视为女性形象的被压抑对象。刘锡长为了迷上梅兰芳,让梅兰芳看自己一眼,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枪杀孟小冬。梅兰芳一方面想接近孟小冬,一方面又排斥孟小冬。作为梅兰芳的女性自视形象,刘锡长枪杀孟小冬,其实是梅兰芳人格中男性眼光和女性眼光的矛盾。
纸枷锁指的是一种内在心理控制即自视。梅兰芳属于座儿的,他要受到座儿的制约。座儿把他当作了女性来观看,那他就不能把自己当作男性。孟小冬的出现让梅兰芳重新感知到自己的男性身份。他要和孟小冬在一起,其实是他挣脱纸枷锁的努力。但作为纸枷锁主体的观众逼迫他离开孟小冬,因为他这样做和座儿对他的观看发生了冲突,所以邱如白要雇杀手逼迫孟小冬离开梅兰芳。如果梅兰芳和孟小冬在一起,他就不能把自己和戏中的女性融合在一起。邱如白认为“只有心中最干净的人才能把情欲演得那么到家,那么美”,孤独成就了梅兰芳,谁毁了梅兰芳的孤独就是毁了梅兰芳。
影片展示出,现代启蒙思想虽然批判了京戏中的封建专制思想,如邱如白批评京戏对女性的约束,提倡解放人,打破压迫和规矩。但是,现代启蒙思想重新塑造了新的视觉专制机制,同样对底层的伶人形成一种压迫的力量。
四、现代明星机制
梅兰芳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国,再到现代三个历史阶段,伶人的地位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就是现代明星机制的形成。与传统不同,现代明星机制表现在;明星是个公共人物,他不仅在戏中属于观众,需要迎合观众欲望的投射,而且现实中也必须符合观众对他的想象和期待。
如果说传统社会把伶人当作低一等人看待,现代视觉机制则要求明星的私人生活也必须符合观众对明星的期待,一种无形的视觉压迫更生活化、更细微化了。当现实中的梅兰芳把自己当作男性接近孟小冬时,邱如白不惜一切手段阻止,标志着现代演员的私人生活已经成为公共空间了。
演戏不仅带上了政治色彩,而且还包含民族歧视和文化侵略意味。日军攻陷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毫无人性的南京大屠杀。为掩盖日本野蛮中国的罪行,实行愚民政策。日军认为梅兰芳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最能表达中国人的情感和人心,让梅兰芳给日军攻陷南京唱戏,是为了从文化上让中国人俯首称臣,为了维护日本的非正义统治。演戏同样也是对中国人的民族歧视。梅兰芳扮演旦角,最能代表中国人心,观看者为日本人。日本人观看演出,其实内在的是主动/男性/日本人与被动/女性/中国人的对立结构。演戏中看与被看的权力结构再次转化为,中国人是低等的、女性的、柔弱的、被动的、是被观看的;而日本人是高等的、男性的、刚强的、主动的,是观看者。
为了抗拒这种歧视,表明民族大义,梅兰芳的留须明志就不仅带上了民族反抗、文化反抗的色彩,而且也是他消除纸枷锁创伤的一次努力。留胡须,在日本军官田中隆一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认为是梅兰芳戏弄自己。田中隆一在这里的质问不仅代表了日本对中国的民族歧视,因为留胡须就不能再让日本人把中国人当作女性来欣赏;而且也代表观众对梅兰芳的质疑。田中隆一也像中国观众一样喜欢京戏和梅兰芳,表明观众开始把演员的私人生活也当作观看的对象,不允许梅兰芳打破观众对其女性形象的欲望想象。梅兰芳留胡须在观众看来不只是戏弄自己,更是戏弄他们心中的欲望,让观众欲望的投射无法实现。
梅兰芳留胡须,不仅是明民族大义,也是一次消除纸枷锁创伤的努力,表明自己的男性身份。梅兰芳希望观众在现实中把自己当男性看待,也是争取伶人地位的努力。影片让他在留须明志时再次讲到大伯、十三燕对自己的期望:体体面面提高伶人的地位。而他能做的只能如此。留胡须,梅兰芳想表明,伶人也有民族气节,而且是有尊严的人。
现代明星机制把演员当作公共人物看待,使得演员不仅要演好戏,而且现实中也要受到观众眼光的观看和约束。这在当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被当作“狗仔队”的记者为了满足观众对明星的窥视欲望,竭尽所能报道明星的隐私,已经成为约束演员的一种压迫性力量,这也是影片创作的现实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