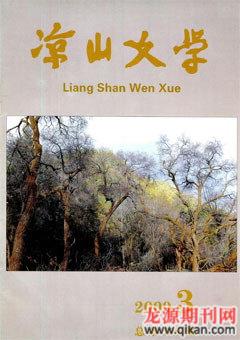让灵魂自由飞翔
黄 玲
彝族作家李骞是一个写作上的多面手,出版过小说及理论专著多部。他同时还是一名诗人,以执着的精神坚持着对诗歌的挚爱。李骞新近出版的诗集《快意时空》,收入他写诗二十五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作120余首,其中还包括一些组诗和三部长诗的节选。可以看作是对他诗人生涯一次比较全面的艺术回顾和总结。诗歌是诗人梦想的集中体现,是对世俗人生的理想超越。李骞这部诗集比较清醒地体现出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追求:以执着的精神坚守,以豪放的姿态追求快意,以率性的情感表达创造美感。同时也可以透视出灵魂世界的另一侧面,在诗人与非诗人之间,世俗与理想之间的挣扎与沉浮。作为诗人,他追求让灵魂自由飞翔的境界,追求情感表达的纯洁性。而这本诗集,就是他的灵魂在自由飞翔中咏唱出的生动旋律。
一
对一个专门从事诗歌创作的人而言,这部诗集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多。但是像李骞这样以业余身份坚持写诗的人而言,则应另当别论。从他开始写诗的1982年到2007年,二十五年间他都没有放弃对诗歌的挚爱,所写的诗积累了1200余首,公开发表400余首。《快意时空》中的大部分诗都选自于发表过的作品。这表明他对待诗歌的某种态度。写诗是自己心灵的释放,追求自由表达的快意。但是编选诗集,还得顾及到作品的审美取向和诗歌创作经历的展示,所以经过了认真谨慎的筛选。
从诗集的目录中可以大致透视出李骞诗歌创作的历程和走向。第一辑“我的滇东北”,有明显的地域意识;第二辑“长诗岁月”,是他发表过的几部长诗的节选;第三辑“白话方阵”,带有他对诗歌写作的试验痕迹;第四辑“情感间距”,顾名思义是诗人情感世界的集中展示。应该说整部诗集注重了诗歌写作的时间线索,囊括了李骞从1982年学生时代创作的诗歌,到2007年写的部分短诗。但又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而是力图从四个角度展示诗人的追求。所以诗集的艺术风格并不统一,前期诗歌比较纯情和富有想象力,青春的激情带着野性的色彩穿过诗行,比较集中于对故乡、地域、乡土的咏唱。后期诗歌在诗的激情中多了理性思辨的色彩,诗歌取材的范围随着诗人人生阅历的拓展变得更加丰富。李骞自己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的诗歌风格很不统一,就像我这个人一样,总是率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的诗也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段话透露了李骞在诗歌写作中的态度:追求自南、率性的写作。在写诗的过程中感受灵魂的快意,努力而不刻板。所以,这是一本内容丰富、驳杂的诗集。既有对童年、故乡的深情回望,也有天马行空般的历史岁月中穿行的篇章。既有对理想世界诗意的咏唱,也有和世俗生活纠缠不清的呓语。开篇第一首《牧童》,展现的是一个纯情、诗意的场景:“把草滩染成金黄的不是夕阳/是牧鞭下流动的羊群。把百鸟呼喊出树林的不是山鹰/是牧童嘴里抖动的歌谣。”从诗行中可以看出李骞早期诗歌受民歌影响的痕迹。但诗的最后一句却透露出诗人内心的大气:“放羊的孩子虽然渺小/除了牛羊他还放牧群山。”在温情的抒情气氛中,视角的广阔提升了诗歌的境界。而他的《作品70号》,则把世俗生活的复杂与沉闷对心灵的伤害展现无遗:“白天有阳光我是正人君子”,“夜晚没有颜色/所有的表情都无人读懂/于是我变成另一个我。”而这种“变”却不是诗人自愿的选择,而是面对世俗生活做出的无奈应对。讲述折射了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坚守和这一坚守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他写《牧童》《青青的菜,白白的菜》这样抒情的小短章。但他也写《彝王》《圣母》这样大气磅礴的史诗。他在诗中描绘金沙江、滇东北的雄浑壮阔,也会在诗中写苞谷、土豆、白菜这些俗而又俗的事物。他还在诗中思考“男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为什么走走停停”这些充满哲理的问题。诗的翅膀既在天空自由飞翔,也会在大地上俯冲盘旋,尽情舞蹈。当然,诗人的飞翔并非是追求简单的运动快乐。他在飞翔中总是会有自己的目标,向着蓝天白云,向着宇宙的无穷空间升腾。著名诗人于坚说:“诗人永远是时代的陌生人,甚至也是他自己的陌生人。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在幻想中高枕无忧。他不能回避他置身其中的生活。他应当引领读者穿过世俗生活的走廊,同时体验着精神世界的乐土。”李骞的诗歌正是在自南飞翔的舞蹈中朝着精神乐土的目标前行的过程。所以,他才能以二十五年的时间坚持写诗,试图以诗来抵抗世俗生活对精神的侵蚀。这种坚持需要来自心灵深处的某种召唤,因为诗是“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它需要承担精神,以朴素的词语承担起灵魂的重量。
李骞自己对于做一名诗人,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这种职业不仅找不到领薪水的地方,还常常被正常人称之为‘疯子”。即便是这样,他却坚持着做一个“纯粹诗人”的梦想,因为他相信: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可以战胜物质、时间和岁月。正是这种超越功利的信念,成了这本诗集最基本的写作动力。
二
高原情怀是每一个身居云南的诗人无法逃避的选择。
对一名诗人而言,写诗的过程也是寻找和建立精神故乡的过程。这是诗人天生的宿命。诗人天性的敏感、多思使他们注定要比常人更多地承担起生存的问题和矛盾,一些诗人乐意追求用词语建造安放心灵的花园,让玫瑰盛开,听夜莺婉转啼鸣。但对从滇东北高原走出来的李骞而言,他的故乡不可能是玫瑰装饰的花园,而是荒凉、雄浑的高原、山野、峡谷、金沙江这些充满雄性气质的自然存在。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曾经用尽力气拼命挣脱这些事物的束缚,远远躲开它们,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诗人永远“在路上”,家园永远“在远方”。诗人海男说:“我曾经渴望在最远的地方有我自己的一间房子,而最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不得而知。”正是因为不知道“那间房子”到底在何处,诗人才会在大地上苦苦地追寻。而在经历了一番奔走、跋涉、寻觅之后,他才发现他一直逃避的东西是心灵深处最无法割舍的宝藏。一个人无论走出多远,永远走不出故乡包容的视线。于是,故乡成了诗人笔下咏唱最多的内容之一。
李骞也逃不出这样的宿命,在现实中他可以远离故乡去寻找理想和希望,但是在精神上他却无法与它们彻底绝裂,反而会时时停下脚步,以温情的目光抚摸那些曾经给过他温情或者疼痛的事物。回望家园,即是回望自己成长的精神土壤。诗人与故乡之间永远存在一条无法割断的“精神脐带”。它隐藏在诗人的心灵深处,提醒着他自己的根之所在。每个写诗的人都有一片自己的精神版图,无形地制约着他笔下诗行的前进方向。
所以,就不难理解李骞为什么会用很多笔墨来抒写“我的滇东北”,在他的记忆深处曾经“活命在一块茅草地/在打满补丁的荒滩上/踩一串浮浅脚印。”(《高原之南》)但他诗中的故乡已经远非实际意义上的故乡,不是一个具体的村寨或者一架具体的篱笆。而是精神空间
的深入拓展,其视野体现出雄浑的气魄。在《滇东北》这组组诗中,他的目光投注到峡谷、岩洞、五尺道、悬棺这些滇东北特有的古老事物上,对它们进行温情的抚摸,使诗人的主体心灵和古老的自然存在之间呈现出和谐的状态,从而创造出新的审美效果。透过跳跃的诗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诗人和这块土地之间的血肉联系,和外来者观赏的目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一块有痛感的土地,也是一块浸透深情的土地。那条割不断的“精神脐带”把诗人心灵的欢乐和痛苦展露无遗。而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归结到“家园”的情结上:
“在中国南部有一块叫滇东北的土地/那是我日夜思念又魂牵梦绕的地方。”
“躺进群山的胸怀/无意仰望璀璨的星空/一天一天打发朴实的日子。没有下酒菜/就走进大自然院落/羊群养在家门口/打死一头猛兽/就像射击栅栏里的一只母羊/接过祖辈传下来的土碗/坐在火塘边/就着老鹰翻飞的旋律/喝完一缸土酒/嘴唇涌向远边的港湾……”
“做滇东北人很快活/这是因为/家园都建在气势磅礴的乌蒙群峰上。”(组诗《滇东北·山顶上的家园》)
也许只有滇东北高原水土养育出的诗人才会以如此大气的视角来描绘故乡的壮阔。在外人眼中那不过是一片蛮荒、贫瘠、落后的土地,滋生的是愚昧与苍凉。而李骞笔下的高原却丰富、生动,展现了世代生息于此的故乡人鲜活的生命形态。令人不禁想起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些被评论命名为“昭通作家群”的诗人中,没有人不对滇东北高原怀有深重的情结。因为那里是故乡是家园,是心灵永远无法挣脱的羁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生命中无法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是在表达的方式上,每个诗人都有其不同的审美视角。比如雷平阳的诗中,以执着的态度咏唱他“针尖上的欧家营”,关注一棵草、一只鸟,为故乡的“面目全非”而焦虑。李骞的彝族血统,加上青年时代的从军经历,使他的精神气质中多了些刚气和豪放。所以他的诗以其特有的率性,大气地抒写高原的壮美:“我们想念滇东北/这是因为/山顶上的高原埋藏着不屈的灵魂。我们怀念红土地/那是因为/云朵下的村庄生活着豪气连天的兄弟。”(《这片荒原·这片热土》)他是以放歌的方式对故乡进行巡礼。而他心中潜伏着的英雄情结则使他的目光关注点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往返。他歌唱的是“从不低头的滇东北”“出产英雄的红土地”。
这是典型的借诗歌形式让“精神还乡”。诗人的身体已经无法回到故乡生存,但诗歌的翅膀却可自由地飞翔于故乡的蓝天下,为它的雄浑壮阔而咏唱。李骞的诗在歌咏故乡的同时,暗含着为滇东北高原建立新的审美维度的愿望。透过苍凉和悲壮,他要用诗歌展示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不为人知的厚重底蕴。所以他在以高原、乌蒙、火地、迁徙为题的诗歌标题前面都冠之以“大”字,大的后面则蕴藏着深沉的痛感:“大高原”,拥有不为人知的孤独和清贫,“大乌蒙”则是“让人生生累死的大乌蒙”。“一生想征服乌蒙/一生都没有征服乌蒙”。滇东北高原正是以它的丰富博大和不可征服性,在诗人心中矗立成高大的雕像。这是一个爱恨交织的过程。
在歌咏高原厚重内涵的同时,诗人也为自己的心灵寻找到了依托的家园。滇东北高原,永远是诗人放牧灵魂的辽阔天地。“我的滇东北”既是充满地域性的诗意表达,又超越了单纯的地域特色,传达出某种令人感动的激情和精神。
三
诗人的精神气质源自于他的内心历程,而又制约着他对诗歌的审美取向。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却产生不出大致相同风格的诗。所以诗人于坚说:“诗是圣经。一个诗人就是一个上帝。”同样是滇东北高原上成长起来的诗人,有的耽于内部世界的行吟,有的注重外部世界的冲突,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前面说到,李骞的彝族血统和军人经历,对他的精神气质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他的诗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豪放风格。但是,对李骞这样以率性风格见长的诗人而言,他不会固守一个角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情怀。他的情感空间同样体现出丰富而立体的特色。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李骞不仅是一名诗人,他还对诗歌理论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曾经出版过几部诗歌理论专著。所以他对诗歌如何表达情感,有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从宏观的意义说,诗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就创作者而言,诗歌往往是内在情感的直捷诉诸。”从文体研究的角度看,“抒情性”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而抒情则离不开主体内部情感的表达。情感是诗歌写作的原动力,也是诗歌审美价值得以实现的主要依据。别林斯基也说过:“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无论诗歌潮流如何变幻,诗歌抒情的本质都不会改变。而抒什么情?如何抒情?则可以检验出一个诗人审美境界的高低。
《快意时空》这本诗集的写作宗旨是追求“快意”,追求灵魂和思维的放松,也最能检验出诗人心灵世界不为人知的真实与生动。走进诗集,也就走进了李骞丰富、驳杂的情感世界。一部分诗歌中可以感受到他似乎与生俱来的野性与豪放。这既来自于滇东北山水的养育,也包含有彝族血统中酒与火燃起的激情。他的视线所至多是大自然中雄浑壮美的事物,在放牧灵魂的同时抒发着豪放的激情。尤其在那些描绘东北高原景色的诗歌中,这种激情得到了酣畅的表达。诗人的主体情感在故乡的大地上游荡、汇聚,最后以喷发的形式奔涌而出:“在充满睡意的乌蒙山顶,猎捕山河湖泊的梦想/一种野性的刺激,在云朵之上的高原燃烧。”(《大乌蒙》)在这些诗中,诗人的情感呈现出丰富、立体、强烈的态势。并折射出因地域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感受:
“即使贫穷一生也懒得向富责低头/站在高高的峰顶,让大江大河从脚下流过/静听一次心跳,可以为爱唱一万首情歌/放纵一千次生命,却不会因失败而后缩半步/这就是大乌蒙,永不弯腰的大乌蒙。”(《快意时空·大乌蒙》)
要有强烈的诗情,才能形成诗之美。这种强烈的情感不是依靠词语的堆砌可以形成,它源自于诗人主体心灵对世界的深沉体验和感受。支撑起李骞诗中滇东北高原壮美景色的,是诗人像地火一样奔突的情感世界。换句话说,在永不弯腰的大乌蒙后面挺立的是乌蒙人永不服输的精神和傲气。它可以超越贫穷、失败,体现出豪放、浪漫的精神气质,生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沉的诗歌内涵使情感的抒发于豪放中透出大气和沉稳,而诗人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期待中的“快意”体验。
甚至,滇东北高原似乎还不够李骞纵马放歌,倾泄情感的江河。于是,便有了《彝王》、《圣母》、《创世纪》这几部长诗的诞生。它们代表着李骞诗歌的另一种审美追求。从内容上看,它们都是对古老的神话传说的改写,却又倾注了诗人对人类起源、历史变迁的诗性思辨。李骞在诗集的“自序”中曾经坦诚自己做不了一个纯粹的诗人,但却用真正的诗人标准
来要求自己。而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会仅仅关心个体的存在,他的目光和视野会努力超越现实生存,投向更辽阔的空间,上穷碧落下黄泉,去追寻智慧的源头。这是诗歌精神的体现,也是诗人精神世界向纵深的拓展。诗集中选取的只是这三首长诗的部分篇章,但足以领略其风格特色,从中感受到诗人如火的激情在燃烧,自由放飞的想象力则如鸟的翅膀一样扇动出浓郁的诗意。
《创世纪》以西方《圣经》故事为题材,放飞想象进入人类的远古历史,对“神”的力量和形象进行诗意创造。这是“圣经”的故事,这又是充满诗意的改写,是现代意识观照下对神话的新审美。《圣母》是对人类始祖女娲的赞颂。《彝王》是“一个远古传说的偶像”。在这几部长诗中,李骞的想象力仿佛插上了翅膀,驾驭着奔涌的情感,在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传说之间自由驰骋。他所要赞颂的是人类共有的英雄情结和充满神性的创造力。比如《彝王》中的彝王这一形象,既源自神话传说,又是彝族人精神的象征,和彝族历史上的迁徙、征战密不可分,是无数彝族部落英雄的化身。一旦主体情感和仰慕的对象在时空中相遇,并碰撞出火花,诗人的情感便如江河之水一泄千里,体现出强烈的审美效果:“走出来/英雄的彝王/从神话中灿烂发光地走出来”。“河岸的百褶裙百折千回/为你绽开幸福的花蕾。”在犹如交响乐般的诗歌节奏中,完成了彝王高大形象的艺术创造。
在远古历史、民族神话、壮阔的大自然面前,李骞的情感世界得到了酣畅的宣泄。并因为主体和客体的有机契合,使这部分诗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效果。
但是,诗人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样的。前面提到的这些诗和现实世界之间多少有些疏离的迹象,是对现实的超越和升华。而诗人不可能永远沉浸其中,他还需要面对现实生存中的各种问题。李骞没有回避一个诗人需要从天空回到大地,从理想回到世俗的问题。在《快意时空》中他专门用了一个小辑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间距”,将诗的翅膀收拢停歇在树的枝头。和前面那些穿越历史时空的诗歌相比,这些诗更贴近现实生存,体现了诗人在世俗生活中情感的诸多侧面。
他借彝山特有的苦荞、甜荞抒写对故乡姐妹的疼爱,写得细腻而柔情无限。他在诗中回望贫苦的乡村母亲、故乡的初恋情人,借“梅”书写爱情的缠绵。甚至把目光投注到一棵青菜白菜和卖菜女孩子的身上。在这些诗中滇东北高原远远退守为遥远的风景,生存的现实空间得到有效放大和凸现。可以看到诗人在大地上行走的足迹,聆听到他内心的“独自”。面对故乡情人,诗人内心有歉疚:“虽然我曾经背叛你/背叛之后却是生生的依恋。”面对大地上的落叶,诗人看到的是生命的轮回:“落叶不是落叶/落叶是飞不动的病鸟。”面对田野上的庄稼,他以喜悦的心情细细描绘着苞谷、高粱、大豆、土豆这些事物,抒发出自心底的朴素感情:“我是吃苞谷饭长大的男人/遇见苞谷我就叫一声养我的娘。”李骞在序言中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诗歌中的感情是纯净的。”这一辑回到大地上的诗歌中,诗人敞开心灵,不加修饰地展现出一个本真的自我,其情感单纯而朴素,自有一种纯静的美感。
当然,世俗生活并不都是全部由美而构成。一个真正的诗人能够书写真善美,也应该敢于直面生活中的矛盾和丑恶。爱与恨的力量同样可以产生审美的力度。在《现代白话实验诗》这一组诗中,李骞比较集中地展示了世俗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死亡的阴影飘散,沉闷的生活让心灵沉沦。诗人忍不住在诗中发出质询:“谁是我/我是谁/我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我默默独居/我不是我。”而面对生活中的告密者、叛徒、小丑,激愤的他用略显直白的语言表达着内心的鄙视。他很无奈地发现:“这些年代/人人心中有条虫/性格变得狭隘。”这一组白话诗正好切合了诗意匮乏的城市现实生活。
一个诗人情感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他诗歌的审美品质。李骞追求的“率性而为”,正好为他诗歌的情感表达拓展了广阔的空间。由广阔到细致,由粗犷到温情,呈现出刚柔并济的美感。
四
诗是需要技巧的。尤其是现代诗,在方法和技巧上的花样翻新简直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形式技巧最终也是最高的目的就是否定自己,成为有内容的形式,在内容中消隐自己。”对李骞这样追求诗歌写作“快意”的诗人来说,二十五年的写作训练和对诗歌理论的研究当然使他对诗歌的方法技巧有自己的理解,《快意时空中》的“白话方阵”这一小辑就是他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所进行的诗歌写作上的试验,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后朦胧诗”的反动。希望以直白的口语形式传达心灵深处的所思所想。尤其在表现个体生命的自觉与内省方面,“白话”诗确实有它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在诗人眼中,现实生活原本就是苍白而缺少诗意的存在,到处是钢筋水泥的建筑,人人心里长了条虫,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使生存变得充满荒谬感。所以在《作品2号》中,他直白地写喝酒的过程,写酒醉的场面,目的是要传达出毫无诗意可言的生存无奈与沉闷感。《作品12号》写感冒的病理感觉,更是有自然主义的特点。这组诗中充斥着对生活的厌倦感和无聊的情绪,“时间被切成两半/一半属于英雄/另一半属于狗。”通过生活平面表象的透视,诗中所要传达的是当代城市人的非诗意生活。
但是任何技巧都是为内容服务的。在李骞歌咏滇东北高原的其它诗作中,则体现出对诗意的大胆追求。高原、历史、故乡,都是滋生诗意的最好土壤。他从中提炼了许多颇有韵味的意象来传达主体情思。在这些诗中宏大的意象有:峡谷、金沙江、五尺道、悬棺等自然存在,传达出高原厚重的意蕴。具体的意象有:苦荞、甜荞、蝴蝶、鸟、蜜蜂、树等微观的事物。人物有故乡的父亲、母亲、姐妹、情人,牵动着诗人的思绪。这些意象共同创造了滇东北高原丰富多元的审美意境,使高原呈现出生动、感性、欢乐与痛苦并存的立体特色。
同时也应该看到,追求率性和快意的写作固然有它的长处,能充分激发诗人的情感,挥洒自如地绘出诗歌的画卷。但是,过分强调“快意”也会带来一定弊端。比如对语言的锤炼,对诗意的提升,都需要诗人投入更多的心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固然写不出大气磅礴的诗,但却能精雕细刻出艺术的精品。我们需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大气,也欣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细腻。对一位诗人来说,大气和精致是不可缺少的两面,若都能兼顾,自然是好事。
生活在一个众声喧哗、欲望横流的时代,李骞却能在诗歌阵地坚守多年,精神非常可贵。这种坚守完全源自于灵魂深处的某种呼唤。他执着的态度和艺术上豪放率性的追求,也为他的诗歌带来独特的个性和风格。作为现实中的一员,他只能双脚站在大地上生存;作为一位诗人,诗歌却给了他灵魂在天空自由飞翔的可能。在飞翔中感受“快意时空”,将诗歌写作进行到底,这将会是李骞永远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