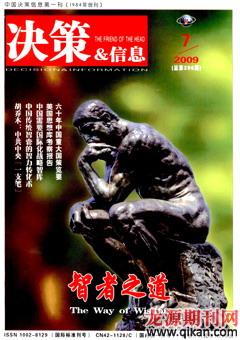三门峡工程决策失败之教训
张 伟 沈 四
决策,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公共工程的决策,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需要严谨的科学论证,需要决策者权衡利弊、排比得失、趋利避害,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需要断然摒弃一厢情愿、好高鹜远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让决策更科学,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论证机制,真正做到兼听则明;怎样通过民主的方式防止决策脱离理性的轨道,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门峡工程的起因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于同年底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纸面上的规划令人兴奋: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度,总库容360亿立方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功于此役。此外,巨大的灌溉、发电、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前景,也令人惊喜。
1955年,水利部召集专家学者讨论这一计划。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4月,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远远超过350米规划中的60万移民。此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黄万里郑重地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要点为:一是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即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二是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水位将提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三是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他们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可叹的是,这种呼声被漠视了。1957年6月10日~2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给两个月前正式开工的三门峡工程出主意,想办法。准确地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外,大部分人不说话,其余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认为“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最后这一条与会者全都同意了,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主持施工的“水利专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6个施工泄水洞全部堵死。
三门峡工程的结局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同年9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就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移民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而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迅速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减产。这一年,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大淤成灾。
1962年3月,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成了名副其实的“悬河”。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而把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披红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丧失了用武之地,只好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漂”。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
1968年,第一期改建刚刚结束,第二次改建就于1969年接踵而至,所有的争论至此已经变得毫无意义,“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以备将来排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1000万元,又将1~5号机组进水口高度由300米降到287米,泄洪排沙。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与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无法实现。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以坝身百孔千疮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代价,暂时解决了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按照一些水利专家的看法,原指望带来黄河清水长流的三门峡工程,已经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
三门峡工程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29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十几次迁移,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三门峡工程直接的经济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整个三门峡造成的损失有人估算不下百亿元。
三门峡工程的决策缺陷
苏联境内很少有泥沙量大的河流,他们的专家缺少泥沙河流治理经验,所以他们的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事实证明,这一方案是脱离黄河实际情况的。
大凡错误的决策,劳民伤财,贻害无穷,而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形成的正确决策,则产生福祉,利国利民,它来源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正是三门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所严重缺乏的。人们轻信甚至盲从无治沙经验的苏联专家的说法,先入为主地论证工程的可行性,工程存在缺陷后又缺乏有力度的纠正。更要命的是,对反对者的忠告置若罔闻,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宽容反对意见的胸怀,造成了权力对科学的排斥和压制。
中外科学史的许多事例都反复证明:科学的真理具有独立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之外的属性,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黄万里的遭遇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判断,这就提醒执政者和社会各界必须重视少数人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异见”,“另类”的声音或许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或对更多可能性的预见。在这种声音面前审时度势慎重行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人为地回避、忽略乃至压制这种声音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正是黄万里们出于爱国热忱,提出一条条在相关领域有相当分量的反对意见,才能为决策者们提供宏大的视角和多维的思路。我们理当为这种反对声音叫好。
中国自1996年开始实行听证会制度,至今已经十余年了。遗憾的是,中国的听证制度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其中的原因是:听证会不由公正中立机构来主持,使听证会先天不公正;听证会参加者不按程序公正法则产生,使听证会不可能形成符合社会多数人意愿的公正结论等。有鉴于此,在进行重大问题的决策时,一定要汲取这一教训,应委托中立机构主持听证会,并且合理分配参加者人数,确保可能或潜在的利益受损者能够达到一定比例,使决策能够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在决策问题上,当政者应自觉摒弃家长制、个人专断的不良作风,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政府投资决策民主化成为一种制度。倘能如此,无疑是观念上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