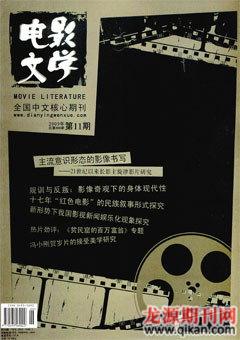电影《苏州河》上海城市书写解析
花艳红
[摘要]电影《苏州河》的表现方式不同于“怀旧”上海电影对上海城市符号式的书写方式。影片通过纪实镜头与虚构叙事的交织,表现当下的上海城市形象。纪实的镜头与虚构的“传奇”叙述之间形成的城与人、人与人之隔是对当下城市的深度解读。抛弃集体记忆对上海城市符号式的注解,上海在这样的诠释中剥离传统海派赋予它的传奇外衣,展现出其在当下独特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上海;城市;传奇;纪实,虚构
从20世纪80年代的《倾城之恋》到90年代的《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画魂》《人约黄昏》《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风月》《海上花》,到21世纪的《花样年华》《半生缘》《美丽上海》《长恨歌》乃至《色·戒》等,来自不同地区的导演在叙述“上海”时似乎达成一种默契,无论是题材还是人物都倾向于“旧”:老弄堂里穿梭着衣着精致的少妇,上演或哀怨或悲凉的悲喜传奇。在这个几乎成为定势的城市传奇模式中,2000年娄烨导演的《苏州河》无疑是个另类。直面今日城市之“新”,纪实镜头与虚构叙述所表现的是另类的上海传奇。
一、纪实:城市的光影声色
“我经常一个人带着摄影机去拍苏州河,沿着河流而下,从西向东,穿过上海。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故事,记忆,还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积在这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可是还是有许多人在这里,他们靠这条河流生活,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在河上,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看的时间长了,这条河会让你看到一切,看到劳动的人们,看到友谊,看到父亲和孩子,看到孤独,我曾经在一条泊船上看到过一个婴儿的诞生,看见过一个女孩子从桥上跳下苏州河,看见一对年轻恋人的尸体被警察从水里拖起来……关于爱情,我想说,我曾经看到过一条美人鱼,她坐在泥泞的河岸上,梳理着她金色的头发,别信我,我在撒谎……”
叙述在苏州河上徐徐展开,镜头随着旁白快速切换:穿着简陋的船工,河边、船上到处乱跑的野狗,斑驳的水泥桥梁,为生计忙碌的芸芸众生,岸堤上肮脏的青苔,水面上漂浮的垃圾……远处是隐约可见的东方明珠和那些被冠以上海传奇的古旧老建筑,近处是张望着“叙事者”好奇的眼睛。这让人想起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也是那些好奇,漠然、紧张、谨慎的眼睛。那些“眼睛”大多穿着朴素,面孔饱经风霜,这是整个影片的环境素描,与许多作品竭力营造的精致上海截然不同。这里可以比较1998年侯孝贤根据韩邦庆小说改编的电影《海上花》。影片中所有的镜头都是室内景,精致的清末民初服饰和大量古董家具摆设,人物常手捧水烟枪,同时辅以大量的人造光源,营造出“经典”的旧上海形象。《画魂》《风月》《长恨歌》等甚至是最近的《色·戒》都或多或少呈现这样的上海。尤其是《花样年华》。尽管其故事发生地是香港,但其中小雨润泽的青石板街道、合身的旗袍、买云吞面的优雅少妇被视为经典的上海元素。
《苏州河》却反其道行之。人们在肮脏的苏州河上生火、做饭、养狗甚至大小便。自然光下的灰色城市就是那个丑陋的“荒原”——上海。尤其是电影开始时“我”于城市行走,在墙上喷漆留下联系方式的场景,不由使人想起当下许多城市都可见的“办证”广告。墙壁、台阶、电线杆上到处都留有这样的黑色“牛皮癣”。灰色是最没有生命力的颜色,钢筋水泥又是极僵硬的建材,许多文人都回避这种形象的“自然”。导演却选择在毫无掩饰的自然光下,赤裸裸地表现城市的“真”:“你要是不喜欢我拍的你,可别怪我。我早跟你说过,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苏州河上的叙事采用原生内视觉聚焦,仰视的姿态显示了如叙事者一样生活在苏州河上“看的时间长了”的人们观察这个城市的方式,也是这些城市生命存在方式的隐喻。“我”在仰视中远观这些沉重的灰色都市底盘,下面则是川流不息的苏州河水。生活在船上、岸边、码头的普通人,他们一如苏州河般柔弱,却能承载城市的重负,随着苏州河水飘荡,不远处是广阔的大海。他们不能到达城市的上空,用骄傲、冷漠、有优越感的眼神俯视城市,不能享受城市带来的先天便利。城市依靠他们、利用他们却疏远他们。他们生活在街道以下,城市与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隔阂。
灰色调的光影中,人物是开放的。“怀旧”的上海往往被符号化,剧中人物也常常无法逃脱城市标签对角色的约束,“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中,旧上海通常都是西化的、陌生的、异国情调的、色情的、女性的、性事上不贞洁、道德上也是可疑的。”无论是王娇蕊、自流苏、王佳芝或者是王琦瑶,都要面对这些文化符号对她们的形塑,并竭力认同、维护。尽管每个人有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但人物的性格塑造却惊人的相似,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脸谱。《苏州河》则竭力摆脱这些符号可能带来的文化想象。去掉沪语,去掉昏黄灯光下精致的老式家具,去掉盘得一丝不苟的发型,去掉合身而优雅的旗袍。镜头下是说着满口京片子,散乱着头发,穿着恶俗皮外套、吊带衫、高底鞋的城市女子,行走在到处是坑洼、泥浆的苏州河畔。带上头盔驰骋在这个城市污浊的小巷深处。观众无法预知人物的行为方式,无法假设故事的结局,人物叙述属于自己的“传奇”。
这些“传奇”没有“上海”的约束,在哪个城市都可以发生。这就是现实上海的真实处境。尽管苏州河是上海的标志性河流,但离开了苏州河,“传奇”可以被重复。这是叙述者对渐渐消失的城市文化特征的反思与表达。生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始,也可以结束。空间失去了其特定性和惟一性。这是对传统上海传奇的颠覆性描述,也是对当下上海城市的认知与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颠覆不仅呈现在光影里,在配乐上也较有想法。表现上海的电影常使用悠扬、含蓄、回味的怀旧风格音乐。《花样年华》就大量使用三拍为主的舞步音乐,“强弱弱”的节奏让受众感受到华尔兹般的回旋。这种乐感是收敛、有节制且精致的。而《苏州河》中惟一能彰显“上海”的歌曲是《夜上海》。靡靡之音在电影中盘旋,镜头下却是传呼机响过后美美嚼着口香糖(典型的美国化随意),在夜色中大步行走的场景。灯光下黄色乱发的女子张扬地在大街上面对镜头挥舞她的青春与笑容,不时抽上一口既而冲着镜头吐出烟雾,甚至吹出硕大的口香糖泡泡,远处是虚化的、模糊的闪着红绿霓虹灯的城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也有这样一段《夜上海》,歌女们浓妆站在舞台上跳踢腿舞,尽管意味粗俗不堪,却是对《夜上海》的标志性解读。《苏州河》的诠释却充满了张力,“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影像表现迷离却不华丽,美美在夜上海的放纵与粗鄙正是对《夜上海》所代表的海派文化的悖反。
大多数时候影片根本不使用音乐,只是通过自然声来充实屏幕。最常听到的是汽车的汽笛声、摩托车的马达声、不绝于耳的说话声和苏州河上的风、水带来的环境音。这让人想起张爱玲笔下的“市声”。许多导演在选择张爱玲作品作为拍摄题材的时候都尽量避免这种“市声”,因为这只能听到城市生活的嘈杂和粗鄙。《苏州
河》对声音的处理一方面忠实于影片本身的纪实效果,也努力抹掉精致所赋予这个城市的标签。
二、虚构:对“传奇”之否定
表面上看《苏州河》是一个离开一回来~再离开,寻找爱情的老套故事。牡丹与美美的形似乃至最后的“相逢”宛如基斯洛夫斯基《维罗利卡的双重生活》。美人鱼的象征和最后的殉情结周似乎更表明了“传奇”的本质。“传奇的诞生,有赖于超异的空间,超常的人物,超凡的举动。而现代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庸常化,以及现代统治管理的日常化和体制化,使得人类那些毫无生趣和创造性的个体越来越陷于被约束被规范的境地。这就是无形和有形的规训全方位地吞蚀着生命个体原本自由的空间与时间的20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人类的传奇即使存在,也只能存在于想象力的世界,存在于艺术大师的虚构和叙述中。”传奇本身不具有真实性,面对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时导演总习惯选择爱情“传奇”作为题材,以“现代”上海抵制当下世俗与庸常之上海。在讲述这些“虚构”影片时总竭力表现故事的“真”,以证明人物、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这种焦虑来自文化“消失”与“重写”间的冲突。
《苏州河》并没有到样新旧之间的焦虑,它对爱情的表现尽管保留了“传奇”的表象,但深层次上对“传奇”的否定彰显出导演对主流书写模式的颠覆。
“我曾经在一条泊船上看到过一个婴儿的诞生,看见过一个女孩子从桥上跳下苏州河,看见一对年轻恋人的尸体被警察从水里拖起来……关于爱情,我想说,我曾经看到过一条美人鱼,她坐在泥泞的河岸上,梳理着她金色的头发,别信我,我在撒谎……”
“我在撒谎”为这个关于美人鱼的传奇定性。美人鱼在影片中是个非常独特的意象。这个形象来自欧洲传说,一方面它代表绝望的爱情。牡丹得知马达利用爱情实施绑架,最终手握美人鱼跳下苏州河是对该隐喻最有力的注脚;另一方面,美人鱼是现代酒吧的宣传照。是在简陋的化妆间,脱下吊带衫和黑色丝袜,穿上缀着闪亮珠片的戏服,套上金色假发的美美。牡丹手握美人鱼玩偶的清纯与对理想爱情的憧憬被彻底击碎。化成美人鱼寻找爱人在现实世界中不过是穿着戏服在纷扰的酒吧金鱼缸里表演。理想与现实如此巨大的冲撞以理想的支离破碎收场。虚构的无力与真实的强大在这里被清晰地表述出来。
正是因为一句“变成一条美人鱼来找你”,马达不断寻找跃下苏州河的牡丹,影片最终含蓄地交代马达找到了他的爱情。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寻找失去爱情的凄婉故事,但影片结束时,导演却用雨中马达与牡丹面目模糊的尸体对这一“真”提出了质疑。已经分辨不清面目的马达与牡丹是否真实存在过?而那个被叫去认尸的“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出现正面影像。“我”是马达故事的参与者、见证者,马达死后“我”又为马达验明正身。但这个证明马达存在、证明马达传奇的人却是无名无貌的缺席者——“我”是不存在的。影片设计了这样一个叙事圈套论证“传奇”之伪的命题。
此外还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我”在讲述爱情传奇时反复出现“也许”,表达叙事者的不确定和质疑。对传统社会的人来说,大多数人生活在已知、熟悉的世界。他们彼此了解认识,人与人关系是确定的。而城市则不同,偷摩托车、送货、绑架,人们穿梭在这个有着一千多万人口城市的各个角落,城市赋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人与人之间的隔与人与城的隔一样深刻。马达与牡丹尽管相爱,但牡丹最终要面对的是马达成为绑架她的帮凶;萧红与老B尽管彼此信任共同犯罪,萧红最后的命运却是被老B捅死,甚至美美对马达的信任,也得通过马达与牡丹在雨中凋零的生命才能得到最终确认。人物经历是从熟悉到陌生的过程。牡丹最后从外白渡桥上背身跃下的命运是对这种“隔”最后的藐视和挣扎,但宽阔的河面,奔流的河水、瞬时消失的身影与牡丹并未找到的尸体暗示的却是人反抗的无力。
城市带给人的是疏离与分别、理想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反复穿梭和最后回归苏州河最终奔向大海宿命式的结局。马达与牡丹并没有随着苏州河漂流至海,他们不属于真实的开放的河流,那些爱情传奇是假的。
纪实的镜头与虚构的叙述之间形成的城与人、人与人之隔是对当下城市的深度理解。没有了集体记忆对上海城市符号式的注解,这个有条苏州河的城市到底是什么?上海在这样的诠释中剥离传统海派赋予它虚构的传奇外衣,展现出其在当下独特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