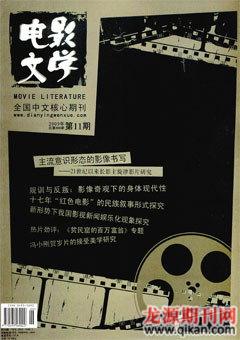试论《宠儿》中历史记忆的意蕴
彭艳秋 吴庆宏
[摘要]托尼·莫里森的巅峰之作《宠儿》是一部旨在揭示奴隶制精神贻害的小说,其着重表现了奴隶制对已获自由之身的黑人心理所造成的严重伤害。1998年《宠儿》被搬上银幕,著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饰演塞丝。故事中的每一个黑人都深陷在历史记忆的阴影里,罹患了记忆缺失症,承受着难以言述的心灵创伤,在痛苦与彷徨中苦苦挣扎以获得一席生存之地。莫里森透过自己的笔触挑战全民族的失忆症,撩开记忆的面纱,填补历史的空白。
[关键词]莫里森;《宠儿》;创伤的记忆;历史
1993年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凭借其第五部长篇小说《宠儿》一举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成为当今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宠儿》是其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一经问世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在1998年被搬上银幕,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饰演塞丝。莫里森从黑人的创伤和记忆中揭示出奴隶制的残酷本性,透过自己的笔触让世人了解真正的黑人历史,给予黑人同胞以鼓舞和希望,让他们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记忆之痛
众所周知,美国黑人饱受了奴隶制的折磨,当今社会的种族歧视与争端也可以从奴隶制中找到源头,几乎每个黑人都在有意无意地试图回避那段屈辱的历史,正如莫里森所言:那段历史《宠儿》中“小说人物不愿回忆,我不愿回忆,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不愿回忆。我是说这是全民族记忆缺失症。”
然而一个民族如果想要忘记过去,那就无异于抹杀了自己的过往,抛弃了民族的文化,毁灭了一个民族未来的希望,试问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又如何在这世界上立足呢?须知历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积淀,是一代代人经验的传承,如果缺失了民族的历史也就等于失去了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从而极易迷失自我。
《宠儿》中的每个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肉体和心灵创伤,于是一心想要忘记奴隶制带来的痛苦记忆,但愈是想要忘记却反而愈是滑向记忆的深渊。所以说逃避记忆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与其要日日夜夜遭受想忘而不能忘的折磨,还不如索性正视奴隶制,揭开记忆的伤疤,重新构造黑人的民族历史。作为一名拥有高度民族责任感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得她不但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常人所忽略的事实,填补历史的空白,而且更能够以其细腻的笔法省视黑人民族的整体命运,为黑人同胞修建起一架通往幸福彼岸的心灵桥梁。
二、黑人民族的创伤性记忆
《宠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关于黑人奴隶生活的创伤回忆。作为现代精神心理学的专用名词,“创伤”(trauma)指的是那些导致严重的身体伤害或使精神思想上反复出现闪回、噩梦等的突发事件。美国心理分析家Judith Herman在《创伤和康复》中指出,“由于创伤经历留在受害人大脑里的记忆有别于普通记忆,这种非正常记忆会以闪回和噩梦的形式占据受害人的意识;同时,由于表面上毫不重要的提醒物会引发记忆,一个看似安全的环境对创伤幸存者来说可能会充满危险。”
《宠儿》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拥有着不可言述的历史记忆,其中女主人公塞丝所遭受的痛苦尤甚于其他人。借助于书中人物的内心独自或对往事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回忆,折磨着女主人公塞丝的痛苦往事便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塞丝完全生活在由往事控制的世界里,没有现在和未来,她生命的天空里笼罩的是创伤和压抑而非自由和幸福。18年前的杀婴往事,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她,令她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往事的回忆之中。虽然塞丝一直在努力尝试忘记过去,忘记在甜蜜之家的日子,但遗憾的是她却无法摆脱过去的梦魇,当她专注于某件事的时候,比如正匆匆穿过草地,赶到水井边洗掉腿上的春黄菊汁,“猛然间,‘甜蜜之家到了,滚哪滚哪滚着展现在她眼前,尽管那个农庄里没有一草一木不令她失声尖叫,它仍然在她面前展现无耻的美丽。它看上去从来没有实际上那样可怖,这使她怀疑,是否地狱也是个可爱的地方。毒焰和硫黄当然有,却藏在花边状的树丛里。小伙子们吊死在世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
《宠儿》中有许多关于塞丝对昔日创伤性经历的自发性回忆。在奴隶庄园她被“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强行按倒在地而挤走奶水,后背被鞭子抽打得皮开肉绽的痛苦。如果说塞丝后背的伤疤是塞丝背负的有形的创伤印痕,那么塞丝在偶尔偷听到“学校老师”正在给他的两个侄子上课,指导他们把她的“人的属性放在左边”,“动物属性放在右边”时所经受的灵魂上的震撼则是她所承受的无形的心灵创伤。总之,无论塞丝如何尽力把每天的生活看做是“击退过去的严肃工作”,她都无法避开奴隶生活的创伤和屈辱所带给她的回忆。“过去的一切都是痛苦,或者遗忘。她和贝比·撒格斯心照不宣地认为它苦不堪言。”
塞丝的这些自发性回忆时常会出现,困扰着她那本已千疮百孔的灵魂,在保罗D告诉她黑尔看到她奶水被抢走后崩溃的情形时,她那颗饱经沧桑的心也在面临着崩溃的边缘。此时她恨不能抹杀掉过去所有的记忆,然而越是想拼命忘记的却反而记得越清晰。她对自己的记忆力无能为力,她痛恨自己的大脑,恨它“为什么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呢?不拒绝苦难,不拒绝悔恨,不拒绝腐烂不堪的可憎的画面?”虽然塞丝想忘记过去,操心未来,可是“她的大脑对未来不感兴趣。它满载着过去,而且渴望着更多的过去。”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塞丝就是由于过去创伤性的经历造成的影响,对现在和将来都不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深渊中。
对于奴隶生活,不但是塞丝和贝比,经历其中的每一个黑人都深受折磨,即使在奴隶制废除之后还很难恢复正常,黑人的精神上永远也无法摆脱奴隶制的戕害。老斯坦普佩德的衣袋里就一直带着一个黄缎带,那是他从一个被人蹂躏之后残害的黑人女孩头发上捡到的,多年以来一直带在身上。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那些难以计数的悲惨往事。保罗D所经历的更是令人难以想象。“猪瘟、铁嚼子、微笑的公鸡、火烧的双脚、大笑的死人、咝咝作响的草地、雨水、鬼一样惨白的楼梯、苦樱桃树……”在这一切之后,他就把过去所有的事情都封在了胸前的铁盒子里,任谁都不能让他再打开。
三、用记忆来填补黑人历史的空白
非洲裔美国黑人被认为是一个没有自己完整历史的民族,他们的祖先被迫远离故土,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大陆,并且饱受了殖民统治的摧残和折磨。而作为主流的美国白人文化霸权又扼杀了黑人的历史话语权,在白人统治的社会里黑人没有独立的话语权,好像是罹患了“民族失语症”。因此美国黑人若想重建民族的历史,就必须解构曾经被掩盖、甚至被歪曲的奴隶制历史记忆,在白人文化占主流的社会中重新争得自己的话语权。
《宠儿》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深受过去记忆的折磨,
而这被压抑的记忆却能真实地再现他们的心理创伤,揭露那段深埋于白人文化土壤之下的黑暗历史。对于黑人的屈辱历史究竟是需要回忆,还是必须忘却;需要压抑还是要努力发掘;需要掩埋还是需要再现。莫里森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让那段屈辱的历史重见天日。她在作品中展示了本民族伤口的创痛,揭示了黑人的苦难记忆,指出了黑人民族文化身份缺失的现实,为黑人的自救提供了希望。非洲裔美国人只有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正视那段持续了300年的苦难史,才能从中汲取力量以治愈黑人民众的历史创伤,重建民族意识。在这里,每个黑人的个体记忆汇合起来就构成了黑人的集体记忆,从而重新构造黑人民族的历史。在这里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忘记;掩埋经历是为了更好的挖掘;控诉罪恶是为了更好地拥抱未来。作为一位有着洞察力和前瞻性的作家,托妮·莫里森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历史潮流,并以文学这种独特的个人表达方式帮助黑人民众修正历史记忆,治愈历史创伤。
《宠儿》就是深埋在每个黑人内心的奴隶制的再现,她既是同胞们努力压抑的创伤,同时也是他们必须要面对和驱除的可怕记忆。不过“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肯开口,肯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不想谈论,他们不想记得,他们不想提及,因为他们害怕”。莫里森在小说中使用了“重现回忆”这一特殊的词。“重现回忆”可以理解为再现过去的活动。而有意识的再现意味着解构过去,重构现在。通过这种动态性质的“重现回忆”,黑人最终得以摆脱过去事件的阴影,治愈心理创伤。在塞丝看来,“有些东西你会忘记。有些东西你永远也忘不了。地点,地点始终存在……不仅留在我重现的记忆里,而且就存在着,在这世界上……即使我不去想它,即使我死了,关于我的所做、所知、所见的那幅画还存在。还在它原来发生的地点。”“更要命的是,如果你去了那里——你从来没去过——如果你去了那里,站在它存在过的地方,它还会重来一遍;它会为你在那里出现,等着你。”也就是说奴隶制虽然已被废除,当年杀婴的现场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后人仍然能够通过别人重现的回忆再次经历当年的场景,重新感受奴隶反抗所带来的震撼。
正是因为深谙种族主义的历史永远无法完结,莫里森的作品拒绝掩饰非洲裔美国黑人的那段历史的伤口,黑人的肤色就展示着民族的历史和苦难。每一个黑皮肤的人都无法逃脱历史,他们的黑皮肤将永远显示着这段历史。他们的个人记忆也不得不接受这些伤疤带来的隐痛。种族受难的记忆对黑人个体看来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无法在自己的记忆中被修复或删改。因此莫里森才借助于“重现回忆”的艺术手法使读者对过去的奴隶制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让世人对那段深埋在记忆最深处的奴隶制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让黑人同胞洞察本民族的历史,重构黑人文化身份。
四、结语
奴隶制是美国历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面,但是美国社会并未能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陈列证物的历史博物馆中,黑人在奴隶制时期的悲惨经历都未能如实得到反映。白人不愿回忆是不能坦然面对过去的错误,黑人不愿回忆是无法承受其所带来的伤害,因此莫里森将其称之为全民族的记忆缺失症。黑人只有正视过去的惨痛经历,直面奴隶制这段黑暗的历史,才能够最终摆脱过去,获得身心的自由。所以回忆不单单是为了黑人,同时也是为了白人,只有黑人和白人都意识到历史记忆的重要性,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民族纷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正所谓追本需溯源。王守仁先生评论说,“只有健康的社会才能面对历史,正视历史,不管历史曾经多么黑暗;只有真正面对过去,才能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