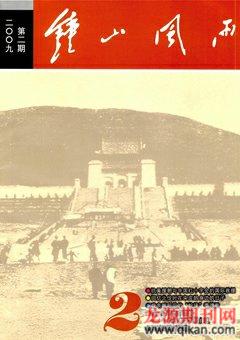南京大学40年前“跨国恋”悲剧始末
洪其庚
1968年7月,文革中的南京大学处在极度亢奋当中。一年一度的暑假已被取消,无休无止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天早上,大约6点半钟,师生多数都在食堂吃早饭,只见一女生从南园女生宿舍五楼纵身跳下,落到三楼时被电缆线猛地一弹,然后就重重地跌落到水泥地坪上,两个膝盖粉碎性脱落,鲜血及破碎骨肉喷洒到几米之外……
跳楼者名叫奚小柔,是外文系法语本科64届学生。落地时奚小柔头部伤情不重,尚处在半清醒状态,几个好心的同学把她送到附近的鼓楼医院。按说如果抢救及时,还有可能从死亡线上拉回一条性命,可那时医院内部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得知奚小柔“里通外国”,为表示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两派医生谁都不敢救治,害怕给自己招来“麻烦”。在家长的一再哭求下,一名护士“冒险”用纱布把奚小柔的膝盖脱落处简单包扎了一下,除此之外其它什么措施都没有。奚小柔因伤痛难忍,昼夜呻吟,几天后终因失血过多,眼睁睁“不治”身亡,时年仅23岁。
奚小柔是南京市人,家住玄武区一枝园。1961年考进南京九中高中部,和笔者系同班同学,1964年考进南大,和笔者碰巧又是同班。正因为有两次同班的“学缘”,再加上笔者有机会接触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人,所以对于奚小柔“里通外国”跳楼的前前后后,与其他南大同学比较起来,笔者知道的要更多更确切。
我们进入南大法语本科学习后,学校用月薪600元的高价聘来法国教师任教。该教师名叫阿尔维·德耐思,男,22岁,平民出身,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汉语专业。用现在的话说,德耐思到中国来任教,等于是出国“打工”,工资比在法国国内要高得多。德耐思任教一个多月后,同奚小柔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奚小柔的穿着也渐渐“洋”了起来,就连课堂上,德耐思提问奚小柔的次数也比其他同学明显多得多。
尽管这样,在那闭关自守的蒙昧年代,班上多数人对这种高度敏感且令人耳目一新的“动态”浑然不知,更不敢多想、多说,只有和奚小柔同宿舍的几个善于观察的女同学知道“底细”。她们觉得事关重大,就报告给了团支部书记,团支书又向上级作了报告。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知情人守口如瓶,比军事秘密还要秘密。岁月沧桑,人事消磨,有些“秘密”也许永远都解不开!
1965年寒假结束,班上同学都开学上课了,唯有奚小柔和一名姓施的女同学突然不知去向。同学们私下纷纷议论,有的说被提前调到外交部去了,有的说被调到东方歌舞团去了,还有的说被国家秘密机关调去搞情报去了……对这些传言,学校既不证实,也不否认。你猜来我猜去,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人再议论此事了。
几年后从大字报上得知,奚小柔“失踪”后,德耐思先是找外文系领导打听,问这问那,回答好像都是事先统一好的“口径”:“你回去安心教学,我们可以帮助查查,有消息时我们再告诉你。”等了一段时间,见没有消息,德耐思又去找校长匡亚明。他几次到校长室,秘书总是客气地告诉他:“很抱歉,校长出去(或开会)还没有回来,等校长回来你再来。”毕竟受爱的驱动,学校找不成,德耐思又去找南京市领导,市领导答复:“这是学校管的事,你还是去找学校。”德耐思还不甘心,又去找奚小柔家所在地的玄武区领导,区领导回答得很干脆:“我们区里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以后不要再来。”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965年6月,在南大招生办公室里,德耐思搞到一份全国高等院校系科目录,他灵机一动,采取“天女散花”战术,按照目录上的相关专业和地址,逐一向全国高校外语系寄发信件。到底是工夫不负有心人,远在重庆山区四川外语学院的奚小柔果然收到了鸿雁传书。这时,“陪同”奚小柔的施同学立即把情况报告给学院领导,院领导就请示国家教育部。部领导指示:1、把奚小柔软禁在学院内,平时不许随意外出,外出时必须要有人“陪同”;2、对她和德耐思的来往信件,校方安排专人随时发现随时扣压;3、切实做好安全和保密工作,以免造成国际影响。这样,由教育部牵头,会同南京大学和四川外语学院,还有省、市相关领导,层层设防,高度保密,奚小柔和德耐思的“跨国恋”被封得严严实实。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如同急风暴雨平地而起。随着北大校长陆平和南大校长匡亚明先后被揪出,各个高校都掀起了狂澜,斗争矛头直指校党委。接着“红卫兵”运动兴起,全国各地相继展开了革命“大串连”。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软禁中的奚小柔暂时得到了“解放”。同年10月,她天马行空,独自一人一举“串连”到北京,到了法国驻华大使馆大门口。不用说,她“串连”闹革命是假,想见见德耐思是真,但她不知道,此时德耐思早已回到法国。看到使馆门口笔挺地站着两个威武的持枪中国士兵,她张望徘徊了很久很久,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直到夕阳西下,“断肠人”才万分无奈地退了回来。
1967年8月,全国各省市领导班子相继被夺权,造反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难分难解,呈现出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机会千载难逢,于是奚小柔便从四川回到南京。当时我父亲(原在南京市委工作)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我本人则因参加过“保皇”组织而受到批斗,心灰意懒,也在家中做逍遥派。可能是“同病相怜”,也可能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奚小柔回到南京后不久即找到我家,老同学仅两年多时间未见,就被革命“革”得恍若隔世。此时的奚小柔已非往日的奚小柔,一脸憔悴,谈话中不时流露出惧怕和忧虑。我除了把她走后学校的情况告诉她外,又问她是怎样被秘密转到四川外语学院的,她说是教育部派人到四川联系安排的,名义上是“借读”,学籍和档案材料都还保留在南大。她去法国驻华大使馆受阻的经过,也是她亲口对我说的。谈话结束时,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双方都约定所谈内容“永远保密”。
谁也没有想到,1968年竟然是奚小柔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年。这年五六月间,随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进一步深入,置身家中近乎隐姓埋名的奚小柔最终还是被造反派揪了出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校园内外成了批奚的海洋,宣传车走街串巷,高音喇叭响彻石城上空,其规模和声势比之当年批判匡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里通外国”、“民族败类”和“女妖精”等辱骂重重地扣在奚小柔的头上。造反派成立批奚专案组,内查外调,上北京,去四川,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差一点就去了法国。他们以奚小柔“跨国恋”为证,断言从刘少奇到教育部到南京大学推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卖国投降路线,大字报上纲上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说就连“旗手”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文革顶级“首长”,都对南大揪出奚小柔给予了充分肯定。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事到如今,对于身处十八层地狱的奚小柔来说,要想自由,除了一死,别无选择。经过一个多月的看管和批斗,奚小柔四大皆空,万念俱灰。同年7月的一天早上,趁着两名看管女生去食堂买饭的当儿,受尽折磨和凌辱的奚小柔大步走到五楼窗口,头也不回,望也不望,纵身往下一跳……这一悲剧发生1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的中华大地上,“跨国恋”终于不再是一种梦想。
小柔同学,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