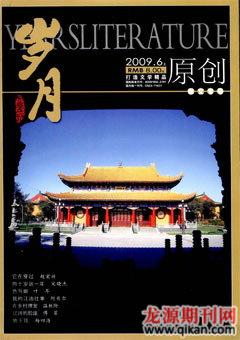采访笔记里的人物剪影
庞壮国
十年、二十年,一恍惚似的。捋一捋日子,我发现没干什么,采和写是我生活的主旋律。习惯在春天里给《岁月》杂志整点文章。《岁月》是我工作了八年的地方,屯亲的感觉啊。于是从采访笔记里,找了几个人物,组合一篇剪影。自己先读了一读,人生波浪般的片段,那些温馨的足迹,我能有机会用我的笨拙之笔变成文字,是天地人对我的恩赐。
徐信科荒野跋涉的诗意
如果说在当代能十年二十年地写诗,诗外的人会给诗里的人起俩名,大名叫傻子小名叫诗人。其实傻子在芸芸众生之中,早已经极端地贵族起来和帝王起来了。例如我们从来不管爱当众洗脚的皇帝、喜欢更新战略口号的首相、喜欢拆迁并新建的市长叫傻子,只管那骑着高马横着长矛穿戴铁锈盔甲攻击风车的堂吉诃德叫傻子。每当我在灰色的光屏上敲击上“傻子”两个字,就会在脑海中浮现一个乐天的怜悯的真纯的骑士,奔波在他的向往里,他会坚信他的所爱只在天涯,不料总是被现实土路上一群滚动的小猪撞倒在尘埃里。即便那样,我觉得傻子还是美丽的。
活着并且梦幻着,这是一种活得高贵而不卑微的质量。为此付出一生潦倒草率混沌迷茫,也没什么必要青衫掩面向隅而泣,当然也没什么必要横刀立马仰天大笑。静静地整理自己东写西写所积攒的心之履痕,把它们装订成册,坚决心疼地出版,然后哪怕把那些漂亮的书放置在自己梦的四周,总觉得值了。为此,我为傻子们想唱两句我少年时期经常唱着唱着就热泪盈眶的《航标兵之歌》:“前面的道路崎岖又漫长,谁能把英雄的步伐阻挡”。
我与徐信科相识是在1984年春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二十年后他跟我提及我俩相识的最初一瞬,在海拉尔城里的海拉尔河畔,我跟素不相识的他问起远在新巴尔虎左旗或新巴尔虎右旗的大庆地球物理勘探队。他说他就是那边勘探队的人,也要到前线去。当时三十四岁的我和当时三十三岁的他,就那样共坐在一辆东风十轮卡上,高高的舵楼里随草原的路怎样颠簸我们却感觉不到颠簸,有远航天涯之感。肩并肩八个小时,我俩,一切细节我至今都不记得了,唯有肩并肩航行的那种心旷神怡,永远嵌印在我的生命年轮里。
车到阿穆古郎(新巴尔虎左旗所在地),在一片小平房构成的镇子的边缘,一个大院子里,停车小憩,人说到徐信科的地震队还有三十里。大院子里的人拎来两个竹皮暖壶。摆上二大碗,哗哗地倒上牛奶加炒糊的稷子米加红茶的热汤,这就是名传天下的蒙古奶茶。我喝了两大碗,生平第一次痛饮蒙古民歌一般地被草原的情意所抚慰,一瞬间疲惫和劳顿全被洗干净了,心底畅快,好像早上刚刚迈出家门就碰上大晴天一样。徐信科却一口不动,用他的山东话垮啦吧唧地哇啦,意思是害怕奶茶。我愣眉愣眼地看他,心里纳闷,还有不喝奶茶的地震队书记么?还有不喝奶茶的战天斗地的荒野分子么?还有不喝奶茶的身在天涯的天涯人么?那一刻,我断定徐信科不是诗人。
在徐信科的地震队我生活了七八天。那七八天里发生的故事如今已经在记忆中飘逝。只清楚记得晚上睡觉不钻进蚊帐不行,三个呼伦贝尔的蚊子或一个半呼伦贝尔的瞎蠓就能装满一个火柴盒。还记得乌尔逊河春汛时节,六七斤的大鲤鱼都挤挤插插在浅水草塘上晾晒黑脊背,地震队可以抬着箩筐去拣大活鱼。
二十年后,仍然用满口垮啦吧唧山东话跟我说这说那的徐信科(他说话我听着莫不如说我是猜着),把他美丽地傻了二十年的责任都推给我了。他说若不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遇见我,他不会去写诗。所以他的诗集就该我来写序。我知道抬举人的方式有各种各样,但是抬举一个傻人,没有比徐信科更到位的了。傻傻惜傻傻比惺惺惜惺惺更确切。惺是清醒与聪明,惺惺与惺惺更多的是玩心眼、使腿绊、半道撤梯、落井下石之类,成语中有许多伪假辞条,惺惺惜惺惺就是。要更正,只能是傻傻惜傻傻。
徐信科牧放着诗歌白羊群,在心灵寂静的高原上,倾听来自他内心“咩咩无助的叫声”,“顿生寸寸怜悯的柔肠”,他感觉那些诗歌总是“在风雪交加的夜晚”,白羊一般“全身心地簇拥在我的身旁”,“用善良的目光无助地期待着”他的放牧和守护。《遥远的牧歌》以亘古的寂寥和连绵的震颤,让我知道“诗人”二字附上谁的身心和名字是极其简单的事情,只要那个人真心地而不是弄景地、真挚地而不是作秀地、真切地而不是卖乖地,从灵魂中流淌他自己的诗行就行了。
徐信科在一个A字型坟墓的外面,《梦醒黎明》,“给我从未有过的惊奇”,“看我入睡的人已经离去”,而他仍然感到“我似乎被爱过,在一种注视里均匀地呼吸”。苦恼也罢烦闷也罢自得也罢飘逸也罢,生活着并能够看见“一只硕大的苹果/在桌上凝聚光的信息”,是太容易又极不容易的一种境界。换句话说,太容易又极不容易,当一个诗人。
徐信科走在秋天,走在秋天的人方才知道《秋天的感觉》,方才知道“秋天也有宽容的一面”。“在雨后乡间被马车碾过的大街上/我多么希望被落叶绊倒在车辙里/当四周的喧闹都静下来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迎面走来一个正在怀孕的成熟女人”。我的心如果是丝弦,会被他拨动出微微轻声,那种轻声,用“惆怅”用“忧郁”来形容的话,都显得随便和省事了。
我读到徐信科这样的诗歌,怎能不承认徐信科是诗人?
但我说徐信科不是完全的诗人。他还是地球物理勘探战线基层的党委书记或者纪检委副书记。在广袤的土地上,人们用粗电线和细电线布成罗网,电线上缀满小红头蘑菇一样的东西,那些小红蘑菇的尖尖铁脚插在大地的皮肤上,不管大地母亲是否痛痒。然后再钻凿一眼眼炮井,塞上炸药,轰隆轰隆的炮声也不管大地母亲是否痛楚。人工地震制造的大地回声用电脑记录下来,然后专家们依据画满曲线弧线三角线的图纸去分析,再确定在大地的哪个要害部位钻凿更深更粗的井,好从大地母亲的血脉里汲取黑色的生命之泉。我们把这不可再生的生命之泉再送给飞机汽车化工厂去烧掉或者祸害。没人想到从黑色的生命之泉里提炼没什么实际用处的诗歌。评价这个人类的荒诞或实用或无可奈何的大举动,要等黑色的血完全枯竭之后,是我们身后几十代几百代人的事情,我现在反对或不反对都没用。
我肯定是把好事和好话不好好说。而徐信科是把好事和好话都好好说了。他诗集中满怀豪情大唱“我为祖国献石油”主旋律的诗篇,能给他佐证。我要是顺着徐信科去说,我不也能当书记了吗?可我不愿意在这点上再跟徐信科一样。左右我跟他一块傻了。再傻得都一样,该叫不傻的人们看着没意思了。
这样一来,年轻时扼杀过许多该当诗人却没当又诱骗过不该当诗人却当了的我。在这个上午,也只能为自己的深重罪孽又一次赎罪,赎罪的最简单方式——别人写诗我来写序。徐信科的意思就是他出诗集应该我出印刷费才对,出不起的话拿喜儿顶债,出不起喜儿的话写一个序得了。我无路可走,这
个上午就这么憋屈又愉快地敲击着,最后敲击的是句号。
李智廉上学念书的往事
李智廉的童年是在陕西兴平县一个名叫王堡的小村庄里度过的。他十四岁那年,还没有读过小学。乡间有个庙,庙里有个老道,老道有点文化,李智廉打完猪草就往庙里跑,央求人家教他认字。村中还有位老翁是珠算高手,李智廉常去他家帮着干活,为了学学算盘。
土改的时候,李智廉的算盘已经在村里排名第二了,就在分地小组跟着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一道给全村人分配和丈量土地。渭河平原上,就是柳青《创业史》中描写的那片土地,有好地也有孬地,地块的形状梯形三角狭长拐曲啥样的都有。分地时好孬都要搭配开。他把这活弄得有条有理,小小算盘噼哩啪啦一响,那几亩几分的数字就出来了,老人们用木尺丈量完,钉上木牌牌,土地新主人的名字便和这块土地融为一体。
乡长来到村中检查土改,发现他少年有为,一问,这孩子还没有上学。乡长说:“不上学怎么行?,耽误人才啊。”当时李智廉的家境贫窘,父亲患腰间盘突出还得忍痛于很重的农活,母亲也有病。弟弟妹妹都小,他是老大,里里外外全靠他。乡长跟他父亲谈,他父亲咬咬牙,同意孩子去念书。后来这位名叫李维远的普通农民自己一辈子忍受病痛和劳累,供他的五个孩子念书都念到了份儿,其中两个是大学生。六十八岁那年老人仍在田间劳作,不幸脑溢血跌倒,与世长辞。乡长还给小学校长写了个条子,李智廉一上学就插在四年级。
全班顶数他岁数大,基础开始又不如人,人家念书是连玩带念,他念就得拼命。或许真像乡长看透的那样,他天资聪慧,更加上起早贪黑,没多久,其成绩遥遥领先,班级里的小弟兄们不得不为之刮目。五年级刚刚读罢,老师见他快过了考中学的年龄,也是慧眼识珠,坚信李智廉能行,便找来六年级的几本书,对他说:“你别继续念小学了,把这些书撸一撸,考县中去吧。”当时新中国建立才两年,他家乡只有县里有中学,乡村孩子能考上的寥若多云之夜的寒星。
那些天,活扒皮一样。一个月起早摸黑地啃课本,瘦得他脱了像。
有一件事使他受到强烈刺激。中午一个同学把一本教学参考书放在课桌上,教室里没人,只剩他自己。他好奇地拿过那书。心想以前听说有这种书,从来没见过。翻了几页,被一道陌生的习题吸引住,演算着演算着忘了时间忘了一切。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抢走了书,智廉很尴尬,想向人家道歉,还没等他张口,气哼哼的一句话使他目瞪口呆,“癞哈蟆想吃天鹅肉呢,也不瞧瞧自己!”他感到奇耻大辱。知耻者勇,哀兵必胜,古话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县中发榜,他榜上有名。
学校离他家三十多里地,得住在那儿。星期六中午放学回家,干上一天农活,星期天下午从家里出来,备上一瓷缸咸菜,背上一包袱干粮,这是他一星期的伙食。从初中到高中连续六年年年如此,最后使他养成了一个毛病,就是一看见咸菜就从胃里冒酸水,后半生他一口咸菜也不想吃。
每年的寒假和暑假李智廉总要跑到百里之外的西安去。那时西安南门外正在修建十几个大学,那里有个人力市场,打短工的人一大早就聚在那儿。雇工的人喊:“一天五毛,谁干?”短工们就说:“五毛不行,7毛吧。”人家说:“那就六毛。”于是干活的人跟着雇工的人去了。白天抬砖搬瓦装车卸车,晚上短工们只能睡在城楼子上仰望星空,几百人黑压压地躺倒一大片,李智廉也是其中的一员。
李智廉看着流星划过苍穹,听着钟鼓楼角檐微响的铃铎,心中就涌动了诗意。打开手电,记录下来。他说那个时期他写了五十余首诗,梦想着将来成为诗人。后来在大庆会战的时候。那些诗篇连同粮票都被小偷从他的小木头书箱里窃去了。至今他对那些诗稿惋惜不止。
有时候干活要到渭河南岸,晚上回不去,就找个屋檐坐下对付一宿。赶上下雨,雨点打在蒙头的雨布上噼噼啪啪震得人无法入眠,这也是构思诗篇的天赐良机。一不小心天就亮了。这样干上四十天,纯收入二十来元钱,一年的学费就够了。
初中时期的他在学习方面一直拔尖。譬如语文课老师在课堂上讲,他在下面把课文看几遍,基本就能背诵下来了。初中毕业没让他考试,被直接保送到高中。后来又被保送到西北大学。
再后来……那就不是他念书的事了,要写须另拟标题。大庆市党委书记、大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这两副担子肩于一身,再忙再累,一想起自己念书的那些日子,他就浑身充满力量。如今儿孙满堂的李智廉回忆起童年少年,仍对那位乡长充满深情。他说,机遇对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候因为出现一个人,那人说了一句话,或办了件什么事,一下子就改变了另一个人的命运。
张学民的一个除夕之夜
1986年的腊月最后三天,张学民和他的两三个工友在寒天冻地里日夜连轴劳作着。他们要刨出深埋在地下的自来水阀井,因为让胡路3楼区有四栋楼两百个住户吃水难,问题出在阀井的阀门没开到位。他们刨冻土、烤冻土,终于在除夕下午,用汽焊灼烤锈死的阀门,浇注机油,开闸放水了。四栋楼五六挂鞭炮齐声爆响,一片赞扬一片欢呼。张学民弯下腰,和哥们盖上新的阀井盖,清理好现场。回到所里已经三点。
刚洗把脸,张学民的工作服脱下了一只袖子。气喘嘘嘘跑来一个男人。他家洗菜池子的下水道堵了,淌厨房满地水。班里的工人们多想回家,孩子老婆都眼巴巴盼着呢。那男人一口一声“大过年的,真不好意思,可我家这年怎么过呢?”
张学民又把那只袖子穿上,“大家都回家,这活我顶多半小时就完。”
党员张学民,小小的班组长,在两天一夜的辛劳之后,没有一丝踌躇一丝抱怨,拿起钢丝抬腿就走。
夜幕低垂,家家户户点亮红灯燃响炮竹的时候,疲惫的想家的张学民穿过满世界的喜气,走向他的小平房。
进屋关门,年的气氛节的欢乐就都隔在外面了。
家里静静的,冷灶,冷脸。妻子女儿和儿子三个人泥塑般坐在床上,他们不理睬张学民。
原来是家里气罐空了。那年娘仨的户口还没迁来,由此领不来住房证换罐证,家里只有一个罐,还是借房管所的,用完了要到所里食堂的仓库去换。他爱人杨兆琴找他一整天也没抓到影,又找不到食堂保管员,人家食堂门窗还贴了封条。
张学民想把爱人孩子的撅嘴变成笑唇,乐呵呵地喊:“过年了,过年了,咱家包饺子!”
杨兆琴说:“没气了!你自己做去吧!”
“哎,大过年的可别说没气没气的,领导放心,我老张出马,伸手就扛个罐回来。”
疲惫不堪的张学民在关键时刻很及时地幽默了一把,把爱人给逗乐了,“谁稀罕领导你。”
这时候已是晚上六点。
张学民骑车钻进夜色,爬五楼敲开食堂保管员家的门,人家正在灶前忙碌。
他叫了一声尤姐。
尤姐烹炒炖烧倒不出手来,自然是挺为难,一大家子等着吃团圆饭呢。她说:“那咋整啊?再说都贴上封条了。”
张学民看看七碟子八碗红鱼白肉绿菜,满屋香气诱得人食欲强烈,想想自己家里空锅凉灶,老婆孩子在大年夜脸色冰冷。他心底许多念头翻滚,说:“尤姐啊,你信得过我张学民,把钥匙给我,换完罐我再送来,所领导那边我去解释。”
晚上8点,千家万户酒足饭饱男女老少坐在沙发上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张学民终于捞到机会能坐一会儿了。爱人领着九岁小儿六岁小女在厨房喜洋洋地包饺子,他也想跟他们一块儿去忙去乐,但是他太累了。
杨兆琴端着两盘热气腾腾的饺子进屋。冷丁就僵僵地站在屋地当中,眼泪涌满了她的眼眶。
张学民歪歪斜斜坐在椅子上,像个淘气的孩子,睡得酣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