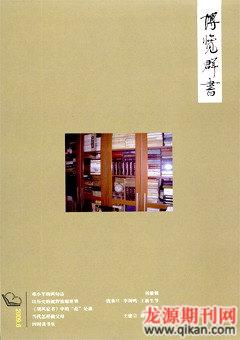水峪
梁东方
离开石家庄,穿越熙熙攘攘的河北鹿泉县城,在经过郏石沟垃圾场之前,从平原上逐渐升起来的公路还没有开始做一个接一个的盘旋动作的时候,看见路上有一队骑车的老年人。老人们穿着运动服,戴着平常在城里的时候看上去很一般、现在在山野中有新绿的麦田与刚刚盛开的杏花点缀的环境里觉着十分有动感的棒球帽。想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是从报纸上看到了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新发现以后,奔着那近在咫尺却无缘得知的水峪村去的。不想,他们却拐了弯,向着鹿泉火化场方向的山谷鱼贯而去。等下午我们离开水峪村的时候,在狭窄的村外小公路上又遇到他们。他们果然还是奔着水峪来的,只是走错了路,甚至走错了不只一次,才刚刚到。因为路面非常狭窄,有车经过的时候,行人和自行车就不得不努力让到路边上去。这时候,我看见其中一个女的冲着车和被车带起来的尘土嘟嘟囔囔起来。那嘟囔的嘴形自然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国骂。这是焦躁的城里人的一个习惯,对不满意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骂。但是这样的骂挪到水峪这样的山村里来,却显得十分另类。这可是一个世世代代都难得见到极端情绪的地方。
水峪村中人普遍是平和的,是在自然状态里生活惯了以后少有外面的刻薄与寻衅习惯的。即使是在小卖铺里做生意的人也非常和善,对也是同村的买货人完全是一副乡亲情谊的态度;卖着东西还在逗顾客的孩子,说着家长里短的话。对于需要找回来的一毛钱,买主很慷慨地说不要找了;卖主立刻就去那倾斜的玻璃糖罐里抓了几粒糖,笑容满面地递向买主的孩子……这里是山中最靠里的一个村庄了,任何一个外人都不可能上这里来买东西,来买东西的只能是本村中人。小卖铺里的东西非常有特点,架子上板子上,甚至地面上都摆满了东西,从蔬菜到作业本,从装在倾斜的罐子里的糖果到农资化肥,一应俱全,都是村子里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东西。酱油醋居然还不是袋装的,而是大桶来了以后分装到买货人的瓶子里去的那种方式,那种自己小时候的方式,也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方式。整个村子里的人的精神状态也多有三十年前的痕迹。在这里,让人多少有了些钻进了时间隧道,时光倒流回到从前的享受。当在曾经的历史中点点滴滴的永远失去了的惬意,不期然地重现在眼前的时候,让人不由自主地一次次地惊喜起来。
这一天阴历逢九,是水峪村一个月三次的集日中的一个。说是集日,其实不过就是在高坡上一小块稍微宽敞点的地方,沿着路摆开的那么寥寥的几个摊位。卖的主要是种子、衣服,还有那种城里两元店里的五金产品。来转的都是本村的人,没有外人,所以卖货的人很悠闲。情绪上很放松。到了这种一向和商品社会没有太大干系的空灵之地,卖多卖少反而成了不必太关心的事情了。人来人往其实就总是那么几个人,大家买或不买,都围在那里看着、坐在旁边聊着,形成了一个散居在各自的屋子里的人们、暂时放下手里的活计、出来互相见面的社交场合。高大的柿子树把自己复杂的枝枝干干的影子温暖地投射到地面上,投射到大家的面孔上,刚刚开始萌发的叶芽几乎还不被察觉,在地面上的枝条的影子上还很难做具体的辨认,不过确实已经与冬天干巴巴的影子有了明显的区别。从沐浴在这影子里的人们脸上的享受的表情,可以知道,大家其实是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区别的存在。春天来了。
时间在水峪放慢了脚步,在放慢了脚步的时间里按部就班地生活着的水峪人,自然也与这样舒缓的节奏协调一致起来:一切都不急,一切都不出所料,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永远不会来。春夏秋冬,雨雪风雷,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环境中的一切都顺理成章,顺理成章的生活着的一切普遍呈现着一种现代人实在罕有的平和冲淡的遥远时代的人类品质。这种人类生活的品质因为距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所以一旦得见,就有一种恍惚隔世望见了自己的前世的生存的醒悟:原来,人还是可以这样度过时间、消化自己的一生的啊!
水峪村延续下来的人类生活的遥远的气息,是一种用环境和细节构成的场,在这个场里,任何一个到达的人都会敏锐地捕捉到它那看不见的存在。如果说这遥远的品质还有什么直接的可以述说的物证的话,那就是它的老房子,也就是在这次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所发现并被登记为文物的水峪民居建筑。那是一片顺着向阳山坡一层一层地垒上去的石头房子,一户挨着一户,一间挨着一间,墙与地面,顶与街道,都是就地取材,从周同山顶上的采石点里弄来的暗红色的石头,一点一点砌成的。这些石头的被使用,都有确切的年份,这些年份就写在山墙顶端与屋顶衔接的所在,通常会在右边写上年号,在左边写上具体的年代。比如一边是“光绪”,一边是“叁年”;一边是“中华民国”,另一边是“壹拾陆年”。有意思的是,一些曾经非常忌讳的年号比如“中华民国”,在如临大敌的年代里,它们和它们的主人都得以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完全得益于水峪村世外桃源一样的地理位置。山高皇帝远,无所不在的政治力在这难以抵达的地理角落里,也会大打折扣的。这是不是当初的先民选择水峪这样偏僻之地居住繁衍的一个重要理由呢?采石于周围的山顶上,从开采运输打磨到最后盖成房子,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偏僻的山里的生活脉络里,艰辛早已成为一代代的水峪人日常生活的题内之义,人们接受起来没有什么障碍,大家早就认可了生活本身就天然地应该含有艰辛的事实。平静是这种石头房子里的生活中最为触动人的一种品质,如水一样的祥和弥漫在时间的所有角落,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行进着的。地理上的群山环抱,使距离县城只有十公里的水峪村处于一种绝对的“地偏心自远”的宁和之中。心远而地偏的状态其实是比较难以经常达到的,还是这地偏心远来得更顺理成章。
这种在建筑上标明建筑年代的传统从过去一直延续到了几十年前,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是砖瓦水泥结构的房子上,也还能在台阶上或者屋顶上看见用碎磁片拼出来的年份记录:“1973,5,25”或者“1979,4”。在建筑物上郑重其事地写上年份,是人类对于自己倾力进行的建筑的尊重,是对人类自己从事的这一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纪念。这种郑重,说白了是对生活的热爱的一种具体表现。水峪人的一辈子里,所干的最大的事情大约就是建房子和生孩子了。生孩子固然重要但是往往水到渠成即可,盖房子则要预先进行多年的准备,既要有钱还要有力,既要有地方还要有人脉,往往都是人到壮年在一生中财富和精力都最好的时候才会盖房子的。房子一旦盖起来,就算是为后代留下了基业,自己一生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任务,可以落幕了。剩下的时光里,只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四季,沐浴着时光,一点点地老去。
水峪村的老村部分,在向阳的山坡上竖着向上依次展开,层层的石头房石头路密集地将人类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的朴素生活场
景立体地矗立在那里,让人唏嘘不已。走进一户户人家,虽然狭窄,但是绝对不浪费空间的布置,每一处都透露着年深月久的时间痕迹,一棵树皮已经相当粗糙了的大香椿树(据说香椿开始几年长得飞快。但是一旦到了一定粗细的程度就变得生长缓慢了,这么粗大的香椿树,年纪一定在两三百年之上了;而两三百年的香椿在水峪一点都不罕见),一棵歪歪的老沙果树(树干上也贴着一个大红的福字,在有生命的植被上附着文化符号的视觉效果非常有震撼力。其实,只有这样的山村,石头墙石头房子前面的对联才最有美学效果,中国传统的对联原来的出处就是这样的人居环境),一棵笔直笔直的梨树(梨树这种罕见的笔直是源于石头院落里相对狭窄的空间的,要有阳光就要向高处生长;不仅梨树,水峪村中那些古老的树木一般都有这么一个笔直的特点),数一数,说一说,都有几百年以上的年纪了!在一户没有门的院子里(后来注意了才发现,水峪村里有门的院子并不多,因为没有外人,一般人家除了吃的喝的也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言,所以几乎没有安装院门的必要),影壁后面正有一头驴在吃草,只露着一个大大的安详的驴脑袋。老太太满脸笑容地迎接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望着大家如入无人之境般地登堂入室,嘴里诚恳地说着喝点水吧、喝点水吧的话。水峪人对很罕见的外人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既礼貌诚恳,又有一种完全不以为怪的大气。你要作为审美对象来看我们的生活,就尽管看好了,就像对待以其它别的目的观察到我们的生活的人一样,我们永远会平静地宠辱不惊地面对一切,一如既往地按照我们原来的节奏进行我们自己的生活。
水峪的民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它还活着,还在被使用着,每一个细节里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一堆牲口粪,一只开始本能地吠叫了几声、继而马上就垂着尾巴跑过来、任人抚摸的黄狗(这村子里的狗平常所采用的最多的姿势就是趴在地上,懒洋洋地睡觉,绝少那种虎视眈眈、如临大敌的平原上的狗模样。它们一代一代地在这种平和里生活得久了,也早就养成了和谐安静的习惯),一条紧贴在红石头墙壁上的挂着衣服的绳子,一只卧在去年的玉米秸里的老牛,一个笨拙地挪着脚步的孕妇,一位用镰刀削捆柴禾的锯子的老人……这种人类依然生活于其间的文物级的民居景观,尚未被商业开发之前的自然状态,是有着一种强烈的吸引力的,让人不由自主地就想象假如自己也是这生活中的一员,会不会就少了很多现在动不动就缠上身来而且总是挥之不去的莫名的焦虑呢?
确实,以前看民居很少设身处地地考虑过,不过是拿他们作为一种与己无关的物在做客观的观察而已。但是在水峪却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一种想象,想象自己生活在这里的细节,这些细节被想象一点点扩展开来的时候,自己就仿佛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水峪人了。要住下来首先想到的是水,水峪水峪,是以水出名的,一条河谷绕村而过,村外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水库。可惜的是现在河谷里撒满了塑料垃圾,在刚刚萌生的绿草中的不多的水上,有几个农妇在洗衣服。水峪是太平河的源头,是现在用拦河坝和地下水整治出来的公园一样的石家庄城市水系的自然源头——在南面渐渐升高的高岭坡地上,有水量已经大不如前了的泉水在无声地潜流着,最终在正定城的古南门外汇入滹沱河的太平河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水峪村里还有一口至今仍在使用着的古井,井边上有几棵碗口粗的爬山虎老藤。那藤向着两个方向的住户的外墙和屋顶上竖着攀援横着前进,形成了一道老藤搭墙的罕见景致。
在水峪村的学校、观音阁和戏台(这后来重建的观音阁和戏台上也有建设年份,1980。我们经过的时候,戏台上,村里的干部正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队员们展示清朝留下的戏服。粗布料子上的彩色十分鲜艳,青蓝与猩红都很扎眼)、医疗所之间,在居住地和田地之间的桥头,形成了整个村庄最大的一块平地,也是村子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带。这里有一种非常难得的开阔——当然,这种开阔在先民看来一定是极大的浪费。仔细查看的话,不难发现,这里是原来的耕地。先民是绝对不肯将这么大一片耕地用作平时无用只偶尔一用的所谓聚会场所的,他们以河为界,河那边的山坡地才是家居的地方,河这边平整宽广的河谷地带都是宝贵的耕地,千百年来都不曾越过雷池一步,现在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改变。耕种与收获的需要的绝对重要性,使任何违背这一点的空间行为都是一种有违道德的恶行。但是商品贸易渐渐地侵蚀着这里一向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耕地的重要不再具有那么立竿见影的惩罚效果了,即使失去了一些耕地,人们也能照样吃饭。水峪也并无例外,在这个时代匆忙的脚步里,它不过是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脚步缓慢、有幸多在过去的时光里浸泡一段时间而已。
离开村子回头看,水峪的四围皆山,中间的谷地却是十分平坦开阔,这是水峪得天独厚的类似于桃源的地方,这种地理形势不仅给居住其间的人以安定感,还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耕种空间。盆地四周虽然都是山,但是山势都不恶,山脊线没有剧烈地抬升和落下,都很圆润,起伏和缓。没有峥嵘之相,处于山怀之中的人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和之感,安静和甜蜜是这个山环水穿的小环境里的气氛主调。
在水峪的这个安静的山怀里,有泉水,有耕地,有几乎树树都安着喜鹊巢的大杨树,有很多古老的柿子树,道劲的枝条和巨大的树瘤都构成一种经年累月的痕迹。不过西南角山顶上(那里原来是水峪村通向更里面的那个正放着地方戏的村子的古路的山口)的那个石灰场实在是煞风景,虽然罩了一个塑料棚子,但还是不能遮挡阵阵飘起的烟灰,它们不断地弥漫到山谷中来。好在这盆地还足够大,能够很快地消化掉那一股股的烟尘。从水峪看外面的世界,就像从过去看现在,人类自己的发展带来的弊端一清二楚;而所谓发展的脚步又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的。
不过,村前的田地和村庄还未受大的影响,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在温暖的空气里。菜地里新出的绿色和村庄上空的大树树梢上古铜颜色的嫩芽,还有高高的大树下全是暗红色的石头铺就的小路上偶然走过的村人,都让人有一种田园画的感觉。那座放着几块老屋上拆下来的大石柱的老桥上,正有一个只买了一角饼提着的老人走过。他身边的一户人家的柴棚的门,居然是不知哪朝哪代的雕花隔扇……
(本文编辑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