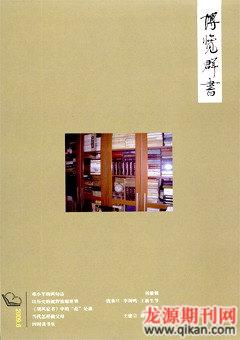转向记
《转向记》,赵京华著,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第一本文章的结集。除了一两篇万字左右的论文之外,都是些书评性质的学术随笔之类,写作时间大致在2003年留学回国至今的六七年间。论数量不算很丰厚,但我自己还是比较看重的。因为,这些文章记录了自己学术转向的经过,留下了阅读当代日本、思考中国和东亚问题的轨迹。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原本是搞中国现代文学的,20年前曾写过一本关于周作人的小书。1990年留学日本,当初也是计划做些中日文学比较之类的学问。没想到海外飘泊10余年,如今会从事起“日本研究”来,而且是远远跨出了文学的范畴。这次编辑此书,使我有机会检点和总结自己近些年的学术工作,将大小文章归类之后,不期然地呈现出了我关心的范围和兴趣所在。
集子里有三个部分。“知识左翼眼中的日本”,是写作《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北京:三联书店,2007)一书时的副产品,主要透过日本当今批判型知识分子对本国思想、历史的反思,来观察那个扑朔迷离的战后日本。我很庆幸,留学期间能够接触到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小森阳一等一流学者,阅读他们的著述文章,不仅提升了理论素养,更让我从历史和思想的深层视域,看到了那个自己曾经生活于其中以为熟悉的“日本”其背后的“历史水脉”和“精神骨格”,也深切地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仅凭日常生活经验是不够的,深度的知识学理观察亦不可缺少。因此,这一部分的文章,虽然在内容上与我那本专著有重叠的地方,但还是收入集子中,希望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和我一样,透过日本“知识左翼”批判性的视角,加深对邻国日本的了解。
“文学、历史、地缘政治”部分,是我引进和介绍日本的另一类知识——中国学,并与之对话、交流的文章,包括在此基础上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地缘政治问题的思考。大家知道,日本的中国学,战前在古典领域,战后则是在鲁迅及革命中国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从留学当初便一直对这方面多有关注,所结交的日本学者、师友也是以这一领域中的居多。他们的思考和研究,为我提供了认识中国的另一个特殊视角。“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实体和错综复杂的想像对象,那种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认识“中国”的想法,是最愚蠢不过的,连称其为文化民族主义都不够格。我们需要多元的视野来看“中国”,国外汉学无疑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当然,日本的中国学包括战前的“支那学”和战后的中国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有自身视野和立场上的偏颇甚至意识形态化的偏见。因此,我在这一部分文章中,不仅看重其杰出的成就和想像“中国”的方法论视角,也对其中的问题如为帝国主义殖民历史辩护的“文明与野蛮”二元论等有所触及和批评,以期形成对话的态势。同样,“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缘政治”也是一个复杂的论述对象,而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以及东京审判之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依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试图从“日本”这一视角进入问题的讨论,开掘知识视野和思考的深度,所得的成果虽然还不多,但愿意继续努力下去。
“翻译与文化沟通”部分,则反映了我这几年来着力去做的另一方面工作:对日本学术著作的翻译介绍。从内容上讲,一如上面所述,翻译的选择还是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学者关于本国近代历史和思想的批判性著作,另一个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我一直认为,“外国研究”首先要注重对该国重要的思想学术文献的翻译。自己留学多年,掌握了关于日本的必要知识和语言能力,在从事研究的同时应该亲自动手搞翻译。世间有一些心急手快的所谓学者,把别人的东西不加说明地“拿来”使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还自以为高深莫测有学术创见呢。且不说这种行为的学术道德如何,至少无助于不同国家民族间文化学术的沟通。我每读到日本学者的优秀著作,常禁不住想挤出研究上的时间来翻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共享这些学术成就。文化沟通离不开虚心坦怀的文字转译。我将自己五部译著的“译者后记”收入这个集子中,目的不光是为了纪念翻译上的甘苦,更期待读者们通过这些导读性质的文字而对原书产生兴趣,从而萌发找来一读的兴致。
回想起来,自2003年归国而转向“日本研究”,如今已有六七年的光景,这转向不仅是研究方向和范围的变化,还包括从文学研究跨向思想史、文化研究的专业性质上的转变,其中的艰难和困惑,自己是最有体会的。我将书名定为“转向记”,也是意在留下一点儿记忆。我不知道这一转向是否成功,但至少以为找到了研究“日本”的感觉,并愿意继续沿着“日本战后思想史”这个方向走下去。而说到“转向”的远因,当然与20年前决计“游学海外”这一个人抉择有关。1990年离开故国,一走就是十几年。我常对朋友笑曰,自己人生中最年富力强也最贵重的一段时光和记忆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日本。尽管对这个“日本”也时有不满甚至隔膜,但它已然成为我记忆的另一个原乡,无法割舍。因此,我关心日本,也是在回顾自己,正如我研究日本也就是在思考中国一样。我的最大心愿,是向中国的读者呈现一个比较真实立体的日本,在褒扬肯定其优点的同时也不忘对其偏狭之处加以批评。通过理解和承认一个作为真实“他者”的日本,最终使人们与那场造成巨大“民族仇恨”的战争历史达成和解,这恐怕是我学术转向的根本动力吧。
编辑这个集子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可以使自己这一段的工作有个了结,从而轻装上阵向新的学术目标挺进。这新的目标眼下还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即从口本战后作为“政治抗议”的社会运动入手,进入思想史研究。我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怎样艰巨的学术征程,但愿意再做一次挑战和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