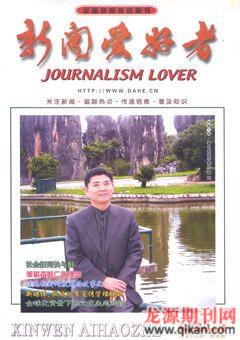走不出男权藩篱的简·爱
杨永华
摘要:很多学者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解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认为简·爱身上体现了浓重的女权意识。同时,作品的叙事方式也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很好的注解,从简·爱的成长历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自尊、自爱、时刻追求人格独立的女子。但是,作者在竭力表现简·爱追求自由、追求平等的同时,却由于顾虑重重而不得不表现出对男权意识的驯服和服从。
关键词:男权意识 独立人格 叙事方式
夏洛蒂·勃朗特是19世纪英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简·爱》因为描写了一个“使心脏跳动得如此快速,使热血如此奔涌”的爱情故事而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书中的女主人翁简·爱这个孤独、平凡、贫穷但充满自尊的女子在追求平等的爱情幸福时所表现出的勇敢、自尊这一新女性形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全书试图表现的是:一个男人的价值不能只凭他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少等非本质的因素来决定,而一个女子的价值也不能仅凭她的美貌、身材、女性魅力等取悦于男人的性的因素来决定,其思想道德、才智与情操等内在因素应该是其实现理想婚姻的重要基础。恋爱中的双方应该地位平等,幸福的婚姻决不是一种等价商品的交易行为,而是两个志同道合男女的幸福结合。但是,通读全篇,从作者的叙事结构来看,其所宣扬的男女平等是大打折扣的,因为其潜意识中仍然显现出对男权意识的尊崇和驯服。在故事的结尾,简·爱得到了她所追求的幸福,拥有了完整的爱情,得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她沉浸其中,与她的爱人在他们的伊甸园里幸福地生活下去。而这一切的实现全都仰仗她所获得的叔父的遗产,她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孤女变成了一个有钱人,她再也不用自卑,再也不用自我克制,财富使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获得了敢于追求美满婚姻的力量和勇气,现在,她可以理直气壮地找到自己已经由于一场大火而家道中落的爱人,相夫教子,回归一个平凡的女性。她所追求的平等婚姻是以她的爱人身体残缺和家道没落为实现条件的,这一点,正是当时的文化秩序在女性作家心理深层的积淀和呈现,是作家心目中的完美爱情与婚姻的理想表现模式,而这种理想模式仍然摆脱不了对男权意识的驯服与妥协,尽管这一点是书中女主人翁竭力反对的。
英国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地位
众所周知,英国18世纪爆发的工业革命使英国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但是,这种社会变革并未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她们仍然是一群缺乏经济基础,不得不从属于男性的集谦卑、柔顺、牺牲为一体的理想角色。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群体在男权意识的掩映下缺失其明晰的、应有的社会群像,尽管有些人不再为生计奔波,但她们的生活空间仍然很狭窄,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家庭生活和自我想象、自我憧憬的情感里。就是作者自己,因为前一次的退稿经历,在作品发表时也取了一个男性化的名字。事实上,在当时的英国,女性没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嫁,通过婚姻来保障自己未来的生活。而她们一旦结婚,便完全变成了丈夫的附庸。
《简·爱》的独到之处
《简·爱》的问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在世间,因为,它颠覆了英国文学中固有的女性形象,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的“理想的淑女”和“家里的天使”模式的反抗,它的故事曲折、惊心,令人耳目一新。在《简·爱》中,我们听到了代表男权的、淹没人性的世俗声音和被压抑的女性反抗声音之间的较量。从头至尾,作者都想把简·爱塑造成一个反传统的、以大胆的叛逆精神热情追求爱情和婚姻幸福的文学形象,她是一没有倾城美貌,二无万贯家财,却有着独立人格和丰富情感的弱女子。而且,作者也的确成功了,从本书的叙事情节我们可以看到,从小说一开始,作者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她家境贫寒,无依无靠,身世可怜,同时,她相貌平平,而且她性格怪异、固执,富有反抗精神。当她无端受到打击时,她会“狠狠地回击”,“叫他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无助的简·爱熬过幼年和少年,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成长起来。但是,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人格独立的女子,为了追求自由,摆脱折磨,她十岁时便坚决离开舅母家,进入一个陌生的寄宿学校。虽然孤苦无依,身无分文,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当时社会所需并可使自己完全独立生活的自立能力。尽管作为家庭教师薪水微薄,但足以养活自己。可以说,此时的她不仅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同时,她坚决反对传统的以出身、财产、阶级等物质因素来划分人们的社会等级,敢于向男性的权威地位提出挑战,提出在上帝面前,人与人真正完全平等。在桑费尔德,经过一系列尊严和人格的较量,她终于用个性的魅力感染了罗切斯特,带给他一种生活的新气息。而且,在得知罗已经有妻子时,她依然抛开痛苦和绝望,抛开灵与肉的抉择,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桑费尔德府。一直到现在,作者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个身份低微、弱小平凡的弱女子,如何抛弃世俗,同时又杀入世俗的中心,作为一个家庭教师,却向自己的雇主——富有的庄园主求爱,而且,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女人向一个男人求爱,一个年轻姑娘向一个中年男人求爱,这些情节描写在当时可说是有点惊世骇俗,令人大跌眼镜,目瞪口呆,同时,这也是近代很多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内容,更有很多人奉作者为女权先驱。
诚然,故事到此,我们为简·爱的不幸遭遇而流泪,为作者所竭力倡导的女性意识而喝彩,但是,读完全书,掩卷思考,我们感觉作者在为女性大声疾呼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回归到了她试图回避的男权意识中去。
本书中所体现的男权意识
作为一个18岁情窦初开的少女,离开整年不见几个男人的寄宿学校来到桑费尔德府的简·爱一下子喜欢上了她的新主人。他富有、傲慢,这些对于任何一个爱做梦的少女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简·爱也不例外,她喜欢上了罗切斯特。但是,她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她把罗切斯特当成了自己的供主,自己的主人,而主人一句温柔的话语都使她受宠若惊。在桑费尔德府举办家庭宴会时,她专门坐在角落里,以期避开别人的注意力,与那些富有、美丽的小姐相比,自己就如同一个丑小鸭。她在画布上画出她心目中的英格拉姆小姐,以便时刻提醒自己,罗切斯特要娶一位才貌双全的小姐,他无论如何不会爱上自己,告诫自己不要做白日梦,不要忘记他们之间巨大的财富鸿沟。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简·爱爱情的勇敢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自卑,即使她发出“我们是平等的”呼喊,但这种呼喊是如此的底气不足、战战兢兢和无可奈何。当罗切斯特说出对她的爱慕时,她兴奋万分,但是,一阵兴奋过后,她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即使在旅行箱上也不敢写上罗切斯特太太的名字,她不敢相信那个名字属于自己。在教堂事件发生后,简·爱选择了离开,从表面来看,是简·爱不甘成为罗切斯特的情妇,她无法忍受失去一个平等自尊、坦诚面世的婚姻与爱情。实际上,这恰好反映了简·爱心中难以摆脱的法律、宗教和社会习俗的约束。简·爱深爱罗切斯特,但她实在没有勇气面对一份即使是名存实亡婚姻的威胁;简·爱口口声声要求人格上的独立,尽管她对婚姻充满了憧憬,但她无法面对伯莎·梅森背后强大的法律、宗教和习俗,无法面对强大的社会秩序: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所以,她的离去,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逃离,是对不道德的逃离,对违背宗教习俗和良心的逃离。这种逃离实际上是她在人性与神性的强烈碰撞和极端冲突下,在她对于神的旨意的服从下所作出的决定。
如果这一点还不足以证明笔者的论断的话,故事的结局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证明。简·爱逃离了桑费尔德府,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自己的亲戚,她感到万分高兴,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与此同时,简·爱得到了过世叔叔的遗产,她不再是一个穷人,有了钱,她再次想起了她的爱人,在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后,她听从心灵的召唤,毅然离开,去寻找罗切斯特,而此时她并不知道在桑费尔德府发生了什么。那么,在这时,她的不愿做人情妇的自尊到了哪里?为什么她这一次要听从心灵的召唤,返回桑费尔德府,难道她不知道罗切斯特还有一个妻子吗?她此时为何不考虑那个阻碍的存在了?那么答案只有一个:现在,她有钱了,她不再是那个贫穷的家庭教师,她完全配得上罗切斯特了。这样,在作者的巧妙安排下,简·爱经历了一个由贫到富,由丑到美的变化,而罗切斯特则经历了由富贵到破落伤残的过程,这样,简·爱与罗切斯特才真正平等了。设想,如果没有伯莎的那把大火,当简·爱回到桑费尔德府,见到依旧富有的罗切斯特和他的那个疯女人时,她有何感想,她真的能够感觉到与罗切斯特先生在精神与心理上完全的平等吗?
当简·爱回到桑费尔德府之后,大家可能注意到,她说话的口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在她见到罗切斯特时他们有一段对话:
“你没死在哪条溪流下的哪条沟壑里?你不是在陌生人中间的一个憔悴的流浪者?”
“不是,先生,我现在是个独立的人了。”
“独立!你这是什么意思?简?”
“我那在马德拉斯岛的叔叔去世了,他留给我五千英镑的遗产。”
在这里,金钱拉近了她和罗切斯特先生的距离。与当初的沉默不语完全相反的是,她大声说出她对爱人的思念,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在小说的结尾,简·爱最终彻底回归到了“家庭天使”的角色中,她沉湎于与罗切斯特的爱情中,她成了罗切斯特的“瞳子”、“骨中骨,肉中肉”,没有了自己,那个口口声声要求平等的简·爱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由上帝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所造出的另一个夏娃。可见,那么坚强、独立的女子如简·爱在金钱的帮助下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尊,同时,伯莎的那把大火使简·爱的自卑心理获得了一次完全的释放,它给了简·爱真正的安全感、平等感。所以,简·爱的回归是建立在这样几个因素之上:第一,她继承了遗产,现在不再贫穷;第二,桑费尔德府经历了劫难,罗切斯特再也不是那个傲慢的主人了;第三,尤其重要的是,那个妨碍他们结合的障碍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束缚他们的法律、宗教和习俗也迎刃而解,那么,作者心目中的完美爱情和婚姻才能够呈现。第四,作者竭力想表现的女性意识大打折扣,这个由简·爱获得了经济与爱情全面胜利的“大团圆”实在是否定了简·爱的精神价值,同时,带着财产嫁给罗切斯特,这难道不正是另一个伯莎·梅森吗?这个自我标榜人格独立、追求平等婚姻和爱情的简·爱为何走上了伯莎·梅森的老路?简·爱就如同一个唐·吉珂德,她以自己弱小的身躯,由于贫穷而产生的自卑,三心二意的独立意志去抵抗强大的男权世俗,但是,一番回合之后,她完全败下阵来,心甘情愿回到她所竭力抵制而又心向往之的道路上去。
由此看来,即使聪敏如夏洛蒂·勃朗特,时代的局限性在她的心头仍然占据很大的位置。同时也证明了,在漫长的男权文化的熏陶下,作者不由自主地在文本中体现出这一文化秩序在其心理深层的积淀和呈现。对此,我们只能解读为:第一,作者自己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第二,作者所要面对的读者群体的要求;第三,作者为了其作品的问世、流传所采取的对世俗观念的妥协。由此,我们只能断定,这种委婉、暧昧的表现方式彻底否决了简·爱对男权中心意识所做的解构。那么,作者为何如此处理呢?如果阅读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的一段话我们就可以明白:当这些聪明的女作家发现创造力被定义成了男性的专利而女性无缘染指时,在创作中,她们时刻牢记她自己竭力想构筑的理想世界与她们又要时刻面对的这个男权意识浓厚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区别。在这样的一种对自己作家身份的焦虑中,她们在作品中对现实进行了妥协。事实证明,作者的这种对当时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现实文化的妥协非常成功,因为这样一个结局最为大众所接受,最符合大众的期望。这样一来,它即为作品的顺利出版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作者赢得了极大的社会荣誉。
参考文献:
1.陈嘉:《英国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4.弗吉尼亚·沃尔夫[英]:《沃尔夫随笔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5.夏洛蒂·勃朗特著,祝庆英译:《简·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6.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