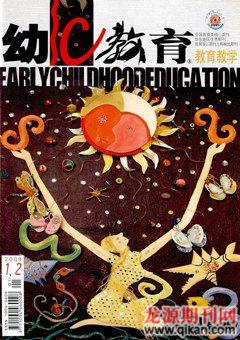自然之序与社会之序
黄 进
我看到了一个属于幼儿自己的典型的游戏情境。
首先,游戏是对生活的选择性模仿。幼儿对于印象深刻的场面往往会有情绪高昂的表现,甚至会偏离教师的引导和构想。这一点恰恰非常吻合幼儿的游戏心理。我们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幼儿的这种心理。比如,听一个故事,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中最具有刺激性和戏剧性的情节,要求成人反复讲述或者他们自己反复表演,而非从头至尾关注故事的完整性。地震事件中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文化的毁灭性,从表面上来看具有速度、动感和新奇感,幼儿对此印象深刻,他们在游戏时对于生活的模仿往往就着力于这些印象深刻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尽管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地震是一场灾难和悲剧,我们出于良知和同情,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安抚心灵创伤和恢复建设上。而没有相关经验的幼儿会被那种毁灭性的场面所震撼,从而在游戏中投入地进行表现。
其次,游戏具有偶发和即兴的特点。幼儿有条不紊地建构新房子,不过是教师的安排。如果他们心里萦绕着前一刻看录像时的震撼,那种激荡人心的情绪和力量还没有找到出口,那么从某一个幼儿那里“决堤”是非常正常的(且不论明明搭建的房子是偶然碰倒的还是故意推倒的),然后波及整个幼儿群体,出现一场集体的“混乱”。这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而是随机变化的。正因为游戏带有偶发和即兴的特点,所以它是开放的、生成的、创造性的。平时,我们常常会在参与幼儿游戏时感觉到他们的即兴思维和应答。比如,幼儿在用橡皮泥做汤圆,不断重复着揉、搓、煮的动作。这时教师过去问:“这个汤圆是什么馅的呀?”他们也许之前并未想过给汤圆包馅,但教师的问话使他们产生了对新情节的构想,于是纷纷告诉老师“这是苹果馅的”“这是草莓馅的”,自如得好像一切早就设想好了似的,游戏也因而有了新的生长点。这使得游戏过程宛如一场对话,成人和伙伴的某句话或某个动作,环境的某个小小变化,材料的某种意外刺激,都会促使游戏偏离前面的逻辑,宛若一场没有结局的戏剧,或者一盘“没有终点的棋局”(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所云)。
第三,这种在群体游戏中忽然产生的“混乱”恰巧是幼儿游戏的一种样式。心理学家观察到儿童在一起有时会出现一种“混战游戏”,比较典型的是追逐打闹行为,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些特征,比如带有爆发性、群体性。儿童互相影响,在集体的某种剧烈动作中获得很多乐趣。在这个“地震”游戏中,由一人的建筑垮掉为诱因,导致所有幼儿都推垮建筑,大家尖叫、扑倒、扒拉积木,并达到一种集体兴奋状态,这比较符合混战游戏的样式特点。它与幼儿通过录像所了解的有关地震的现实经验结合在一起,具备了游戏的形式,也有现实生活经验做支撑。
以上判断是心理学角度的。游戏是我们了解幼儿的窗口,我们可以通过它看见幼儿对于生活经验的感受和理解,也可以看到幼儿成长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是,教育应该做些什么。我们都清楚,游戏是幼儿的本能,教育是去保护、引导和发展这种本能,而不是让幼儿停留在完全依靠本能去行动的层面上。这就使得我们要思考教育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仅仅是培养遵守常规和纪律的人?我想每位教师都不是这样思考的。我们希望培养的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行动能力的人。而我们的困惑在于:自由和快乐的游戏是否会妨碍儿童成为一个严以律己、自我控制的人呢?
我们都知道,自然和社会都是有秩序的,秩序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条件。以自然为例,从时间上它表现为生命的各种节奏,从空间上则表现为生命形态的多元格局。而社会的秩序则要复杂得多,它既是某种随时间展开的文化变迁或者更替,也是社会互生互补的差序、层次或者等级,更是人际的各种规范和规则。一个小小的生命体来到世界上面临的一大关键任务,就是如何将他那自然的生命秩序融入、延伸和成长到社会秩序中去。这两者从起源上来看并无矛盾。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的秩序过渡和变迁为社会文化的秩序的。从自然之序抵达社会之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然而儿童期只有十几年,只有十几年的时间用于从自然之序进入社会之序,用于复演人类几千年走过的历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一个已经完成了社会化的成年人,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将儿童身上的自然之序看作是原始的、野蛮的、要改造的。他们歌不成调,他们笨拙幼稚,他们没有规矩,他们自由不羁。作为他们最自然和本真的活动——游戏,更是集中反映了儿童的这些特点。
特别是在游戏被改造为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之后,我们感到一种紧张和焦虑。我们重视游戏,尊崇游戏,希望幼儿自由和快乐;而我们也希望他们符合规矩,遵守秩序。我们希望他们按照成人的要求能放能收,在我们的边界中游戏,既自由又有“纪律”。自然的人,身体心灵融为一体,感官门户全部开放,情感世界与规律世界交叉重叠,目无等级与权威,热爱建构与表达。这些特征在给予我们感动的同时,似乎也带给我们很多麻烦和困扰,因为它们破坏了我们成人世界的规则和框架。而现实中有时就会出现这个话题所表述的一种尴尬:自由和纪律难道就不能兼得?如果不能,到底如何取舍呢?
将自由和纪律对立起来,其实就是将自然之序与社会之序对立起来。原因是我们将成年和童年看作了对立的两极,中间没有过渡,没有循序渐进的发展,我们急于用社会之序去替代自然之序。而两者是统一于时间长河之中的,这要求我们成人格外有耐心和信心,去等待儿童从一个自然的人成长为一个社会的人。没有自然生命的尽情绽放,就不会有完美成熟的社会果实。因此福禄贝尔才会说:“一个能够痛快地、有着自动的决心、坚持地游戏,直到身体疲劳为止的儿童,必然会成为一个完全的、有决心的人,能够为了增进自己和别人的幸福而自我牺牲的人。”
游戏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使儿童成为他自己,成为了自己,才谈得上控制自己。出自内心自我的控制和出自外在他人的控制,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曾笑谈:中国的儿童在世界上是最被严格要求遵守纪律的人,上课坐得一动不动,作业做得一丝不苟,而中国的成年人是世界上最不遵守纪律的人,最喜欢插队、随地扔垃圾、没人管的时候就乱作一团。不论这个说法是出自什么样的心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对现有的儿童教育的批判。
我们从来都强调儿童的行为规范和秩序,而最终却失去了这一切,其原因在于我们强调的是外在秩序,而不是内在秩序。我们把逻辑上优先的事情理解成了时间上的优先。社会之序是我们的目的,可从时间上来说它不是第一性的。一个儿童的内在自然有着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在幼儿这个阶段,要尊重这个规律,就要让他们去自由地游戏。
自由的游戏孕育着看似无序的有序。例如,在这个话题中,幼儿重演着灾难的发生难道不是在试图掌握这种灾难?通过游戏来掌握某些创伤性事件,恰恰是他们建构内心秩序的重要途径。他们奋力的“抢救”行为难道不正体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珍重?这种由衷的行动难道不是由同情和共鸣所产生的道德良知?透过这种混乱的无序场面,我们能看到幼儿在建构着自我的内在秩序。而自我主动建构比起依靠他人控制而言,是多么有力量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外在秩序也需要有所要求,我们更愿意把它限定于“游戏时不能伤害自己,也不能伤害别人”。除此之外,我们都应该更宽容些。
当然,从自然之序到社会之序并不像面团揉入酵母那样会自然发酵,否则儿童的世界就根本不需要成人的引导了。儿童恰恰是需要教育的,不过,合适的教育是通过成人参与儿童的活动实现的。在幼儿园里,当每个儿童都投入到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中时,纪律和自由事实上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