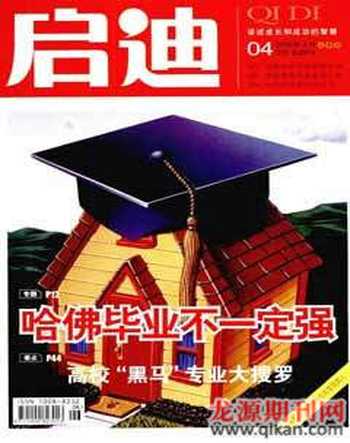母亲的镇定救了儿子的命
王 璐
丈夫在加拿大攻博的第二年,我作为陪读也到了多伦多。不久,我就有了一个给电视台打工的机会。
那天我们接到报料:一个刚满5岁的男孩被绑架了。突发新闻部迅速行动起来。那位5岁小孩母亲的名字叫凯瑟琳,是一位看起来十分一般、十分朴素的女人,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但她却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在绑匪打来电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很平静,跟儿子讲话的声音和平时一样温柔、亲切:“孩子,你还好吗?你看,妈妈和你在一起,这么多人都和你在一起。你别害怕也别着急,带你走的人会把你带回来的。”
我注意到她没有用“绑匪”一词。和那些热切的媒体、心急的观众和备受压力的警察比较起来,反倒是孩子的母亲显得平静多了。这个母亲的表现令我颇感意外。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凯瑟琳家里。在摄像机还没打开前,她对我们提出要求,她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情绪不要过激,用词也要中性,比如报道中不要反复用歹徒、残忍、卑劣等词,只需要把事实告诉人们,表示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就行了。一旁负责此案的高级警官汤普森向凯瑟琳投去赞许的一瞥。
我们的节目风格于是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凯瑟琳平静的面孔又出现在第二天和第三天的荧屏上。她请大家帮助她找到她的儿子,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在为他担心,你们也爱他,他确实是一个好孩子”。最后,她还请那个“带走孩子的人”不要伤害他。绑架男孩的人打了第一个勒索电话后就一直没了音信,度日如年地到了第四天,终于又有了一个电话。凯瑟琳温和而坚定地对对方说:“请你原谅,我们没有钱。”在场的每一位都听得清那个绑架者绝望的声音:“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稍停,凯瑟琳说:“你把我的儿子送回来,你也可以到我这里来。”那边没有再出声,一会儿,电话被挂断了。
我们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很快我们发现,凯瑟琳哀而不伤、静而不怨、遇事不乱的表情打动了电视观众,他们分明喜欢上了这位相貌平平的女士,都愿意帮助她。
一起沸腾的事件,却被我们做成了一档安静的节目。我们节目的风格又影响了整座城市,一时之间,好像整个多伦多甚至整个加拿大,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5岁小男孩安全地回到他妈妈的身边。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男孩还没有回家。绑架男孩的人一直没有再出现。电视台每天都在跟踪报道,凯瑟琳平静的脸庞依然保持着平静。虽然几天下来她明显瘦了,人也憔悴多了,但是只要我们的摄像机转向她时,她都会理理头发,迅速调整好自己的表情和声调,她仍然坚持说,相信儿子一定会回来。我们关闭了机器,她还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她的丈夫上前紧紧地拥住她——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极其有限的几个人才会看到凯瑟琳心如刀绞的痛苦。
到了第八天,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局面出现了:汤普森接到了电话,“绑匪”终于决定要投案自首!5岁男孩终于回家了。我们第一次拍到了凯瑟琳泪流满面的画面。
“绑匪”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当主持人罗德里格斯向他提问时,这个绑架者居然泪流满面。他语无伦次地说他需要钱,无奈加上一时冲动,才做下了这种糊涂事情。
随着主持人的继续提问,他的犯罪心理过程逐渐明晰:绑架男孩之后,他的内心既充满了恐惧,同时也有一种鱼死网破的决心。但是第二天,孩子的母亲出现了,她的平静令他颇感意外,不觉中也平息了他狂暴的情绪。他十分感谢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称他为“绑匪”或者“歹徒”。
但是他怎么办啊?他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无法进退的境况,但又必须做出决断。他打出了第二个电话,正是凯瑟琳本人接的,他在电视中已经熟悉了她的面容,那是他犯罪以来看到的唯一一张平静甚至亲切的脸。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啊!他伤害最深的人,他对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这时她却是唯一能给他提供平静和安慰的人。所以他拿着话筒,不由得就把心底的绝望对她喊了出来:“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她居然这样回答:“……你也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惊呆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发现电视报道也跟着起了变化,人们似乎安静了下来,凯瑟琳身上那种宁静的、淡淡的笑容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阻止着他干出更坏的事情。越到后来,他越感到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等待一个小男孩回家,也在等待一个大男孩从犯罪的深渊回心转意。他知道自己再也无力走下去了,他感到身心俱疲,也好想回到自己妈妈的身边。就这样,他带着小男孩,亲手把他交到了凯瑟琳手中。
我们拥向了凯瑟琳,她抬起泪流满面却笑逐颜开的脸向我们表示感谢。这时,罗德里格斯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夫人,您不用感谢任何人,是您自己救了您的儿子。”
洋埠亦清摘自《今晚报》编辑/米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