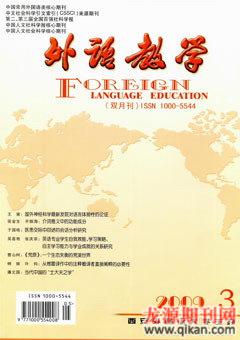当代中国的“士大夫之学”
潘文国
摘要:本文提倡一种相对于“博士之学”的“士大夫之学”,它包含五个方面:1)为人重于为学;2)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3)广博而深邃的学识;4)高屋建瓴的治学眼光;5)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作者认为杨自俭先生的治学符合这五个方面的要求。
关键词:士大夫之学;博士之学;士的精神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44(2009)03-0109-04
清儒陈澧曾言:“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当代学者余英时对此解释说,所谓“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的分别,简单地说,便是“通识”和“专业”的不同,但又不止于此。“博士”是专家,其知识限于他的专业范围;而“士大夫”负领导政治与社会的重任,他们需要有贯通性、综合性的知识,以为判断和决定重大问题的依据。陈澧强调士大夫之学比博士之学重要,并且感叹在他那个时代几乎已经没有了士大夫之学。这一感叹我想也适用、甚至更适用于当今这个时代。所幸在这个“几无士大夫之学”的时代,我们有时还能见到几位多少还有点士大夫精神的学者,使这个浮躁时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学术界还不至过于苍白。杨自俭,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这部《杨自俭文存》,所体现的就是当代中国、至少是在外语学界的“士大夫之学”。
“士大夫”这个词语,现在人们已经很陌生了,我们有必要加以申述。“士大夫”中的核心概念是“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者西方话语中的“公众知识分子”。在不久前一次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中,我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每一个重要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凝炼出一种“民族品格”,成为该民族在世界上的形象符号。这种民族品格不是指那种带有调侃意味的形象标志,如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浪漫、德国人古板等,而是正面的并且为该民族所自豪和追求的。我并举例说对英国人而言,这种民族品格就是绅士风度,对德国人而言,就是好学深思,对美国人而言,就是探新求变。对中国人呢?我提出就是“士”的精神。这种精神起始于春秋时期,就是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忧国忧民、终身以之的强烈的责任心。这种精神到后来通过各种语言表达出来,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鲁迅的“中国人的脊梁”等等。在做学问上,就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严复的“了国民之天责”,陈寅恪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可叹的是,随着百年来不加分析地否定传统,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些优秀东西正在被人们忘却。而在治学上对“科学主义”实为工具主义、技术至上的盲目追捧,也使钉位之学成了“科学”的代名词。在这个大气候下,“博士之学”日增、“士大夫之学”日亡,就是必然之事。年轻一代更不知士大夫之学为何物。借着《杨自俭文存》的出版,让我们循着杨先生的学术道路,重温何谓“士大夫之学”,对于治疗我们的学术浮躁病,未尝不是一剂良药。
所谓“士大夫之学”,我以为至少包含以下五个方面,而杨先生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第一,为人重于为学。
这是士大夫之学的灵魂、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就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大学教育奉行科学理性主义,实际上忘掉了这个根本,许多现象因此而起。这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吁这一精神的回归。但在我的印象中,至少在当今外语界,在各种场合呼吁做人重于做学问的可能没人超过杨自俭。例如2002年上海会议上,他以《老实做人,认真做事,严谨做学问》为题致了开幕词,强调学者要进行长期认真的自我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特别提出“要始终无条件地追求较高和最高的层次”、“要正确认识自己”、“要积善成德”、“要慎独自律”,并告诫大家永远记取、领悟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并付之行动。2004年重庆会议的开幕词上他强调会风的重要,“它是学人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问题,它是学人的伦理道德和精神境界问题,它能决定学人的学术价值与生命。”2006年烟台会议上,他特别总结了他与学会创会老会长刘重德先生刻意培植和发展的会风,其中第一条就是“高尚的道德与情操……为人为学为人在先,学术为重,淡泊名利,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杨自俭这么要求别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大家都知道,他是当今中国外语学界、特别是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界众望所归的学界领袖,靠的是什么呢?在广博的学识和明锐的学术眼光之外,我觉得更主要的是靠他几乎难以阻挡的人格魅力。而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学术界目前最匮乏的东西。
第二,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如果说人格修养是士大夫为学的第一步,则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就是士大夫之学的鲜明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优良传统就是时刻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历史的使命紧紧地结合起来。前些年在总结严复的翻译思想时,我曾感叹说,像严复那样把从事翻译当作“了国民之天责”的人,现在恐怕再也难以找到了,甚至他的这种想法也已经很难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了。因为在工具理性主义的人们看来,翻译不过是个谋生工具或者是个人情绪的泄发,所需要的无非是技巧或方法而已。同样的,学术研究已被论文发表的要求所取代,后者更已成了敲开各种名利之门的敲门砖。当手段成了目的,还有什么事不能做的呢?因而当今学风的败坏是从知识分子人格的沦丧开始的。杨自俭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表现出对当今社会世风、学风的各种忧虑。在2006年的烟台会议上,他更形象地将之比喻为“三座大山”:“第一座是官本位”,“第二座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第三座是‘重使用轻理论的传统”。他忧虑地说:“毛主席领导我们用了不到30年推翻了那三座大山,但这三座大山恐怕用50年甚至100年也难以推翻。”正是由于有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才会对所研究的对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读这本《杨自俭文存》,你会感受到他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在关注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如何真正解决中西结合问题,二是如何真正解决古今继承问题,三是如何解决学术创新问题,四是如何解决理论应用问题。可说,这四个问题已涉及到了学术研究的全部,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作出如此深刻的思考。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出“字本位”的例子,这是杨自
俭近两年学术思考关注的焦点。有时人们可能会纳闷,作为一个主要活跃在外语界的学者,为什么对汉语界这个争议未决的问题有这么大的兴趣?其实字本位理论正好是杨先生所关心的四个方面的问题的汇合点或者说聚焦点,杨先生从徐通锵等人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语言学根本问题解决的希望,也看到了中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新的前景。而这个理解,不循着杨先生自己学术发展的思路是难以做到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收在本文集的《跟随徐通锵先生学习字本位》一文,对于了解杨先生为人治学有着分外重要的意义。
第三,广博而深邃的学识。
正如上面说到的,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的基本区别是通识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区别,也是中国传统治学与今日急功好利的所谓“搞科研”的区别。《中庸》上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两千年中国士人所奉行的学习方法。古人深知“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重要性,因而强调治学过程中的“于书无所不窥”,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自勉。古代的例子不胜枚举,近代的经典例子有曾国藩和梁启超,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做出重大成就的原因。直到五十年代初,吕叔湘还在告诫我们,翻译工作是“杂学”,译者要“竭力提高自己的素养,有空闲就做一点杂览的功夫”。但半个多世纪来,随着学科分工的细化、知识的海量“爆炸”,特别是西方细分再细分那种分类和描写方法的引进和备受推崇,“博学”、“通才”已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人人都盯着眼前那一小块,细挖再细挖,分析再分析,例如把一个“了”字分析出十几种、二十几种用法,似乎这才是“科学”的研究。然而,“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没有广博的学问做基础,专学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杨自俭是当代学者中少有的明白人之一。他曾对对比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过六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比较丰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基础知识;二是英汉语言及其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三是英汉语言史及其语言学史;四是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包括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五是方法论基础(包括哲学、逻辑学、系统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方法等);六是对比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相信很多人看了这个单子都会吓一跳,以为这是凡人不可达到的高标准。但实际上,了解杨先生治学道路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他治学经验的宝贵总结。我们在读杨先生文章的时候,常常会为他深邃的洞察力、气度恢宏的学术视野所折服,其实道理很简单:站在山顶看山和钻在山沟里看山,得到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我还想特别提到杨先生的逻辑修养,我以为,在当代外语学者里,还没有什么人的逻辑学水平能超过杨自俭先生,这是他的论述总是那么细密、那么有说服力的原因。
第四,高屋建瓴的治学眼光。
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使杨自俭在从事具体学科的研究时,站到了一个常人难以达到的制高点。因而他的学科研究也就有了一个与旁人不同的眼光。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杨先生的学术研究,关注的始终是学科建设的全局和最宏观的方面,诸如学科的性质、学科的定义、学科的基础、学科的地位、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学科的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学科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建设、学科的发展趋势、学科的广泛应用等等。无论对英汉对比语言学、翻译学、对比文化学、典籍英译、语言理论、字本位学说等,均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国内外语界公认的一位学术领袖。许多人新书出版,都爱请他作序,他的品评,常能道出作者自己所没有发现或感受不深的内容,对作者自己也不啻是个升华。我本人就为此受益不少。同时,作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深受爱戴的老会长,他不止一次发起全国性的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学科建设讨论,为推进国内这些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各种会议作的开幕词、闭幕词,常常是对学科发展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总结,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五,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
阅读本书的目录,读者还可能注意到,在全书所收的80篇文章中,为他人著作写的序言倒有39篇,占了几乎整整一半。这在当代国内外学者的论文集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有人为他感到惋惜,觉得他孜孜不倦数十年,多数时间是在替人作嫁,却没有时间写一本他自己的学术专著。而按他的学术水平,如果有充分的时间,不要说一种,就是两三种专著也早就出版了。这就涉及到他的另一种可贵的品格,也是传统士大夫的品格,就是淡泊名利。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样的说法。《老子》也强调:“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曾国藩总以“功成身退,愈急愈好”告诫自己,强调“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虽然前人有这么多的榜样,但老实说,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下,真要能这样淡泊自如,还真的不容易。而杨自俭先生却做到了,这还成了他的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如上所说,国内学者出书,喜欢请他写序,以之作为重新认识自己著作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杨先生对请托者,一向来者不拒,他把它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倒也不是过度的谦虚话,我发现,常常一篇序言写成,作者研究的这一领域也就成了杨先生的囊中物了。他认为这是两得益彰的双赢好事。我们常常见到,他写的序言,不同于一般作序者那样三言两语,敷衍搪塞,而是在精读、细读了原文之后,提出了真正精到的见解,使读者包括作者自己茅塞顿开。他的序言常长达一万余言,这大约也是国内外非常少见的。但这样的做学问方式,在今天环境下,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成果都是别人的,自己的研究再深刻,也只是贡献了一篇“序”而已,既进不了“核心期刊”,也算不了“学术成果”。但这样的事愿意常做,而且做得其中有乐,也只有杨自俭那样完全淡泊了名利的人才行。杨自俭说,他特别喜欢三首诗,认为表现了做学问的境界,这里我也把它抄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第一首是唐代李翱的诗句:“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这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治学而忘我的境界。第二首是李白的诗句:“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窖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一种脱离了世俗的敬业的境界。第三首是王国维的《浣溪纱》:“本事新词定有无,斜行小草字模糊,灯前肠断为谁书?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区区情事总难符。”这是学术研究永不完善永无止境的境界。我们引这三首诗词,既以之表示对杨先生治学精神的敬意,也希望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