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样教我
刘 吉
理查德·费曼曾对原子弹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1988年因患癌症逝世。下面的内容摘录于他的著作《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当我还坐在婴儿椅上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带回家一堆小瓷片,就是那种装修浴室用的各种颜色的东西。我父亲把它们堆起来,堆得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小瓷片重新堆起来。这次,父亲让我变出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行了?他爱在哪儿加个蓝,就让他加好了。”可我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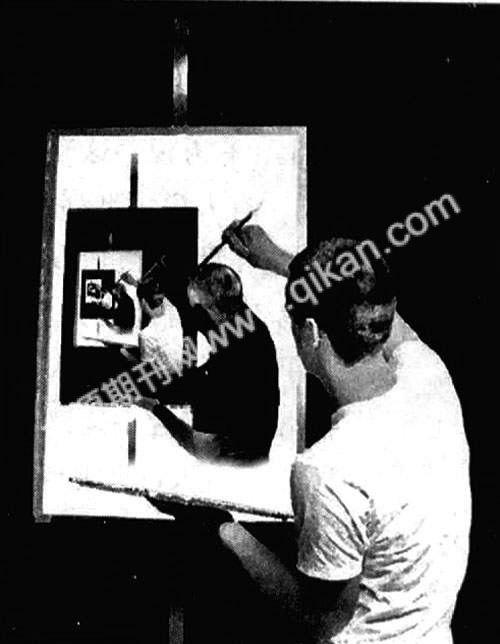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让我读里边的章节。有一次读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父亲对我说:“让我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的脑袋比窗户还宽呢!”我想象居然有这么大的动物,而且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极了,新奇极了。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任何书上的内容,我都要琢磨出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我于是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事物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事物”的区别。
我长大了一点后,有一次,父亲摘了一片树叶。我们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个C形的坏死的地方,从中线开始,蔓延向边缘。“瞧这枯黄的C形,”他说,“在中线开始比较细,在边缘时比较粗。这是蝇,在这儿下了卵,卵变成了像毛毛虫似的蛆,蛆以吃树叶为生。于是,蛆每吃一点就在后边留下了坏死的组织。蛆边吃边长大,吃的也就越多,这条坏死的线也就越宽。直到蛆变成了蛹,又变成了黄眼睛、绿翅膀的蝇,从树叶上飞走了,它又会到另一片树叶上去产卵。”同上一例一样,我现在知道他说的细节未必对,没准儿那不是蝇而是甲壳虫,但是他指出的那个概念却是生命现象中极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终的目的。不管过程多么复杂,主题却是重复一遍又一遍。
我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爸爸,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而我停住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因为运动的物体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样。”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摩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没错。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进行兴趣盎然的讨论,没有任何压力。这一直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 物理教学探讨·初中学生版的其它文章
- 寄语物理科学的新生代
- 夜为什么是黑的
- 神秘月球
- 宇宙的未来之旅
- 科学家也会搞错的问题
- 光武器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