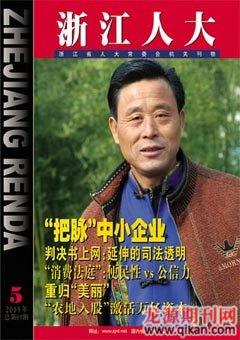官员外逃之内省
季卫东
最近几年,“官员外逃”事件日益增多,让人不免感慨系之。这种趋势与举国上下公务员考试热不断升温的场面相映成趣,形同钱钟书先生描述的“围城”现象,构成了一道很奇特的政治风景线。
是范蠡功成身退与西施泛舟江湖的古老传说影响太深远,还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教训太沉重?莫非政府里陶渊明式的人物突然多了起来,都玩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游戏?查看这些案例,可以发现:其实什么都不是。只剩下经济犯罪者试图避免惩罚这一最低级的动机而已;只剩下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赃款被转移到别国这一最简单的事实而已。
不言而喻,与这种“官员外逃”相伴随的,还有国家财富的两次大规模流失:首先是损公肥私,然后再“吃里扒外”。因此,有关当局不能不加强防范,加强制裁的力度,并在反洗钱、反贪污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08年春天开始,主管部门加强了对因公出国的审查和限制。针对妻儿携产移民、官员“裸身从政”的问题,舆论界甚至还有不给官员亲属出国护照之议。但不得不指出,诸如此类的禁令可是涉嫌侵犯人权的,也不利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而且,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文化氛围里能否真正行之有效,也还要打个很大的问号。
换个视角来观察,贪官污吏纷纷挂冠遁走,倒也未必就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当反腐败运动加大力度、动真格时,政治嗅觉敏感、消息灵通的官员就会作出与地震前小爬虫们类似的异常反应,而首当其冲者就更会感到恐慌,赶紧逃之夭夭、躲避风头,或者至少是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对于政府而言,这是敲山震虎的必然后果。
另外,在民主法治理念渐入人心的过程中,特权势必受限制,官越来越不好当了,所以对外逃的心理障碍就将大幅度减少。一旦腐败分子大量退出,官场的风气变得比较清新,在人事方面的“劣币驱逐良币”趋势会被扭转,政治改革方面的一些重要举措(例如高级公务员财产申报制)的推行也就比较容易畅通无阻了。排出污浊、引入清流,这也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个方面。
对无数官员前赴后继地贪污、受贿,然后背井离乡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恐怕不应该仅以私欲或个人品质为理由来解释。但无论如何,“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现在到了重新审视那个岿然不动的“庙”——结构框架,或者制度——的时候。而在制度设计上探讨解决官员经济犯罪和外逃问题,最关键的是争取形成某种合理的机制,让官员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沿着贪渎之路下滑,因而也就无须外逃。
所谓“没有必要”,是指薪俸足以养廉,待遇优越,而纪律极其严明,导致犯罪的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如果违法所得较小、所失太大,当事者自会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作出合理抉择,没有必要再对他三令五申,没有必要把监督机构弄到重重复重重的程度。反过来,假如官员的行为方式和人生只是像黄仁宇教授在《万历十五年》里所描述的海瑞那样:“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那么,防止“裸身做官”、“官员外逃”的举措就很难普遍见效。
所谓“没有可能”,是指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前提条件下,对罪行的揭露比较及时、制裁比较公正,让人不敢心存侥幸。在这里,与其强调严打重罚,莫如强调违法必究,尽早尽量地破案起诉。另外,在这里,政治信息公开和表达自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暗箱操作的状态为上下其手留有大量的机会,私下交易和“一言堂”则构成贪污受贿的温床,对由此产生的组织败坏,只有透明化的阳光才是最佳防腐剂。为此,有必要敦促有关部门尽早制定政府伦理法,把公开高级公务员的资产和收入状况作为其中的核心内容。
在确保“没有可能”贪渎方面,各种检查、监督、审计制度等当然不可或缺,但这些机构必须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威慑力量,不能停留在行政部门内部自我监察的水准上。否则,就难免流于形式,无论叠床架屋多少层也不可能收到显著成效。
为了加强对官员权力的制约,首先必须把选举、票决以及协商等民主决策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官员真正对人民负责的体制。其次,要落实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确保法院和检察院严格按照法律处理案件,对任何人都不偏不倚。再者,还可以通过把行政系统内部的监察机构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尤其是立法权和监督权以及法院的审判权相结合,或者改进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等方式,使之具有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面对外逃讲内省,只有在上述条件充分具备之后,“官员外逃”才会重新成为例外现象,而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携产移民的社会问题,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也才得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