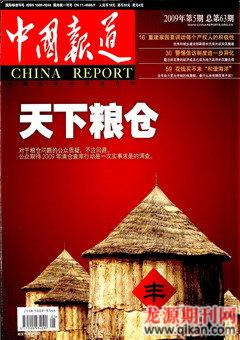百年国图尽沧桑
“百年馆史”不仅是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因为在这一百年里,国家图书馆的命运和国家发展密不可分,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国运昌,馆业兴”。
2009年9月,国家图书馆将迎来百年华诞,其前身成立于1909年的京师图书馆。
李致忠先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从此与国家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他与这座图书馆相伴走过了44年的风雨历程,如今已年逾古稀。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先后担任过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业务处处长、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在时代的跌宕起伏中,李致忠先生与国家图书馆难舍难离。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驾乘着版本研究的一叶扁舟,从此岸到彼岸,痴心不改,深情不变。
访问李致忠先生时,他主持的国家图书馆“百年馆史”编撰工作已近尾声。在他眼里,“百年馆史”不仅是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因为在这一百年里,国家图书馆的命运和国家发展密不可分,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国运昌,馆业兴”。
馆名更迭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名京师图书馆,创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9月9日。16年后。馆名始发生变化。
1924年10月,经美国政府同意,在中国特设“中华教育炙化基金会”池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来专门管理美国退还的第二笔“庚子赔款”放年确定此项资金当用以“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
为贾彻上述决议案,1925年10月2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与中国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舍办“国立京师图书馆”。11月26日,教育部发文,谓“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暂移北海地方”。京师图书馆馆名由此第一次变更。
中基会与教育部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初,进展十分顺利。双方契约中明文规定,建设专门图书馆馆舍的建筑、设备乃至未来的购书费用100万元,完全由中基会承担,这是开女的大宗。而日常费用每月5000元,则由合作双方各任其半。但彼时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国库空虚,中国教育部难以女特每月2500元的日常经费。
1926年初,中基会致函教育部,声明在教育部未能履行契约以前,应即暂缓实行契约:“而原定计划中之图书馆,则暂由董事会独立进行,并改名为北京图书馆。”此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图书馆”有本质的区别。
1927年,国民政府决议改“北京”为“北平”。7月,南京大学院通知京馆“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北平图书馆”。如此,京师图书馆又改名为“北平图书馆”。而中基会独办的“北京图书馆”只好于是年10月改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
1929年6月,中基会在天津举行第五届年会,会议接受当时中国教育部长蒋梦麟的提议,继续执行前北京教育部与中基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契约,将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再改“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北京图书馆”。50年后的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于9月9日举行90周年馆庆时正式改称为“国家图书馆”。
馆舍变迁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京师图书馆归教育部领属,并于当年8月27日在今什刹海东北隅的广化寺开馆。此为国家图书馆最早的馆舍。可是开馆不足两个月便闭馆待迁,因教育部“部议本馆馆址湫隘卑湿,不宜存贮图书”,并派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鲁迅会同王懋镕等馆员另谋他址。
经过鲁迅等人将近5年的努力,到1917年1月26日,才又在安定门里方家胡同原清代国子监南学旧址开馆。此为国家图书馆历史上的第二处馆舍。
国于监南学馆舍总计房屋119间,较广化寺宽敞得多,但四周民户杂居,火灾隐患较大,井不利于消防。且办馆12年,因此地偏居京城东北一隅,交通不便,读者寥寥,而不断遭到批评。故到1928年10月,又将方家胡同馆南学馆舍改为京师图书馆分馆,而将本馆则迁至中海居仁堂,于1929年2月重行开馆。
居仁堂原名海宴楼,是庚子年慈禧跑到西安回来后所建,专为招待女宾之用。门外陈列12生肖兽首人身像。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后在此办公,于是将该殿改名为居仁堂。此为国家图书馆的第三处馆舍。
中基会与教育部于1925年合办图书馆后,双方契约中有100万美元临时费,专供馆舍建筑、设备及购置书籍之用。后经中基会筹备建设,1931年5月20日,图书馆新馆在今文津街落成,“该馆以绿瓦红墙围绕,体量高大……门内庭院开阔,环境疏朗……总体权衡与细部做法基本合乎则例,是此类设计中比较成功的一座”。
是年6月2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开馆典礼,蔡元培馆长专程从上海赶到北平主持开馆典礼,教育部等机关官员、国内外学术单位代表、名流学者、社会贤达以及各国驻华公使等近2000多人前来参加开馆仪式,盛况空前,轰动一时。国家图书馆第一次有了专门的馆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图书馆(当时尚未更名,称为“北京图书馆”)发展很快,虽然在原地又扩建了书库,并先后新建了三栋小楼,但总起说来,与书刊增长速度不成比例。政府虽先后拨借神武门楼、北海松坡图书馆、故宫西路寿安宫、柏林寺等,作为北京图书馆藏书之地,但书分多处。管理不便,阅览不宜,加之周围环境复杂,更构成了安全威胁。
1973年10月29日,图书馆老馆扩建计划呈送到周恩来总理面前。总理看后指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但因当时尚处在“文革”当中,无法落实总理指示。
1980年5月,刘季平馆长向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作了关于图书馆工作的汇报。在同年6月1日发出的《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写到:“关于新建北京图书馆问题,会议决定,按原来周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一位图书馆馆长能够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是非常罕见的,刘季平馆长对国家图书馆的影响。前无古人。
1983年9月,图书馆新馆在风景秀丽的紫竹院公园长河北岸破土动工。邓小平为它题写了馆名。1987年新馆落成后,总面积达14万多平方米,设有3000个阅览座位。国家图书馆进入跨越式发展的阶段。
2001年,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获准立项,并于2008年6月竣工,9月9日开馆。这样,国家图书馆就拥有了25万多平方米的专门馆舍,成为亚洲第一大图书馆,排在世界第三位。
缴送制度承传
1916年3月6日,教育部片奏北洋政府,要求饬下内务部,凡立案出版之图书请该部分送京师图书馆庋藏。北洋政府同意了
这个请奏。这是京师图书馆接受国内出版物缴送的开端,也由此奠定了中国图书出版缴送的最初制度。
1929年10月14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呈文教育部转咨内政部,要求内政部修订《著作权法实施细则》时,增加新出版图书寄存平馆条款。几经周折,教育部基本答应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合理要求,从而保留了图书馆接受呈缴本的资格。
1955年4月25日,文化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颁布的关于书、刊缴送的法规,再次明确当时北京图书馆接受缴送的资格。
一年以后,文化部修订全国报纸缴选样本办法,对县市及县市以上单位、各地厂矿及高等院校所出版报纸的缴送。做出了明文规定,当时北京图书馆同样享有此项受缴的资格。至此,北京图书馆对国内出版物有了全面接受缴送的权利,建设国家总书库的天职光荣地落在了国图肩上。
改革开放后,出版体制虽无多大变化,但出版机制不断创新,各出版社缴送出版物状况良莠不齐,为此,新闻出版总署从国家大局出发,不止一次发文,要求各级各地出版社,及时如数地向国家图书馆缴送各自的出版物。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版介质不断更新,电子出版物层出不穷,新闻出版总署亦适时发文。规定缴送制度,确保国家图书馆的受缴权利和国家总书库建设。
藏书建设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成立于1909年。但到1949年,也就是在40年的时间里,虽然迭经馆员百般搜采,到北平和平解放时,所积累的藏书也只不过140万册(件)。不过,虽然京师图书馆藏书增长可谓慢如蜗牛,但其藏书品类、文种在当时还算齐全,形成了国家图书馆初期的藏书基础。
从1950年到1978年,藏书净增755万册(件)。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跨越,但还不能跻身世界发达国家图书馆的行列。而到了2008年底,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总量已经达到2700万册(件),较1978年以前的藏书总量增加了1800多万册。这是何等惊人的速度!
世界上任何类型的图书馆,尤其是国家图书馆,其藏书量的增加,最本质、最重要、最有效、最可靠的还是源于政府对购书经费的不断增加投入。
1978年,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的国拨购书经费是210万元。第二年,亦即1979年,国拨购书经费是275万元,比上一年增加了65万元。而到1988年,国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图书馆紫竹院新馆也已经落成开馆,读者量陡增,书刊流通量成倍增长,这一年政府财政拨1655万元,专供国家图书馆购置书刊报等文献信息资源。1998年,政府下达给国家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已到了8000万元。而到2008年,国拨购书经费已达14500万元,是1978年购书经费的69倍。国拨购书经费逐年增长,正是国家图书馆藏书量倍增的根本原因,也是国家图书馆藏书建设赖以传承的生命线。
60年记忆
1966年“文革”之前,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干事业,图书馆的工作围绕着业务部门进行,后勤为一线服务的态度非常好,整个环境很和谐。
这一方面是因为刚刚解放,中国进入百年来少有的和平时期,大革命胜利的优势继续鼓舞着老百姓,人心非常痛快;再者,建国后,国民经济恢复较快,国家在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特别重视科技发展。
解放后的第一任馆长是曾任东北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的冯仲云。他虽然不懂图书馆业务。但每次布置完工作,就会深入各个业务组,和大家一起工作,领导与员工打成一片。
那段时间,图书馆的馆藏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善本书,很多藏书家生怕落后,纷纷向图书馆捐书。也有不少是在国家领导人的女持下“枪教”而来的。
香港名重一时的藏书家陈清华,家底殷实,热爱藏书。解放初期,他出现经济困难,开始出售自己的藏书。当时,也有外国人盯上了这些书。时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是这方面的行家,一再呼吁抢救这批善本,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在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总理果断决策,于1955年和1965年两次斥巨资从香港购回陈清华的藏书,拨交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收藏。
国家图书馆曾是名家辈出的图书馆,如编馆藏方志目录的谭其骧,编中国小说书目的孙楷第,图书馆学大家王重民、刘国钧,研究中西交通的名家向达,以研究晚明史料著称的谢刚主等,都曾是国家图书馆的员工。
我到图书馆工作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间,图书馆因动乱而闭馆,接待读者数量为零,1971年以后才逐渐恢复开馆。“文革”初期,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阐述收集“文革”材料的意义,后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派专人出去征集传单和大字报,“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现在就收藏在我们馆里。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效益也越来越明显。国家图书馆本来是承担着类似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功能。但我们的国情是图书馆少,所以国家图书馆现在承担了很多社会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但不管怎样,从事图书馆事业的人,理所应当把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作为自己的目标。
采访后记
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我—直在心里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不是回溯国家图书馆百年历史,我们对博尔赫斯的活不能更深刻的领悟。
在历史变化奇诡的20世纪,国家图书馆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可是,在百年的沧桑巨变中,无论境遇如何变迁,无论名称如何更改,它却始终犹如—座屹立在人们心中的灯塔,以知识的光芒照亮着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
如果没有和李致忠先生的交谈,我们对博尔赫斯的话也不会有更微妙的感触。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李致忠的生命和国家图书馆及善本书建立起难分难舍的关系。当他讲述自己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见到平馆当时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102箱善本书时,眼中莹润着泪水,几近哽咽着说“不谈了,不谈了”,让听者感到心痛难抑。
因篇幅有限,对国图历史上的人和事,难免挂一漏万,不失是—种遗憾。但希望所记录与书写下来的这百年嬗变中的点点滴滴,不止是一段冷冰冰的历史,而是充满温暖和人性的一段回忆,并能够借此,对所有以赤子之心热爱图书馆事业并奉献终生的人们,表达我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