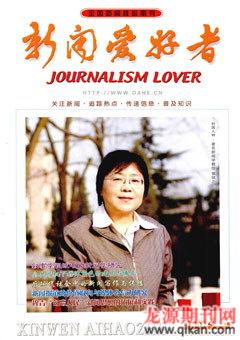李浩然《新闻报》短评初探
吴 霞
摘要:李浩然,《新闻报》总编辑,主持《新闻报》笔政30年。《新闻报》,解放前沪上最有名的商业化大报之一,和《申报》齐名。本文集中考察了“五四运动”发生后李浩然撰写的新评,并将之和同时期的《申报》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看出对于李浩然这样一位近代职业报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作为。
关键词:五四运动李浩然《新闻报》《申报》
李浩然,《新闻报》总编辑,主持《新闻报》笔政30年。《新闻报》,解放前沪上最有名的商业化大报之一,上世纪20年代前后,销量超过老牌大报《申报》,成为遍布上海大街小巷的“柜台报”。发生在90年前的“五四运动”,影响深远,是中国的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四精神更是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众多的关于五四时期新闻传播的研究中,常被提及的是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一些进步的革命报刊的论述,对于像《新闻报》这样资产阶级的商业化报刊,它们的言论经常被无意忽视,或是置若罔闻。但它们在“五四”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着怎样的作为,对于李浩然这样一位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报刊事业、评论事业的近代职业报人,对五四事件,又抱着怎样的态度,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李浩然,188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府成阳县庇礼村(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庇礼村)富绅之家,和著名报人张季鸾是同乡,幼年时又与张季鸾同学于关西大儒刘古愚。19世纪末留学日本。1910年,李浩然在上海协助于右任、宋教仁、邵力子、张季鸾、杨千里、沈缦云等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民立报》,开始步入新闻界。1911年5月,李浩然受聘进入《新闻报》,最先担任日文编辑。1913年开始担任《新闻报》总编辑,主其笔政,直至1941年年底上海租界沦陷后毅然去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任《新闻报》秘书一职。1947年,李浩然在搭乘电车上班途中遭遇车祸去世。
从时间上看,李浩然从1911年进入《新闻报》,一直到1947年逝世,在《新闻报》工作达36年之久,主持《新闻报》笔政则为30年。李浩然去世后,于右任为其所书墓碑是:“新闻记者李公浩然之墓。”诚然,“新闻记者”确实是对李浩然一生的最好评注。
李浩然除了主持《新闻报》编务外,还每天针对当日发生的时事撰写短评和时论,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古朴清丽、可读性强和感染力大的评论文章。这些时论、短评,在当时有“北张(季鸾)南李(浩然)”之誉。在李浩然进入《新闻报》的第9个年头,发生了近代中国史上最为著名的五四事件,此时的李浩然担任《新闻报》主笔不过两年,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作为当时沪上销量最大的报纸的主笔,李浩然在这一阶段撰写的新评,从文体、时间和内容上都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文体上:标题规范直观,开创短评新文体
民国初年,当很多报纸还在热衷于以长篇论说为号召时,《新闻报》就别出心裁地将长篇的社评改为“新评一”、“新评二”、“新评三”的短评,篇幅短小,文字简练,由此一来,不仅形式新颖,让读者耳目一新,内容也变得更加通俗易懂,深受民众的欢迎。五四事件发生时,李浩然以总编辑的身份,执笔每日的“新评一”,篇幅不过二三百字,但短小精悍,字字针砭时弊。如1919年5月6日的新评《示威活动》,全文虽只有184个字,但不仅明确指出当局“利令智昏,始终不悟”,告诫当政者“民不可欺”,更敏锐地看到“若以扬汤止沸为能,则事变所极”。
同一时期,陈景寒以“冷血”为署名负责《申报》的时评。单从标题上看,李浩然的新评标题更规整。多以四字或五字的形式出现,而冷血的时评标题就显得随意性,有时仅以一个字为标题,有时标题义多达八九个字。除了直观上的字数不同外,两者在选取以何为标题时,李浩然多以评说对象为题,例如1919年5月6日、7日发表的新评《示威活动》、《北京戒严》,读者可以从中一目了然地知道评说之内容。而《申报》的评说则更多地以作者的论点作为时评的标题,如5月7日的时评《解散大学之无识》,比起李浩然直观、朴实的标题,陈冷血的标题显得更有政论色彩。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跟“新申”两报不同的办报理念有关。《新闻报》是以“经济新闻”为立报之本,总经理汪汉溪经常向编辑部同仁表示:“上海人口以从事工商业者为最多,我们办报,首先应当适应工商界的需要。”而工商业者,多喜好用短时间获取更多的资讯,李浩然用规范、一目了然的标题正是应了这批受众的喜好。而《申报》是一家着重政治新闻的综合性日报,它的评论标题具有更浓厚的政论色彩也就不足为怪了。
时间上:当天事当天评,注重报纸评论的时效性
五四事件发生后,《新闻报》几乎以每天一篇短评的速度,尽力做到当天事当天评。针对6月1日发生在武汉的学生遭军警殴打的“六一惨案”,李浩然于当晚就撰写相关评论,读者在6月2日一早的《新闻报》上就能看到这篇新评《对待学生》,开篇指出,“政府对待学生”,“乃一变而用高压手段,不得要领。不过于事无补,则大背今日人心趋势”。认为武汉学生的行为出发点单纯,“然在学生方面之发动,敢断言其无党争关系”。并进一步告诫政府“实告政府诸人,今唯有顺应人民爱国之精神,努力奋勉,为自全之策”。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闻报》客观上说还是一张注重广告收益的“柜台报”。广告与新闻必须经常保持六与四的对比,即广告占六成,新闻占四成,新闻版面有限。因此,具有时效性的“新评”除了阐发观点,表明立场外,有时也兼具了新闻的特质。如在1919年5月29日发表的新评《益世报停刊》中,李浩然除了在文中明确指出政府“对于赞助学生之报纸,加以摧残”外,在结尾处还加上该事件的最新进展“自此事发生,美领馆即提抗议,旅京外国人士亦联名保被捕之记者,仍无结果”,比起《申报》在6月2日刊出的新闻《益世报事件近闻》,李浩然的这篇新评可谓“先声夺人”。
内容上:有理有据有节,理性思考下的激进态度
虽然这一时期李浩然的短评还带有明显的“文人论政”的特点,但相比较之前文人们“以极端之议论出之”、“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手法,李浩然的短评显得朴实而冷静,常常是援引材料,多角度分析。例如在1919年5月8日刊发的新评《对内与对外》,开篇中就提到:“今日之事,对内对外当分别进行,而对外尤重”,“对内诸事,则因对外而发”,并进一步分析到,“我国主张苟不得当,即勿签字,质言之,则不啻表示吾国有退出和会之决心。事已至此,吾国固当由此表示”,最后得出结论“此其成败虽不可必,但我国方面,苟可以尽一分力者,必须分离前进。公理战胜强权之声,方弥漫于全世界,不应毫无效果,时不我与”。
从时间上而言,除了评论的对象是新近发生的事件之外,文章还对进一步发展的时局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预测。这样就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有了作者自己理性的延伸,同时也让读者有了强烈的新鲜感。
除了注重理性思考外,这段时间李浩然的评论也显得相对“激进”。马光仁在《上海新闻史》中写道:五四群众反帝运动,也激起了在政治上一向落后保守的大报的爱国热情。这里就包括当时上海滩上的两家大报《申报》和《新闻报》。同时马光仁也指出,这两家旧时大报在这段时期的表现还是有所不同的。
比起《申报》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发表的没有倾向性的社评,《新闻报》的表现可用“激进”来形容。同样是5月6日发表的评论,同样以“青岛问题”开篇,相比陈冷血所说的“青岛问题,至于今日,国人不能无一种表示之态度,此为各国常有之事,亦人类共有之性”。李浩然所写的“青岛问题,于吾国为生死关系,日来警耗迭传,举国愤骇”。就显得激愤得多,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笔者认为,激进的文字更能起到振聋发聩之效。
总结
还原《新闻报》在五四事件中的表现,有学者分析,它之所以在这段时期表现激进,与之前保守大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此时的《新闻报》还是一份外商的报纸,在美商福开森的名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针对国内政局敢于比较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固然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原因。但同时,作为报纸的总编辑和主持笔政的主笔,李浩然在五四事件发生后,通过笔端表达出的理性思考下的爱国热情,同样是这一时期商业化大报评论中的一抹亮色。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