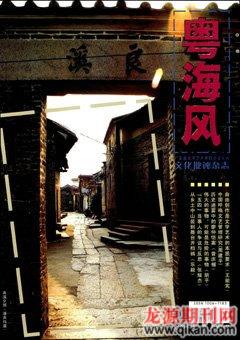“五四”的双重记忆
叶 开
关于“五四”,似乎包含着起码两种以上的记忆形象。
我个人从小的记忆,是北大的少年英豪翻墙而入痛打外交官和“火烧赵家楼”的光辉形象。这个形象,跟革命的热情相结合,非常壮美,而渐至于水泊梁山那些好汉们剜心吃肉的大气概了。还有一种是文化革命的形象,好听点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意见是“全盘西化”。到底是西化成什么样子?是白化还是赤化,有待争论。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化”。
“化”这个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意义最明显:两个人反向对偶相背,有如后来的太极图。转动起来,则渐至于无物。所以,“化”是很高深的学问,但是弄不好,却会搞成上海人说的“捣浆糊”。20世纪80年代之后,最能明确的是“现代化”,而且是四个。“现代”一词,听起来非常悦耳,但是什么是“现代”?现代的好处是什么,短板又在哪里?却缺乏认真的分辨。
记得去年十月在北京开会,严家炎先生就我发言的一个纰漏,在会后吃饭时,很认真地给我进行了“启蒙”:“打倒孔家店”这口号不是“五四”时期提出的,而是胡适的发明。他在为《吴虞问文录》写的序言里面说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人”。严家炎先生是严谨的前辈学者,他把《新青年》全都翻过,没有看到“打倒孔家店”的字样,且形成了论文,而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这个学术成果。严家炎先生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写文章发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评论》上,跟美国的林毓生教授商榷“五四”问题,可惜没有得到林毓生教授的响应。严家炎先生的这个研究成果,是要证明“五四”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意思。盖因“五四”以来,激进思潮越来越热,想到什么都是“全盘”,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接受,没有中间过度。这跟传统的“中庸”思想,固然是彻底的不妥协了,中国到底要去往哪里?却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90年代而至于今日,我们似乎仍然在兜圈子,打游击,玩小孩子藏猫猫游戏。
20世纪80年代,在反思上也有点狂飙突进的意思,曾达到过一些深度。
总体来讲,学界都执著于好与坏这种角度,而不去深入反思其背后的深层思想原因和这种思考的角度的利弊得失。林毓生教授去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研究院讲课,谈韦伯的“Ideatype”,说他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五四”,发现其中有一个致命的死结,即鲁迅等先君子既出于旧文化,又如何能够彻底超越?
不管怎么说,按照严谨的学术逻辑来反思和按照放火烧楼的角度来想往,是绝然不同的角度。猫吃鱼,狗吃肉,各有所好,和而不同,有什么不好?一定要强令人人都往暴力上和狂人上模仿,未见得是明智之举。
“五四”这样一个双重的运动,具有丰富的双面性,后来的思考远远不够,也不深入,更谈不上彻底。
大陆某作家撰文呼唤“狂人”,以为这个社会不够完美是因为缺乏“狂人”。而事实上,现在的“狂人”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暴力的“狂人”不说,文化“狂人”更是不计其数。对知识的学习上,大多是暴力思考模式,是革命的思考模式,是推翻前人,重打江山的好汉帮的气概。文学如此,文化如此,莫不如此。这一代人,总的来说,记忆中的“五四”就是个暴力的、火烧的形象。而对于其中的“文化运动”,不甚了了。
“狂人”不是新鲜货,鲁迅早就呼唤了。唤出什么来了?斜着眼睛看人看世界,都是恶人坏人,是吃人的世界,对传统文明成就的一棒子打倒,再踏上一脚。“五四”的激愤青年,在推翻旧有的一切时,倒洗脚水连孩子也泼掉了。“五四”后二十年,学界不无反思,反思得似乎还很深入,胡适之劝人们“ 多干实事”,很多实干家去调查乡村,搞乡村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也有人对“火烧”进行了法理上的批评。这些反思,可惜后来都被彻底中断了。 以至于现在反思“五四”,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是火烧赵家楼的美丽猛烈,是英雄好汉武二郎手刃二十来人的动人形象。一把火烧掉,这是爽快的事情,从秦皇到项羽而至于破“四旧”,放火的事情,不可谓不多,但是爽快之后,一片废墟。
而所谓“五四”,除了“火烧赵家楼”这个动人的英豪型男魅影之外,还有“新文化”反思中输入并且早就被中断了近半个世纪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徒具形骸,而无实质进展,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现在的“赛先生”,似乎活得有点滋润,且要扶正成为主义和唯一的观念了。然而,“赛先生”一人独大,未免寂寞,且缺乏根基。最重要的“德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现代化的最重要内涵,到底是“赛先生”还是“德先生”?我不故意做摇摆,我明确地觉得还是“德先生”。没有“德先生”,要达到“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谈何容易?“德先生”是土壤,“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是果子和果树。
传统的现代化还是现代化的传统,都绕不过“德先生”,没有“德先生”做根基,“赛先生”越滋润,就越可能滋生狂妄和暴力。
“五四”既是一个旧话题,也是一个崭新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