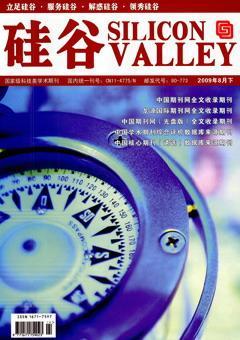浅议青海民歌“花儿”
顾 潇
中图分类号:J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09)0820200-01
青海“花儿”是青海广大劳动人民都很喜爱的一种民歌,不论男女老少谁都能哼唱。“花儿”不但有丰富的文学内容,也有极其绚丽多彩的音乐形象。自2002年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以来,各地热情高涨且成效显著,要做好花儿文化生态的保护,应当在对传统花儿、花儿会等遗产进行保护的同时,深入了解花儿的起源,花儿的音乐特征,使青海花儿得到继承与发扬。
一、青海花儿的渊源
青海是花儿的故乡,河湟花儿是西北花儿的精魂,最美的花儿是用三江最纯净的源头之水浇灌的圣洁之花。居住在这里的汉、藏、回、土、撒拉等各族群众,无论在田间耕作,山野放牧,外出打工或路途赶车,只要有闲暇时间,都要漫上几句悠扬的“花儿”。可以说,人人都有一副唱“花儿”、漫“少年”的金嗓子。青海农民唱起“花儿”,村里的张秀花、王富贵们就会泪水涟涟。花儿对青海人来说象每天的饮食一样普通。
花儿又名少年。花儿是产生于青海,并流行于青、甘、宁、新等地区的一种山歌,唱词浩繁,文学艺术价值较高,被人们称为西北之魂。花儿发源于临夏,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加之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北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六盘山花儿就是其中的一种。回族群众喜爱花儿,是花儿的创造者、演唱者、继承者和传播者。花儿是心头肉,不唱由不得自家,可见回族对花儿的喜爱程度。流行于固原地区的花儿主要有两类:河州花儿和山花儿(俗称干花儿)。河州花儿委婉动听,基本调式和旋律有数十种,变体甚多。形式上有慢调和快调。但是,固原回族多唱山花儿。山花儿在旋律上起伏较小,较多地应用五声羽调和角调,衬词衬句使用较少,段尾或句末用上滑音。在文学上除具有河州花儿的一些特征外,还派生出一些变体,有时也采用信天游或一般民谣体。演唱形式有自唱式和问答式。曲目无令之称,属抒情短歌。花儿音乐高亢、悠长、爽朗,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鲜明。用比、兴、赋的艺术手法即兴演出。虽然大部分花儿的内容与爱情有关,但在歌颂纯真的爱和控诉封建礼教及社会丑恶现象给恋人造成生死苦难的同时,深刻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语言朴实、鲜明,比兴借喻优美,有比较高的文学欣赏和研究价值。20世纪80年代,花儿的演唱形式已发展到花儿歌舞剧。
二、青海花儿的音乐特征
(一)花儿的唱词格律
1.花儿的唱词格律。“花儿”奇特的方言组词造句功能,奠定了花儿唱词不同的凡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格律基础。一般来说,四句式、折腰式和连缀式是“花儿”唱词基本的结构形式。
四句式的“花儿”(也称“头尾齐式”)是最典型的一种“花儿”,每首四句,分为上下两段(民间俗称“上下联”),每段由上下句组成。
“折腰式”也叫“折断腰”或“两担水”,是在四句式“花儿”的上下句之间加入一个半截句(腰句),通常为四个字。加在四句式上段的上句与下句中间,叫“上折腰”,加在下段,则叫“下折腰”。半截句的加入增强了连接性,丰富了表现力。
“连缀式”是把四句式、折腰式唱词用对唱、时序和叙事的形式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对唱式是花儿的基本演唱形式,演唱时通常用问答的语调连缀。
2.句子的节奏。“花儿”的基本节奏是:一、三句是九字,四顿,最后是单音节落尾;二、四句是七字,三顿,最后是双音节落尾。另外,折腰式节奏和节奏性衬字花儿唱词因记录人而异。
3.“花儿”唱词。“花儿”讲究“顺口”、“易唱”,所以押韵得当是很重要的。一般情况下,“花儿”唱词有五种押韵形式,即通韵式、交韵式、间韵式、随韵式、不押韵。通韵式是花儿中最常用的,即每句均押,一韵到底,有尾部单押、双押和多字押等形式。在押韵中,尾字押韵字为“实”字,因与传统诗歌的韵法相同,故被称为“实字押”,而尾字由“虚”字担任(如“哩”、“了”、“过”、“者”、“的”、“呢”等),一字通押的称为“虚字押”。
(二)花儿的调式、旋律
1.“花儿”的调式。“花儿”大多系单一调性的单一调式结构,采用“五声音阶”调式。在调式中又以商调式和徵调式为普遍。五声中“宫”、“角”、“羽”三音,表现出活泼不稳定的性质,它们对于曲调的进行与扩展有着强烈的推进力。而“商”和“徵”两音则具有静止的性质,各个音以各自的性能形成强烈而又自然的倾向性和稳定性。无论音调怎样发展变化,“商”和“徵”两音总是象一块磁铁吸引其它各音。此外,还有六声音阶的(如《下四川》)、七声音阶的(如《上山令》)等,但通常这种情况很少见到。
2.“花儿”的旋律。花儿的旋律通常有“单峰式”和“双峰式”两种。比如土族花儿《好花儿山令》,即是由两个五小节的乐曲构成的单曲式。如果两个乐曲都是先从低音开始,级进上升到调式主音“2”之后,以九度大跳急转直下,前后形成两次起伏,成为“双峰式”状。花儿的节拍多采用二拍、三拍、四拍等形式,有时也有节拍交替出现的现象。
三、青海花儿的继承与发展
“花儿”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艺术,也是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美的产物。在人类社会中,美与善总是相随相伴的。“花儿”之所以有它永不消失的魅力,就是因为它揭示了人民群众生活和心灵上美与善的内在联系。因此,对于“花儿”,我们应该从民间文学的特点来认识它、分析它、研究它、欣赏它,继承和借鉴它的营养价值,并找出它形成的原因、发展的规律,探索其文学、艺术、音乐、语言乃至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及美学方面的价值。
“花儿”虽具有高亢激越的高原特色,但也有不少曲调的基本情调和性能是以表达叹诉压抑,凄怆怨慕的感情为主。这从曲调的趋向可以看出,大都是下趋形式,结尾很少“上挑”。既使从唱法上加以变化,也还是改变不了这一基本情调。很显然,这种调型和情绪的形成,往往与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以及婚姻不自由这一社会历史根源是分不开的。“花儿”音乐大都是单一调性的单曲体结构,不易叙事,一支曲调一段词,或多段词上套用同一曲调,这种曲体形态以及唱词上的四句式,七言字的传统格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花儿”音乐的发展,这对表现今天人们的生活,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曲调情绪的下趋与忧怨这一旧时代留给“花儿”的深刻烙印和今天时代人们的生活节拍、艺术欣赏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外,今天的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今天的青年男女享有婚姻自主的权力,这与传统“花儿”创造者们所处时代也有着根本区别。
当然我们认为,“花儿”在音乐、唱法上也要推陈出新,不能墨守成规。我国历代的诗词,从旧体发展到新诗,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当然首先要根据内容的需要,要在“花儿”原有的格律基础上进行,保持和发扬“花儿”原有的艺术特色。否则,就会弄巧成拙,群众也不会承认。鉴此,应当根据社会和“花儿”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对“花儿”进行加工、改造,从而赋予新的内涵。这样“花儿”将会在新的时期得到新的发展。
在未来的日子里,青海花儿,这只独树一帜的艺术奇葩,定将发出越来越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