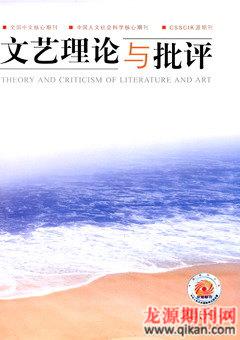不一样的世界
鲁太光
除了结构张致、语言通透、人物鲜活、故事周全等因素外,笔者以为,洞察力也是优秀中短篇小说的必要因素之一。在今天我们这个“思想淡出”而生活又急剧变化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素质显得尤为重要。具有洞察力的作家,往往能够穿越现象看到本质,因而能够在作品中通过对人们“习见”的生活的描摹而呈现人们因太过熟悉而“不见”的故事、情感和思想。换言之,即营造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令读者读后耳目一新,思维活跃。
近期,笔者就有幸读到了三篇有洞察力的中短篇小说。
第一篇:薛舒的《摩天轮》
要想观察中国,特别是观察风起云涌风云变幻的现实中国,是需要一个恰当的角度的,如果找对了角度,那么这个观察就具有了纵深感和高度,其中的现实感和戏剧性自然纷至沓来,引人入胜。在《摩天轮》中,作者就将我们放置到摩天轮这个自改革开放以后就在中国都市空间中到处“生根发芽”、激情旋转、风光无限而今天又渐趋式微,面临被淘汰命运的道具上,使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在多个交织的层次上,看到了不一样的社会风景。
小说的叙述框架其实是“谷贱伤农”的传统文学主题的“再现”。当然,作家写的不是农业时代先是粮食丰收,再是粮价大跌,最后是农民没有粮食吃的悲惨故事,而是匠心独运,将这个前现代语境中常见的文学主题移植到现代乃至后现代语境中的今天,写由于大规模征地而由一位菜农“升级”为一家大型游乐场摩天轮操作员的王振兴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了30年,却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免费)坐过一回摩天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了三十年弼马温却从未骑过亲手养的马”或“做了三十年菜农却从未吃过自己种的菜”。他不是不想“骑自已亲手养的马”、“吃自己亲自种的菜”,他也经常想。有一次他甚至已经“骑”上了“自己亲手养的马”——坐上了摩天轮,可“假洋鬼子监督员”的出现以及老板“游乐场人员不得假公济私,违者辞退”的“严令”吓得他立刻猫腰钻进了缆舱的座位底下,直到双脚踏回地面,再也没敢让自己的头露出来。此后不久,他的表兄王德华因违规让老婆孩子坐自己看管的“急流勇进”被发现而被辞退的例子,让他既暗自庆幸没有被发现,又后怕不已,这种失败的经历,使他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同时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中——既时不时地想挑战成规,又时不时地为这成规所警醒,所规训。
王振兴这个“弼马温”的失落固然令人感慨,然而结合小说无处不在的暗示,比如谈恋爱时,王振兴的女朋友张芳“误以为”外国老板如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一样,允许职工家属免费享用职工的浴室、食堂、班车等福利,因而顺理成章地把游乐场“误称”为王振兴的“单位”,并要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去游玩一番。再比如,王振兴的表哥王德华违规被发现后,“外国老板可没有心情来批评教育违纪的人”,“直接就炒了王德华的鱿鱼”,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写王振兴的失意其实大有深意,即通过时空对比,使我们在回想起往昔岁月的温暖记忆时,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谷贱伤农”的故事是发生在新时空里的,因而具有不一样的意义——与以往常常是苛政(权力)猛于虎不同,如今资本(内资和外资)似乎成了新的“猛虎”,冷冰冰的,与“苛政”一起,成为压制社会的力量。这为故事向纵深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历经30年的风风雨雨,人们对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急剧转换的不适感(比如想当然地把“外资企业”称为“单位”)渐渐消失,人们的心理也在这不适感的消失中渐渐转变,并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心理。《摩天轮》对这一转变也做了出色的挖掘。
与王振兴由战战兢兢转为任劳任怨。由任劳任怨转为沉默无声,并在沉默中由外向内地积攒着不平的力量不一样,他老婆张芳的心理转换是由内向外的,是由无声向有声,由有声向大声转换的,特别是当她与丈夫一起“参观”了昔日游乐场的开除员工今日城市蔬菜基地总经理王德华为“二奶”购买的豪宅后,她的不平彻底爆发了:先是自怨自艾,怨自己当初嫁错了人;再是恨上了王振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他既没有当上官,也没有发了财,害得自己跟着他一起吃苦受累;最后,她竟然“仇富”了,恨起了表哥王德华,恨他向自己炫耀财富;恨起了跟自己住在一个小区的园林局局长和他老婆,恨他们张扬,恨他们骄矜……
在作家细腻的笔下,这“恨”是如此的微妙,既包含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又包含了对生活不公的无边愤恨,甚至还包含了不合时宜的“弃暗投明”的心思——张芳对王德华的二奶和楼下园林局局长夫人所过的“神仙日子”的向往即为有力的暗示。
作家的功劳并不仅仅在于呈现了“底层”心理的复杂和微妙,而更在于坐在摩天轮上,举着望远镜,引领我们,揭开笼罩在社会“中层”和“上层”身上招摇舒卷、温情脉脉的面纱,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生活中的腌臜、“拮据”、无聊和颓废的心理状态,从而相对完整地揭示社会心理。大款王德华开宝马,住豪宅,包二奶,似乎风光无限,可这风光背后,隐藏的却是堕落和百无聊赖,想一想他的菜农出身和被游乐场开除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这风光是怎样的“悲剧”——这是“底层”背弃自身的悲剧,是财富脱离精神的悲剧。更可悲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老婆跟踪而来,来抓二奶了,于是一个被背叛的女人的悲剧与一个被包养的女人的悲剧纠缠在一起,演化为一场我们看不见却又时时处处在上演的“闹剧”。在张芳眼里,园林局局长的老婆也够风光的了,整天打扮得像一朵胖嘟嘟的塑料花,气喘吁吁地吆喝着到处撒欢的小狗,不亦乐乎!可就是这个“快乐”的女人给园林局局长戴了“绿帽子”,而且似乎又面临着被“新欢”嫌弃乃至抛弃的境地了——又是一出家庭的悲剧,社会的闹剧!
正是这一系列无声的悲剧和闹剧组合在一起,使我们不无痛苦地意识到:正如小说里那架突然停顿的摩天轮一样,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运转、一度风光无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之后,我们的社会这架巨大的“摩天轮”似乎也耗尽了自己的能量,运转不畅,因而需要停下来,重新积蓄能量,并考虑新的发展路径。
或许,这就是我们坐在“摩天轮”上看到的风景之深意?
第二篇:萧笛的《老毕的艺术人生》
“毕老师”原来不是“老师”,而是“老毕”;他的人生原也不是“艺术人生”,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是用破筛子网和乱毛线头做成的别致的脚踏垫,是用青霉素瓶粘成的红鱼绿树,是春节时挂在家门口的走马灯,是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在院子里堆的雪人、雪屋子以及在畜牧站院子里堆的雪马、雪猪、粗手宽脚的雪老汉、奶大臀阔的雪娘儿们……
老毕的日子原本过得活色生香。因为他心灵手巧、多才多艺,在家里,老婆疼,孩子爱,煞是滋润;在外边,也是人人夸赞,个个羡慕,好不快活。然而,一位城里来的女摄影师
罗西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她先是改变了老毕的名称——使之由老毕变成了“毕老师”,并进而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之由过日子变成了“艺术人生”,因为,她给老毕堆的形形色色的雪人、雪屋、雪动物起了一个新名字——雪雕,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命名。而且,这一命名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机缘巧合,牡丹江市举行雪雕大赛,县艺术馆推荐老毕去参赛,并捧回了一个大奖。为了给老毕庆功,县艺术馆在城里最有名的满江红酒馆大摆庆功宴,席问,县委副书记、分管文化的副县长先后给老毕敬酒,按老毕的说法,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一口一个“毕老师”地叫他。就这么着,老毕成了毕老师,成了小镇的“艺术家”。
成功地改变了老毕的命名后,罗西又来改变他的“气质”了。原来老毕总是西服领带,板板正正的,可罗西却认为老毕的打扮“太屯”,并劝他说:“毕老师,你理在是艺术家了,要有艺术家的气质。”在罗西指导下,老毕换上了牛仔裤,在花花绿绿的毛衣外面,罩上了一件像罗西那样到处是兜的马夹,头发也刻意不剪,留长了,披在耳后,而且,自此之后,他言必谈“艺术”。
命名和气质变了,老毕的心思也变了,由“做人讲究”的“爷们”变成了风流才子,时时“在别人的田里摘个瓜弄个枣啥的”,“有时,就是不动人家的瓜果,在人家的地头溜达溜达,品评一番,想象一番,感觉也挺恣儿的”。(此处是作家对老毕拈花惹草生活的幽默讽刺)他的“艺术人生”由此开始。
这样的变化虽为老婆林茹所不齿,但在小镇人心目中却仍情有可原,但严重的是,就像化学反应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一样,老毕的心思一旦发生变化也一发而不可收拾。当得知罗西离异后,他的心竞不仅离开了老婆林茹,而且离开了乡里的“红花绿草”,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好看的护士石静,而一味地系在了罗西身上。在小说中,这是一个有意味的信号,暗示老毕想离开乡土进入都市了。当然,是在情感和精神上进人,而非在身体上。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老毕开始“双线作战”:一方面是痛下决心,断绝同石静的暖昧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殚精竭虑,想给罗西一个惊喜,给她做一只天鹅雪雕,“艺术”地表明自己的心曲。然而,由于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老毕必然“双线溃败”:一方面是“后院起火”—-_林茹在心怀嫉恨的石静“点拨”下吞服了大量安眠药,想造成自杀的假象,将老毕从罗西身边拉回来,然而由于阴差阳错,林茹意外死去,石静也落入法网;另一方面是一头撞在了南墙上——老毕按照自己想象中的艺术标准(都市的标准)做的天鹅雪雕,不仅没有博得罗西的任何好评,而且简直被贬得一无是处,被贬成了一只呆头呆脑的大笨鹅。这暗示着尽管老毕做了“脱胎换骨”的努力,但他与罗西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因为,说到底,在罗西眼中,老毕其实像他手造的雪雕一样,不过是乡土文化的另一种存在而已,而老毕眼中的罗西,也不过是都市文化的一种幻象,离“真实”还远得很呢!
果然,林茹死后,当老毕不顾风言风语向罗西表明心意时,罗西不仅断然拒绝了他,而且满腔鄙夷地抨击他,“根本不是搞艺术的料”,因为别看他“头发长了,衣服换了,可是脑袋没换”!经受不住双重打击的老毕疯了,每天说着同一句话,见谁跟谁说,一遍一遍地说:“你帮我换换脑袋吧,你帮我换换脑袋吧。”至此,小说终于剥除家长里短的外衣而露出要探讨的严肃的社会主题一城乡断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城乡之间的“双重文化误读”。
由于启蒙主义和新启蒙主义话语泛滥,多年来,城乡间的文化关系一直笼罩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阴影下。近些年,虽然有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这一论调进行批评与反拨,但其影响仍根深蒂固,其重要表征就是在文学叙述中,每当涉及城乡文化关系时,农村多是“被看”的一方,农民也多以“愚昧者”的面目出现。
《老毕的艺术人生》是少有的以平等眼光严肃观察城乡文化关系的小说,尽管语言是幽默的。事实上,由于城乡间的文化断裂,在作品中,以罗西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和以老毕为代表的乡土文化在彼此观照时,由于视角的差异,恰如灯塔虽然能照亮远方的黑暗,却无法照亮自己脚下的黑暗一样,因而往往“以己度人”,无法全面观照对方,甚至误读、误解对方。比如,在罗西眼中,乡土文化就是老毕雕的那些质朴夸张的雪雕,而非活生生的老毕以及老毕活生生的情感,或者说,即使老毕进入了她的“法眼”,但本质上却是以雪雕的形式进入的,而非鲜活地进入。而在老毕眼中,城市文化就是罗西的举止所展现的随意、大方与“多情”,而非其中蕴含的自由、真诚以及暗藏其间的“分寸”。就是这样的双重误读,导致了理解的徒劳,并最终酿成悲剧。这样的探讨,不仅超越了单向度的文化立场,而且提醒我们要以反思的眼光看待自己立身于其中的文化,并由此出发去理解别样的文化,而非“东方主义”式的文化“猎奇”。其意义可见一斑。
第三篇:范小青的《我在哪里丢失了你》
小说虽不足万字,却如一根犀利的银针,一针见血,刺穿了为“名片”所遮蔽的“熟悉的陌生”。
在人际关系成为人力资源成为生产力,成为潜在的“敲门砖”或“摇钱树”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空前地“熟悉”起来,于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或典雅或朴拙,或名贵或廉价的名片,如铺天盖地的雪花一样,分发起来,传递起来,飘舞起来……于是,小说的主人公王友先后遭遇了两次令人难忘的“名片事件”。一次是一群萍水相逢的人凭名片“开路”觥筹交错热热闹闹地大喝了一场,在离开酒店的路上,其中的一位顺手把“杜中天”的名片扔掉了,王友看到杜中天就在身边,为了避免尴尬,于是捡起名片并提醒扔名片的人说他丢了名片,而丢名片的人却浑不在意地说这张名片不是丢的,而是故意扔掉的。而当杜中天恼羞成怒,一把将名片夺过来撕成碎片扔了一地后,他仍振振有词地表示无所谓,说晚扔不如早扔,因为这名片没用。这张名片的故事,使我们知道了“功利”和“势利”的含义。另一次是一位老太太凭一张捡来的名片将王友“骗”到她家,并说王友是他已故丈夫最好的朋友之一,王友虽然万般疑惑,但却不得不随着老太太“回忆”自己和她丈夫之间发生的一些趣事。这张名片背后这个荒诞的故事,使我们明白了热闹背后的“冷漠”和“孤独”的真意。
由此,一张名片的正反两面都昭然若揭:正面是“功利”和“势利”,背面是“冷漠”和“孤独”。由此,名片这个本应用来为联系提供方便为熟悉提供便利的道具变成了互相隔膜的障碍。由此,一个令人痛心不已的问题油然而生: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人情社会”中,在张张或心照不宣或心知肚明或言不由衷或怀揣心事的名片背后,有多少真正的感情被遮蔽了,有多少鲜活的人被遗忘了,又有多少真正精彩的人间故事被忽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