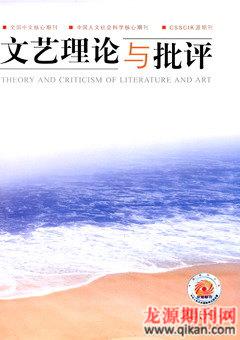关于鲁迅的问答
主持人:我想问张教授两个问题,第一个关于鲁迅先生的《伤逝》的小说,他写这篇文章前后心理上的变化以及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和变化,您怎么看鲁迅先生这篇作品对他以后思路和创作的改变。第三,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对鲁迅的认识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现在鲁迅过时了,不用去看鲁迅的文章,但是也有更多的人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了鲁迅的文章,觉得又回到了作品描述的那个时代,我们今天怎么样重新认识鲁迅,怎么样看待他的文章。
张旭东:《伤逝》是我很喜欢的作品。很多人把它作为爱情小说来看,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它是借用自由恋爱的悲剧,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一个虚无和虚无的克服的问题,我在别的场合讲过,所以今天就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读法。小说一开始是悔恨,回忆当时是这么开始的,“我”一个人坐在这个会馆里,一切又是这么空虚、这么无聊,当年子君来的时候,“我”有期待、有向往,生活充满了希望,“我”是仗着子君逃出了空虚,这句话很关键,也就是说涓生是启蒙的醒了的青年,但是在中国的现实里却是无路可走,在非常敌意的现实里,一切都是空虚,寂寞,他想抓住一个什么东西走出空虚。子君,女性,爱情,是借一个实的东西,逃出空虚,最后发现她逃不出去,回归了空虚,最后子君死了。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一点,以前争论也很多:这就是涓生是否代表一种男性的精神性的往前走的启蒙的理性逻辑,这种启蒙精神负担不起子君这样一个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儿童般的幼稚所代表的累赘。大家知道最俗套地讲,两个人理想地恋爱之后发现这个女人变成了一个负担,成天问你“还爱不爱我”等等,另外还有外地人生活的不便、失业等等,最后涓生抛弃了子君,但他是不是在悔恨这个决定、这个行为呢?在这个小说里这是一个让人费思量的问题,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不能掩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空虚、虚无主义的克服,克服虚无主义的失败的问题。这是一次爱的失败,但是涓生的斗争,并不限于爱的范围,也无法从爱中得到最后的证明。只有在克服虚无主义的意义上,他说,“我”必须要向新的生活迈进,“我”必须要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句话是非常令人费解的,为什么要用遗忘作为前导?克服虚无是一个假象,但是人不能没有这个幻象,人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信念,人只能以这种方式,依然要遗忘,——不遗忘就要背着这个负担,——就像尼采说的,创造性的遗忘,创造性的幻觉,通过这个你才能实现你的价值的创造,也就是新生,最后他是用新生这个乌托邦的希望的语言来跟虚无对峙。对于《伤逝》,我基本上倾向于读出一个思想、观念,并不是把它作为实实在在的小说,里面所有关于爱情的部分都非常俗套,非常程式化,作为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家,这不会是他用力的主要方面,他并不是要写出一个栩栩如生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是一个幌子,最后解决的是另外的问题。这次回国我才知道有人说主题不是男女爱情,而是兄弟失和,是他和周作人的关系,我倒没看出这个问题,但作为一个旁证,对我的东西有一点点意义,至少说爱情这个故事的结构是一个幌子、一个设置,主要的矛盾是在另外一个层面。
第二个问题说鲁迅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不能简单地把鲁迅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比较,因为中间隔着一场中国革命,某种意义上,这在鲁迅那儿是希望的、形而上学的,是以杂文的形式、以诗的形式、以梦想的形式出现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的确越来越多的人就走了那条路,这条路真的走出来了,不能忘掉中国革命是成功的。中国的左翼思想或者进步思想和西方的左翼思想或者进步思想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只有失败的经验,没有成功的经验。中国的左翼思想是有成功经验的,我所接触的包括我非常尊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激进的思想家,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毛泽东以前批评过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或者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他们确实缺少一种组织路线,缺少人民、国家、人民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等等,他们有个人思维上、理论上的革命性、批判性,但他们从来没有过成功的经验,没有过一件事是从几个书生读了几本书开始闹革命然后做成了,换了人间的,他们没有这个经验。鲁迅的梦想其实是中国革命替他实现了,这点不能轻描淡写地带过,也不能忘掉,这是前提。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从窗户里看出去,看到的只是一个商业化、资本化的社会,一个官僚资本的社会,一个各种各样的沉渣泛起的社会,旧的东西又回来了,那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大时代”。鲁迅有一个“大时代”的概念,大时代就是面临生死抉择的时代。如果今天我们又面临这样的观念,当然是跟鲁迅的时代有非常深的关联性,不是表面现象,不是一对一似的,关键是深层意义上的。即使在这层上我也不认同又简单地“一觉回到解放前”等说法,因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业化包括改革里,留下很多制度性的、体制性的、经济基础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感情方式,日常生活领域的很多基本建制并没有完全被打掉,和非西方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有很多非常得天独厚的条件,要不然即使纯粹的市场经济改革也不会成功那么快。并不是说简单地一下子回到解放前或者1925年、1927年,种种被鲁迅深恶痛绝的活在人间的那种黑暗、压迫、那种挤的痛,早已为大众革命打掉了、消灭了。李泽厚说革命是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1980年代的诗都是这么写的,包括谢晋的《芙蓉镇》在去革命化路径上走得很远,但是谢晋谈到新旧对比是毫不犹豫的,他完完全全赞成新社会,反对旧社会。还有一个对比是“文革”,“文革”不能再来了,“文革”是十年浩劫,谢晋的矛盾就是既强调了新旧对比也强调了十年浩劫,所以他有矛盾。我的意思是说,鲁迅的那个世界被革命的世界彻底地改变了,但是改变以后的中国,知识界尤其青年学生,正因为生活在一个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比较干净、比较无菌的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里,包括我们都没有帝国主义的直接经验、没有关于殖民主义的直接经验、没有剥削的直接经验、没有金钱社会的直接经验,因此,我们今天一点点地仍然在学,仍然对新的社会的变化感到震惊,我们都被大众革命、被社会主义革命给打磨了,我们这代人包括我们的上代人,更不用说现在的80后、90后(80后这次抗震救灾有了一个翻身),没有免疫力,没有面临过这样的问题。今天的社会是一个被大众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性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环境,现在忽然门窗打开。改革嘛,就是把门窗打开,苍蝇肯定是要进来的,不开不行,我们当时都是赞成的。但现在门窗四面都打开了,全球化、接轨等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体制化、专业化,使得一个原有的,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遗产,在共时性的空间里,同时和各种各样的力量并存。这种接触,在某些局部我们确实能感觉到鲁迅当年描述的东
西,比如说鲁迅有一篇《再谈香港》,结尾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的香港不怎么时髦,1949年上海的国民党的姨太太跑到香港都在抱怨找不到人打麻将,比上海差远了,但是鲁迅去香港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了。什么意思呢?中间是洋人,他的周围围着富裕华人、买办,再外面是黑压压的无声的大众,上海以后就会这样,全中国以后都会这样。现在全中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上海差不多是这样的,中间是洋人,外国跨国公司,最贵的房子,这个倒不见得是上海市硬性规定洋人只能住在市中心,这是市场行为,房地产价位就把人分散开,劳工阶级都是住在外环,中环以内是白领,最内层、最贵的楼盘是在新天地,就是一大会址,“新天地”是共产党开辟的,“新天地”现在是上海所有白领的地盘,相当于三里屯、后海酒吧,上海的“新天地”房地产就相当于后海周围盖了一圈高楼,非常贵,一平米11万,我们这儿的职工是买不起的,所以只能是洋人和一部分富裕华人,这是非常明显的,房地产业空间意义上已经形成了。但就整个中国来说,哪怕就上海来说,是否就回到了那个时代,也不应该这么说,问题就是共存、并存,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语言体系、不同的阶级立场,处在这个膨胀空间的竞争中。今天我们一方面是比鲁迅那个时代要好很多,在主权意义上,在国家体制的意义上,在很多具体的意义上,当然比鲁迅那个时候好。今天除非是非常激愤的人才会说中国差不多完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比现在要好。另一方面也有不如鲁迅那个时代的,我们今天无论是思想、学识、道德,还是政治意识的坚毅程度,远远比不上鲁迅,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锻炼出来的,天生有这样的免疫力,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知道自己跟谁打,知道自己痛在哪儿,病在哪儿,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仍然在观念上、在意识上、在价值上、在政治上处于一个没有免疫力的状态、没有反思的状态,很多问题没有痛感。今天的人没有痛感不见得说属于胜利者,还是属于嗡嗡翁,还是被新的东西的、新奇感或者被钱、被物质的膨胀,或者被种种的机遇诱惑,还是处在一个眼花缭乱的状态,还没有能够像鲁迅的眼光那么毒辣,一眼看到对手的真面目,马上回敬,以牙还牙。这种意识没有。也就是说在政治性上,我们差得太远了。一代不如一代,比如说在文学史、学术史上,年轻一代,1980年代的人,在文化主体性意义上,比不上老一代人,老一代比不上解放前那批人,再这么退化,基本上就要退化到头了。今天的现实有现实的矛盾、现实的阶级分化,各种各样的冲突应该让越来越多的人睁着眼睛看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开始有痛感了,开始对这个人间有新的理解了。这个人间,一方面我说了,比鲁迅时候好,另一方面不是很单纯的东西,也是非常复杂、非常不合理、非常黑暗、非常让人欲哭无泪,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倒不觉得鲁迅是个神,碰到什么问题立刻就要回到鲁迅时代,拿鲁迅的话来说,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并不是这样的。鲁迅也只能解决鲁迅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但我们从鲁迅那儿可以学到人怎么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获得一种真实的观照,获得一种真实的意识,取得一种真实的强硬的立场,这一点就是读鲁迅的文章的意义。
听众:最近有一部电影《鲁迅》,不知道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但是我觉得如果过多地强调鲁迅很柔的东西,鲁迅是多疑、泼脾气,我猜想是不是想把鲁迅真正有力的东西给消除掉,是不是想把鲁迅的文化层次降低到温文尔雅,让鲁迅丧失危险性?鲁迅看到肯定会非常不满。
问:1990年代关于鲁迅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你是争论的重要一方,能否请您对这场争论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与评价。
张旭东:我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论争,但我当然站在鲁迅一方,鲁迅是一个试金石,所有想颠覆鲁迅、柔化鲁迅、淡化鲁迅、消解鲁迅的人,往最坏里想,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背后都觉得鲁迅硌得慌,又臭又硬,这种东西最好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推到最后会有意识形态的政治含义在里面。但有些东西也是属于我刚才说的意识形态上的,去政治化以后带来的幼稚或者纯粹的好奇心,那种新奇感带来的副作用。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成天就是鲁迅鲁迅,都烦了,哪一天忽然读了钱钟书,很有意思,或者读了胡兰成,觉得胡兰成、金庸比鲁迅伟大。但是这个都长不了,这都是一时的,因为鲁迅在人间、在人生扎得很深,这是其他人无法比的。把那些东西跟鲁迅硬要拉在一起,是这个时代的文化乱象。今天也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这种乱象里,该争论的就争论,该辩驳的也要辩驳,你得承认他们确实有市场。因为我们读鲁迅的时间,除了马列就是鲁迅,除了红色经典以外唯一的全集就是鲁迅,这样无形之中它就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年轻一代会有逆反心理,这个也可以理解。而且现在文学各方面都专业化,觉得文学就要是不朽的东西,你看鲁迅的书随便一翻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都是短兵相接的,跟人打在一起,搅在一起,鲁迅的形象就不太光辉,跟人揪着头发,脸上是别人的吐沫、鞋给打掉了、衣服撕破了、脸被抓了,是这么一个形象,灰头土脸的打仗的形象,那些很高雅的博士生做论文,而且要去美国读学位的,当然觉得这个不够艺术,形式上不够莎士比亚。这么一来的话,又有另外一种逆反心理。我们今天的生活还能不能使得我们理解鲁迅意义上的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鲁迅还是能被人理解的。
我不想说得太强硬、太过分,今天的生活确实是往好的方向走的,我们应该承认。我倒不希望死抱着一个东西,拒绝一切的丰富性、多样性,这个是不好的。现代生活的多样性会产生新的可能的受益者,多样性会带来新的社会的可能,并不是件坏事。今天说鲁迅并不是要强迫你,不是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也不是搞高校排名,鲁迅一定要排第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现在读鲁迅的话是否还能读出来,能否读懂,能否跟你的生活经验发生关系,并不是说以鲁迅去压制喜欢读张爱玲或者喜欢读金庸的人,现在你爱读什么就读什么,但如果最终回到知识的思想的政治性的争论的话,在争论的最根本、最高的层面,有些话必须要说清楚。
问:一方面文学对革命没有做什么,一方面鲁迅又在不停写作,这怎么解释,这个矛盾造成后期鲁迅杂文的什么特点?
张旭东: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还是回到《革命时代的文学》,这篇文章很多人都读过,都很熟悉。第一段,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这是他前面讲的,有实力的人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幸而不被杀的就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待他们,这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鲁迅当然不是说文学没有用,而是说文学对于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用,他想的是文学对开口就杀人的东西还有什么办法,鲁迅并不是说事情永远都是这样的,而是说在
今天的中国是这样,他说,“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著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这个说得很挖苦了,想想很可怕,我不希望这次救灾活动完了以后,大家能记住的就是“范跑跑”或者什么山东作协副主席写的“纵做鬼也幸福”那种诗,那样就很可悲了。
这里鲁迅否定了看上去很对的,而不幸的是后来的左翼文学理论和官方的文学理论也一直在推崇这么一种,就是所谓的“宣传为革命”的遵命文学,鲁迅后来讲的文学不是那个意思,“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最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善革命”,毛泽东在一次延安座谈会上讲话,一定程度上也有这个意思,这个讲话是为了军队文艺工作讲的,说文艺是要为革命的军事斗争、社会工作做贡献。鲁迅说,“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这也是夫子之道,他虽然写这样的东西,但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从心里流露,但流出来的就是杂文,你说“我”是写杂文好呢还是写那种14行诗或者莎士比亚诗好?你让“我”选哪一个?鲁迅说“我选杂文”,鲁迅的文学定义是这么定的,定得要比文学更深。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又何异于八股?鲁迅这代人包括周作人,他们对八股是非常提防的,怕又做回八股里,革命八股也是八股,毛泽东不就批评党八股吗?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改变什么了。“革命期间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积极,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鲁迅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就是革命人了,但是在他跟现实的紧张关系,在他不得不写这点上,文学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他说得非常明白,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他用的是豪猪的比喻,但他又不会打架,文学是他唯一的武器。这两者完全不矛盾,因为鲁迅没有说过要参与革命的军事斗争,他始终是非常本位地做自己的文学工作。为什么不停地写作?解释非常简单,是他活着、存在着的唯一方式,写作证明他还活着。一方面文学对革命没有做什么,一方面鲁迅又在不停地写作,这两者同时造成鲁迅后期杂文的什么特点?这个我再想一想。我对鲁迅后期杂文还没有想完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回答。
问:我们知道毛泽东对鲁迅曾经做过很高评价,但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了一本书,他里边披露了一个历史事实,毛泽东在1950年代的时候曾经说过,鲁迅要么关在监牢里继续写,要么识大体不说话,后来《南方周末》也发了这样一篇文章,谈到这句话。我想听听您怎么评价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的关系。
张旭东:我不知道毛泽东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是在什么上下文里说的。但是毛泽东对鲁迅是真的推崇的,我认为鲁迅的乌托邦,是毛泽东把它变为现实的。在这层关系里,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深的,不是直接意义上的,是乌托邦和现实的关系。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毛泽东是在行动的领域里考虑问题,政治对毛泽东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事,鲁迅归根结底是个文学家,是一个“作为作家的斗士”。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使他们两个人的很多考虑又会不一样,但是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我觉得毛泽东的原话说得很到位:“鲁迅没有一丝一毫的媚骨”,这就是毛泽东最欣赏的东西,因此鲁迅头上文学家和革命家、思想家这些封号也是当之无愧的。这样的话放在谁身上谁都担当不起,郭沫若、茅盾都承担不起这样的东西。鲁迅对民魂的执着,不是感伤主义的。毛泽东也不是简单的一个民族魂,两个人的精神气质是非常相通的。
至于当今对鲁迅和毛泽东的种种所谓“走下神坛”的评价和臆测,我只能说:仆人眼里无英雄,但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人只是仆人。英雄不是完人,也无需我们去帮着造神,我对文学研究和文学阅读里的“鲁迅教”或“鲁迅腔”向来是不耐烦的,但在最起码,在所谓的“时势造英雄”的意义上,我们总应该在时势的条件下去把握、理解什么造就了鲁迅,使鲁迅成之为鲁迅的吧?还有一个更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我们今天仍然爱读鲁迅。这里又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鲁迅仍然不断地在同我们说话,同我们的时代说话。二是鲁迅的说话方式或语言方式,在我们对中国语言和语言本身的理解上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前面一点是鲁迅意义的历史决定,后面一点是鲁迅意义的非历史决定。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语言都不需要鲁迅了,那鲁迅自然会“寿终正寝”,不是几个做文学批评的可以起死回生的。
问:在上个世纪鲁迅和毛泽东之间,我觉得从鲁迅的角度来讲,他很聪明,他发现问题的能力比较强,能够针对这个问题的实质直接揪出,给大家以警醒,刚才您说他是“恨”的文化,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恨一个人,只会跟他更加疏远。像毛泽东却从一个建设性的方式来看待他,把我们都拉到新的时代来。我觉得,我们要按照鲁迅的方法来思考,做事情还是要用建设性的方式。
张旭东:你说得挺好的,我想讲一点,我今天讲鲁迅,完全不想造成一个印象说鲁迅还是我们行动的楷模、指针,完全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在谈鲁迅的杂文写作,他的憎恶、他的针对性、他的反击,他讲的都是小事,陈西滢怎么惹他了,胡适怎么惹他了,徐志摩怎么惹着他了,李四光怎么惹着他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卫兵怎么样了,他都是针对这样的小事,但是这么多杂文杂感累积起来,以小见大,我们能够感觉到鲁迅整个的形象。我觉得学鲁迅并不是照搬他的态度、腔调,而是说我们今天要有同样的对真实的追求、对真实的执着,而对各种各样的自我嬉戏的东西、油滑的东西、自欺欺人的东西、伪饰的东西、自以为是的东西、拿大帽子压人的东西,我们应该有反抗、抵抗或批判。我们抽象地看鲁迅那里有憎恶,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以憎恶来对待所有事情,这就把学习鲁迅抽象化了。所有的对象都是在具体的语境里,有非常具体的来龙去脉,“我”就“执滞于小事情”,这个话说得很老实,这是鲁迅杂文的特点。并不是说鲁迅的文章是哲学论文,也不是说鲁迅是故意限的,没有这个意思。
今天再以鲁迅的笔法去写谁,谁都受不了,因为矛盾性可能不一样,但是毕竟不能排除有可能矛盾的性质确实已经水火不容了而你还不知道,你还以为大家一团和气。今天确实有这个问题,有些矛盾已经很尖锐了,有些人的手段、有些事做得很上不了台面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是温文尔雅、一团和气的,还以爱的姿态去面对,你打不着他,也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
问:鲁迅一方面是要倡导人道主义,另一
方面他说过人是不可饶恕的,这两个方面看起来是比较矛盾的,但是又并存于他的身上,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您怎么看?
张旭东:我觉得鲁迅并不是人道主义者,从人道主义方面讲鲁迅就太简单了。鲁迅是有对人的大爱,这表现为对人的期待,这跟他早期受达尔文主义影响,后来受尼采影响,到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有关的。这几个思想的转变,如果有共同点的话,他选择的几种主要的西方现代思想都不是人道主义思想,都不是强调个人、强调温情、强调人的本位,强调爱心等等,都是把人作为一个实现更大正义、更大目标的一种手段、桥梁、工具。鲁迅对于人的大爱体现为他对正义、对合理的社会、对他所理解的人间的追求,当然包括温隋、爱情,但是你在一个不讲道理就杀人的社会里,他是要谈仇恨的,你连恨都不敢恨,你怎么敢反抗,你连行动的勇气都没有,总想做和事佬,总想妥协,怎么可能颠覆这个现有的制度呢?但是所有这些颠覆、反抗、斗争甚至绝望的东西总得有一个希望的指向,这又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故乡》,对这个故乡很失望,对这个家乡的人的亲情的淡漠、甚至小时候的朋友闰土叫他老爷他都很失望,但是他还是想起了少年闰土的形象,蓝天上挂着金黄的满月,海滩上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挂着银项圈,拿着一个叉子,这是非常美好的乌托邦的景象,这个画面并不是一个浪漫的想象而已,而是最后回到主题,谈的是希望。在最没有希望的社会里,你也不能否认希望的存在,因为只要有人活着就有希望。人活着为什么会有希望?因为人会斗争、会抵抗、会挣扎,挣扎的人、斗争的人、抵抗的人绝不能宽恕自己的敌人,他最后死的时候也不宽恕,你不要以为死了就一笔勾销了,你妄想,账还没完,算这个账,毫不留情,这个目的是为了能带来这么一种社会的变革。鲁迅确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它强调恨或者人性丑恶的那一面,但又不是为恨而恨,而是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和目标。
问:鲁迅说他的杂文写完后就不管了,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评论或攻击。如果杂文写作同时代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他对批评的回应不理不睬呢?
张旭东:鲁迅的确说过,“挤”出来的文章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这是说粗话呢,听出他里面有股恶气,“我”是被人“挤”了才说话的,“我”自己学生在政府面前被人打死,你说“我”写不写,“我”还照你的规定写不成?“我”还照莎士比亚的规定写不成?“我”还照陈西滢、徐志摩他们给“我”定的文人绅士的标准写不成?“我”还在乎章士钊怎么看“我”?“管他妈的”,写就写,写完就完了,这个姿态表明,“我”根本不是为这个文学写作的,“我”是作为一个活人不能不写,“我”不能不叫。第一,这不是人间,第二,这个人间正在压迫着“我”,“我”再不叫,“我”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在这个意义上,他当然就说“管他妈的”。“我”这个不叫创作,没有创作,至于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被“挤”出来的,这个“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个挤牛乳是用来说明“挤”字的,并不是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别以为“我”的作品有什么营养或者说是什么好东西,“我”就是用它来说明“挤”,“我”也不希望被人比作牛乳,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我”不想待在玻璃瓶里,也不想被供奉。现在突然流行起来的论调,将青年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所以“我”便是打胎。因为你是那种道貌岸然的教授、阔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写东西太急着发表,所以就讽刺年轻人的作品都是流产,那他们流产的话,“我”就是打胎,没满月就硬给打出来,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所以一写完便完事。书贾怎么凑,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我”都不管,但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并称赞,“我”终究是喜欢的。有人说好,“我”也高兴,但那些人要说不好,“管他妈的”。这是“挤”。他在自问自答地回应批评他的人。第二条,你如果只是“挤”的话,你写东西认真不认真?如果只是被别人挤痛了,你叫一声,好像没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写作的严肃性。鲁迅说“我”是有虔敬心的,很虔诚,很有敬意,认认真真的,为什么?他不是说“我”被送进艺术之宫多了不起,“我”觉得我在艺术之宫里创作,所以“我”要正心诚意。1980年代的时候文学是很神圣的,有的人写东西的时候要洗澡,穿皮鞋,不穿皮鞋写不出来,要打领带,还一定要用墨水、钢笔,圆珠笔、铅笔不行,真人真事,我就不说了,就是这一代的事。鲁迅的虔敬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文学有多高傲、多高雅,他一定要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才能写,鲁迅所谓的虔敬就是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故意要耍些油腔滑调,他的前提是“我”决不油腔滑调,“我”决不哗众取宠,“我”决不是做戏,为什么呢?又回到了“挤”字,“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吗?倘能,那简直是神仙了,我并没有在吕纯阳祖师门下投诚过”。你被挤着、被压迫着,气都喘不过来,呼吸的空间都没有,这么痛,这么忍无可忍,你写东西还嬉皮笑脸,哗众取宠,还想玩点什么小技巧、小花絮,摆点文人腔,这太不正经了,所以还是“挤”出来的。换句话说,“挤”给写作带来一种紧迫性、严肃性和这种存在意义上的痛感,有这种感觉,写东西是不会油腔滑调的。今天写的东西很多是油腔滑调,各种各样的油腔滑调,文人腔、名士派、各种左派、各种腔调,博客体,电视上那个大讲堂,都属于油嘴滑舌、油腔滑调,感觉到自己是在被“挤”的人是不会这么说话的,至少有一种沉痛感。这种痛你自己知道,你要是没有这种痛的话,就是哗众取宠。我觉得散文,就是杂文写作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发感想、发评论意义上的写作,油滑的东西太多,因为什么?大家肯定没有被“挤”的感觉,觉得很顺、很宽松,大家都活得很自由自在,这个时候,鲁迅说,“我”要是能过那种日子我就不写了,不“挤”就不作。
第三条是写后不管。这个我就不说了,他说这么写出来的东西,被“挤”出来的东西就跟“烟士皮里纯”没什么关系了,“烟士皮里纯”就是灵感,不是灵感突发来的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创作感性,用今天的话说,也不是来自于什么为艺术而艺术的冲动,也不是来自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欲望或者叙事的逻辑,是被“挤”出来的。被“挤”就跟外界有物理意义上实实在在的接触,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不是为纯而纯的东西,是不纯的东西,是没有自律性的东西,是他律性的东西。今天所有文学都在谈自律性,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谈自律性的时候,往往是文学最没有自律性的时代,因为整个是商业化、被炒作被运作的市场化的东西,在市场里的人也不觉得被“挤”,而是商机又来了,都是买卖。鲁迅的“挤”的状态,由这个“挤”而发的所谓的创作论,在今天看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心平气和就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温敦之谈、两可之论、直忠之说、公允之言,写这些还不如不写了,写等于没写,说等于没说,这些话“我”不说,“我”说的话都是被“挤”出来的,被“挤”出来的就是不得不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