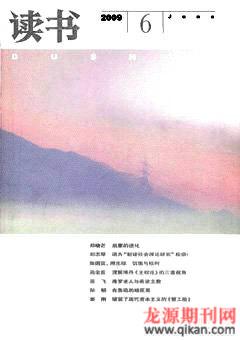茶语茗香话《读书》
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的《读书》杂志,今天已迈入了而立之年。为答谢读书界三十年来始终不渝的关爱与支持,四月二十一日,本刊编辑部在北京金台饭店举办创刊三十周年雅聚,出版界的老前辈与现任领导,读书界新老作者与不同年龄层的读者代表,还有历年参与过《读书》编辑工作的编辑,旧雨新朋,老少咸集,大家欢聚一堂,共庆《读书》三十岁生日。
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总编辑樊希安主持了这次聚谈会,他说,三十年前的春天,在改革开放浩荡春风的吹拂下,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等著名的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创办了《读书》杂志。三十年来,《读书》坚持面向知识界、服务知识界,以其高雅格调和品位,赢得了知识界的普遍喜爱。她既是思想文化界改革开放的标志,也成为我国期刊之林的一个著名品牌,同时也型塑了三联书店图书出版的风格,在读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享有良好声誉。在《读书》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我们诚邀读书界的新老朋友于此雅聚,既是缅怀过去,也是前瞻将来,意在为营造和谐社会增添几缕书香。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贾宝兰在致辞说,三十年的《读书》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回顾与总结。这五个方面是:一,积极参与拨乱反正。第一期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是《读书》在新时期冲破思想禁锢,拨乱反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文章发表后,引起思想界的普遍共鸣和社会关注,它为《读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二,注重思想启蒙。改革伊始,《读书》以自己的资源优势,组织评介二十世纪的西方学术名著和新思潮。这些评介,不仅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影响了一代知识人,而且延续成三联的风格。三,彰显人文精神。《读书》以思想、人文类文章为主,侧重对人、对国家及民族的人文关怀。从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与启蒙,再到九十年代延续至今的对改革问题的反思,无不体现着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读书》区别于其他的刊物,是《读书》的生命力所在。四,追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五,本着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至理名言,创办了“读书服务日”这种服务形式。最初的“读书服务日”主要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服务日上展览各社新书,为作者提供最新出版信息。到后来发展成为编者与作者、作者与作者之间的自由聚会。“读书服务日”这种形式一方面奠定了《读书》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使《读书》拥有一个庞大的作者网络和群体。最后她表示,今后仍将继续秉承《读书》的办刊宗旨, 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流利畅达之文,注重思想启蒙和弘扬人文精神。
读书、编书、出书,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他作为《读书》杂志的老读者,以读书人、编书人、出书人的三重身份,说几句个人感言。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刘伯根代为宣读了这一书面发言。发言说,《读书》杂志的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成果。说《读书》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点不过分。三十年来,《读书》一直在解读好书,引领阅读。让读书人在这里选择、吟味和使用书籍;让写书人在这里拓展思想,开拓思路;让出书人在这里确立追求,提高质量。它所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的精神,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他特别称道《读书》常年举办的“读书服务日”活动,认为这个名称是取自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向作者、编者展示新书,相聚一堂进行交流,一杯清茶,畅所欲言,相互交流,发表见解,领受选题。吕叔湘先生到八十多岁还参加这个活动。老一代的创业精神、渊博学识和严谨品格,已经铭刻在史册,是我们继承和学习的楷模。他在发言的结束语中说,《读书》既有鲜明的办刊宗旨和编辑风格,也有自己强大的作者队伍和稳定的读者群,相信她将会越办越好。
“莫道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李朋义,是作为《读书》上级主管单位的负责人来参加聚会的,他援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认为三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算短暂,但对一个期刊而言,却还依然是年轻的。他说,《读书》杂志的创刊号上曾经发表了一篇开风气之先的《读书无禁区》宏文,不仅表达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冲破思想的藩篱、渴望读书的时代心声,也开辟一条追求知识、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光荣道路。三十年来,《读书》杂志积极引导文化消费的新潮流,大力推动社会阅读的新风尚,热切关注知识群体的新生活,努力满足广大读者的新期待,受到学术界、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广泛赞誉,逐步成长为一代代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成长为一个著名的学术文化品牌。三十年来,《读书》开榛辟莽,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奋斗以成,扶植和团结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才华、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为繁荣思想学术百花园,为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文化氛围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读书》杂志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产物,又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它不仅见证了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见证了伟大祖国不断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读书》杂志的发展与成功得益于政府管理部门的正确指导,得益于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大力支持,得益于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全体职工的辛勤耕耘和默默奉献。对于《读书》杂志今后的发展,他提出了四点殷切的希望:首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要善于回答改革进程中突出的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稳妥处理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辩论与争鸣,要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二,加强作者资源建设。作者资源是最为宝贵的出版资源,是出版精品涌现的源头活水,是我们维护品牌影响力、扩大文化竞争力的核心力量。希望《读书》编辑部团结更为广泛的学术界、文化界的朋友,凝聚并发挥多方智慧和力量,努力实现文化建设上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第三,树立“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意识。第四,努力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期刊文化风格。在上个世纪初叶,《新青年》、《语丝》、《东方》等著名刊物以其独特的文化风格,在中国期刊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希望《读书》杂志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编辑队伍建设,继续保持高雅的文化品格,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期刊文化风格。
《读书》杂志创刊三十年来,她的读者遍布于各个社会阶层之中,既有普通的知识人,也不乏身居高位的官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说,他是作为《读书》杂志的一名读者来参加这一雅聚的。他说,《读书》杂志是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一九七九年创刊的。三十年来从《读书》杂志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文化变革历程的影像。我们读《读书》的时候,感受到它对时代思潮的评介不是说教,而是用谈心的方式和平实的语言来交流的。《读书》杂志看起来薄薄的,也很朴素,但有文化格调,内容非常有味道。所以很多人喜欢《读书》杂志,很多人愿意读。现在的书非常多,但我拿到《读书》还是要翻看,有些文章还要认真地读,因为读完之后可以引发人思考一些问题。《读书》引发的这种思考是内心的、充满智慧的,它给人以感悟。我们现在的刊物和书籍很多,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读书》杂志不仅介绍书,谈与书相关的人、相关的事,还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评论。让我们读者感觉到内心能够有所相通。现在,这样的杂志确实不是很多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价值多元,取向多元,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很多刊物或者很多出版物追求娱乐、追求时尚是这个时代一种必然现象。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读书》一直遵循着自己办刊的宗旨,坚持自己的精神品格,通过跟读者交流,揭示思想的深刻性,使我们读者想读它,希望它办得越来越好。我想,现在有这么多的刊物,为什么《读书》三十年来能始终坚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呢?这是由于老一辈出版人的求真、求实的文化精神被传承了下来,被一代一代的编辑接力下来,用他们的努力,通过思考,把他们的智慧赋予其中,不断赋予时代新意,保证了这个优良传统和创新延续下来。
时光荏苒,三十年前创办《读书》的老一辈人中,现今有的已经故去,健在者也已年届耄耋,步履维艰,不能再亲临聚会了。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感慨说,尽管如此,但我想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地看到刊物能够一直成长到今天的“而立”之年。他回忆《读书》杂志创刊两周年的时候,陈翰伯老人亲撰《两周年告读者》,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期《读书》上发表。陈翰伯重申,《读书》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杂志的性格应当是:一、解放思想;二、平等待人;三、提供知识;四、文风可喜。认为《读书》杂志要提倡四种风气: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平等待人之风。陈翰老当年语重心长地指出的四个性格和四种风气,我认为值得我们永远重视,永远成为检查我们是否完成任务的标准。
三十年前,当《读书》创刊之际就在国家出版局工作,后来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宋木文,当年与陈翰伯同志、陈原同志交往接触比较多。他回忆了创办期的一些经过,认为《读书》的特点之一,是它依托的机构建制是比较独特的。在翰伯同志领导下,以原三联书店有成就的出版家、编辑家作为主要的成员。翰伯同志当时是国家出版局代局长,也是《读书》的决策者、定调的人。陈原同志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因为志同道合,才参与其事。他是出谋划策之人,非常睿智,对《读书》的贡献很大。范用同志还健在,他是位很务实的出版家,是《读书》很多工作包括编辑工作的实际担当者。那样的状况,那样的班子很难复制。他认为,出版界的同志应当思考一下,这种体制,这种志同道合的组合,对当前正处在不断深化的报刊改革工作中的我们来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意义?其次,他认为《读书》杂志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这个杂志起到了引领学术发展的作用。它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回答新的问题,讨论新的问题,使人愿意读它,愿意看它。不乱穿靴戴帽、不说大话、不说假话。《读书》杂志的成长过程中也有曲折,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在一些重要关头,是顾全大局的,《读书》的同志也是非常努力的,这才成就了这样一个杂志。
从《读书》创刊至今年第四期总共出版了三百六十一期。读书界中每期不落收藏全套杂志的颇不乏人。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说,他也是其中之一。他说,能够参加今天的聚谈会,内心充满了温暖的记忆。因为从创刊开始就一直在读《读书》。无论是创刊词还是以后的一些文章,一些发人深省的话,至今言犹在耳,印象深刻。三联的两本刊物是我一直非常爱读的,一是《三联生活周刊》,有些栏目我是抢读。但对《读书》我是要捧读,因为有些文章要细致、深刻地体会,要不时翻阅,去思考。一本杂志能够聚拢那么多学术文化界的名人,他们像是围拢成知识火炉,不断燃烧,散光、散热,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影响了文化人的治学倾向和人文理想,这都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读书》成为知识界案头长存、内心总有的刊物,非常了不起。我作为同行满怀祝福之心,祝福它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从创刊时代起,以钱锺书、金克木、费孝通等先生为代表的我国学术文化界的硕学耆宿,还有大量当年的中青年学人——今日学术文化界的中坚,就给予《读书》的编辑工作以鼎力支持,编者与作者之间的共同努力,才奠定了《读书》杂志的高格调。本次雅聚特别邀请了三位作者代表发言。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读书》杂志的老朋友,他说,我们的职业是写书和教书。要写书和教书,就必须看书。所以,我一直把《读书》看成是我必读的杂志之一。《读书》为知识人建立了一个得以惠风和畅地交流思想的平台,能够在这里以文会友,交流自己的心得,通过思想的撞击和比较找到答疑解惑的门径。因此,他首先感谢《读书》给与丰富的精神营养,使人们在思考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问题时得到许多启发。大家都说《读书》是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产物,应该说,它的内容本身就是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更确切。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这篇檄文一出,打破了限制、束缚人们打开眼界、思考问题的禁锢,思考破闸而出,形成滚滚洪流。其次,他期望《读书》继续发扬三十年来已经形成的精神品格,为解答我们面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上的诸多问题,提供更多的精神思想成果。什么是《读书》三十年来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目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读书无禁区的践行者”,“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读物”,如此等等。他同意贾宝兰说的直面现实、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有段时候《读书》 “不好读、读不懂”的问题引起了争议。在纪念《读书》二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也曾提出过这个问题。最近社会上还在继续争议。南方某家报纸纪念《读书》三十年的专版上,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极不相同的看法提出了好几种解释:例如:背后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过去的“知识分子高级休闲读物逐渐显露它的现实锋芒”,“不再是一位携酒而来的风雨故人,而是更像一位让人敬而生畏的饱学之士”,如此等等。他觉得这些解释好像都不能够令人信服。就他自己的感受而言,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并不能构成文章“不好读、读不懂”的原因。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有阅读的价值。另外,学术上的渊博和高深似乎也很难成为“不好读,读不懂”的理由。这些年《读书》发表的一些学术性很强的文章,虽然要费点劲,但还能够看懂。实在“看不懂”的往往是一些对问题陈述无法让人理解的文章。他说,也许是职业偏好,总希望文章的概念明确、逻辑清晰。但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把许多没有清楚界定、又互不相关的概念堆砌在一起,这样的文字,实在难于成为沟通思想的工具。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说,《读书》的独擅之处在于,她是读书人的家,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但《读书》杂志本身却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门庭”可能会变得“冷落”,“朋友”会越来越少。因为如今的社会,真正的读书人是越来越少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后,是有一个读书人阶层的,但他们读书的目标很单一,就是为了科举。读书的范围也很狭窄,一切围绕“五经四书”来旋转。这样的读书人其实已经开始“异化”,《儒林外史》描写的那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史笔。倒是晚清迄于民国百年以来,确实渐渐有了读书人的群体。但近年来这个群体正在分解和弱化。为了专业研究而读书的人多了,无特定目的闲适读书的人少了。为此,他建议《读书》能否就“读书人”和“知识人”的话题,有所关注,有所讨论? 另一点,是鉴于目前的“国学热”,由于缺乏经学与小学的基础,很可能结不出文化果实。因此他建议,对于那些古今中外最基本的文本经典,《读书》杂志如能细水长流不间断地有所介绍,那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文化长策。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曾经提出了“《读书》文体”这一概念。在这一文体风格的背后,不仅仅只是文风活泼、讲究趣味,而是东西方文化早从古典时代就已发萌的关于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人文理想。许多《读书》的老朋友还记得,在庆祝《读书》创刊二十周年之际,陈平原曾引用了胡适说的一句话:在他之前二十五年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创造一个时代,那就是《时务报》、《新民丛报》和《新青年》。他当时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如果可以找一个能够代表时代,介入社会、代表社会的很可能是《读书》。十年后,陈平原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不过他注意到近年来《读书》的作用在下降,这和新兴媒体的出现有关,也和社会变化有关。他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杂志从一开始就定位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今天“以书为中心”基本丢了,而成了思想评论刊物,《读书》基本不再“读书”了。这是刊物最成功的地方,但长处也可能成为自己的陷阱。以后在这个地方应该做一些调整,继续把书作为一种媒介,评书、品书。在这方面,《读书》的思想高度以及跨学科的视野、文章的风格和超高的人气,都可以对《读书》以后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
中宣部出版局为此次活动发来了贺信。副局长郭义强宣读了贺信。贺信中说,三十年来,在一大批老一代出版家、文化人的参与和培育下,在无数热心读者的关心与爱护下,在杂志社广大同仁的辛勤耕耘下,《读书》杂志自觉弘扬三联书店“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优良传统,发表了许多思想性、学术性俱佳的好文章,凝聚了众多高水平有影响的作者,形成了独具文化个性的品牌,为推动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学术繁荣、提高民族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当今时代,出版面临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新技术在传媒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出版格局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希望《读书》杂志以更加宽广的眼界,更加开拓的精神,推出更多思想深刻、学术规范、文笔清新、影响久远的好作品,更好地服务广大读者、服务学术文化、服务社会发展与进步。衷心期待《读书》杂志能够进一步提升刊物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扩大刊物的品牌和影响,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茶烟袅袅,满室余香不散;书香浓郁,让人回味良久。作为本次聚谈会的主人,樊希安最后表示,《读书》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百尺竿头,还须更上一步,我们会进一步领会大家的建议和意见,认真研究刊物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改进我们的工作和不足,继续发扬品牌优势,不断提高刊物质量,满足知识界、读书界的阅读需求,不负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
在《读书》三十年的成长历程中,最让编者内心铭感难以忘怀的,还是无量数的读者作者所给予的支持。一个杂志,无论业绩如何辉煌,其根基终究还是建立在广大读者支持、关爱的基础上。就在北京读书界雅聚之际,相隔千里之外的一位南方网友在他的博客中给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赠言:
风雨相伴有《读书》。三十年过去了,《读书》已长大成人,值此创刊三十周年之际,遥向北国的天际道一句心声:风雨兼程,莫违莫离;霜雪相伴,永不言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