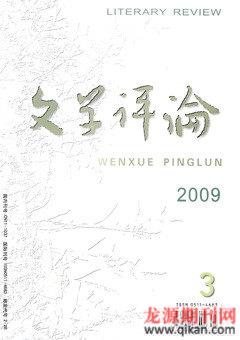鲁敏小说论
王彬彬
内容提要鲁敏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在叙述上十分用心、讲究,能够以鲜活、灵动的口语,精细地描绘事物。鲁敏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小说以城市为背景,揭示人们精神上的“暗疾”,这类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另一类小说则往往以苏北乡镇为背景,表现没有“暗疾”的人是如何善良;当人们都没有“暗疾”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美好。这一类小说其实具有强烈的传奇性。这类以“东坝”为背景的小说,往往叙述得更有神韵。这类小说有时叙述的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如果没有叙述上的精心、精细、精确,这类小说其实是不堪卒读的。鲁敏以美丽的方式叙述着这些传奇般的故事,才使故事显出自身的美丽。
一
人们对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我对小说也有一种很私人化的分类法。我把小说分为“赶路式小说”与“散步式小说”两种。赶路与散步,都是行走,但却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行走方式。赶路有一个终点,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它追求的是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目标。因此,赶路,应该目不斜视、心无旁骛,对途中的一切不但可以而且必须视而不见,能抄近路就决不绕远途。评价一个赶路者的唯一标准是速度,是途中花费时间的多少。而散步则不同。散步不追求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到达目标,甚至可以根本就没有一个目标。散步是为走路而走路。每一次双脚的迈进,都是一次目的的实现。散步,应该尽可能充分地细致地观察、欣赏、品味途中的形形色色。新柳和枯荷、嫩蕊和残花、飞鸟和落日、怪石和流云、家猫和野狗、水边的垂钓、路边的争吵……都可以成为观赏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散步,不妨合近求远,不妨合易求难,不妨弃近路而绕远途,不妨离大道而涉小径,甚至不妨驻足小停,不妨路边小坐,也不妨往回走走。
那么,何谓“赶路式小说”又何谓“散步式小说”呢?所谓“赶路式小说”,是指叙述者只追求尽快说完—个故事或说明一个道理,每一句叙述都仅仅是一种手段。这样的叙述,可以是十分流畅的,但却是那种单调、乏味的流畅。这样的叙述,甚至也可以是精致典雅的,但却是那种没有个性的精致和典雅,或者说,是程式化的、可以批量生产的精致和典雅。这样的叙述,通常是很书面化的,每一句在语法上都中规中矩,在逻辑上也都无可挑剔,而且每一句都长短相当,很少有那种口语化的短句,也很少出现忽长忽短的现象。叙述者不像是在讲述,倒像是在背诵。这样的叙述,很难挑出枝枝叶叶的毛病,但也绝少有那种让人眼睛一亮之处,绝少有那种让人击节叫好、拍案称奇之处,也绝少有那种让人细细地玩味、静静地消受之处。这样的叙述,像是一个人在匀速地赶路。这样的叙述,也像一条人工开挖的小河,没有波澜、没有曲折,直直地向前流去。读这样的小说,也许不会至于让人很痛苦,但也不会让人很享受。而“散步式小说”,叙述者似乎并不以目标为意,一字一句的叙述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在叙述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追求清新、别致、准确。这样的叙述,最大限度地避免空话、套话,最大限度地避免程式化的语言,最大限度地避免“红光满面”、“汗流浃背”、“骨瘦如柴”、“慢条斯理”、“无精打采”、“乱七八糟”这类小学生也惯用的熟语、成语。这样的叙述,往往是口语化的,句子总是很短,很少有语法结构很复杂的长句,但也不避忽长忽短的芜杂和参差。读这样的小说,常常让人低下头玩味、仰起脸寻思;常常让人对作者的想象力、对作者的文学感觉和叙述能力由衷赞叹。我注意到,今日活跃于文坛的小说家,往往具有“两副笔墨”。他们时而以“赶路”的方式写小说,时而以“散步”的方式写小说。以“赶路”的方式写小说,也像是在拧开水龙头,叙述像水一般哗哗地、顺畅地往外流,但也像水一样寡淡。以“散步”的方式写小说,也像是拿起了绣花针,叙述绣花一般里里外外、缠缠绕绕、曲曲折折,紧紧慢慢,但也像绣花一般好看、耐看。一个有能力以绣花针写作的小说家,之所以时而又以水龙头写作,我想,那是因为以水龙头写作,毕竟是更容易更省力更快速的事情,而避难就易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必须赶速度时,水龙头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现在该说到鲁敏了。最近几年,朋友聊天时,时常有人提起鲁敏,见2008年第1期《钟山》上面有鲁敏的中篇小说《墙上的父亲》,一读,立即就被吸引住了。“父亲眉清目秀,三七分的头发梳得锃亮,脖子里是半长的藏青围巾,前面一搭,后面一搭,相当文艺了。他就那么文艺地挂在墙上,在‘香雪海冰箱的上方,在冰箱顶一瓶白蓝相间的塑料花上方,从十六年前起,一直挂到现在——‘香雪海的各项功能基本失灵,只有噪音如常;那塑料花亦掉色了,白花发了黄,蓝花发了白。但屋子的这一角,风景从未变过,好似随时准备上演同一幕旧戏。”这是小说的第一段。小说开头的几段很重要,往往决定读者是否读下去和以怎样的心态、眼光读下去。《墙上的父亲》这第一段,很口语化,看似很平常,其实是很考究的。例如,“前面一搭,后面一搭”,似乎可有可无,在那种“赶路式”的叙述中,这样的细微处通常会被省略,即使不被省略,也不会被以这样口语化的方式所叙述。例如,“白花发了黄,蓝花发了白”,这是极平常的口语,也是极平常的写实,却那么富有诗意,这其实就是诗。在那种“赶路式”的叙述中,这样的摆设通常会被这样地叙述:“冰箱上一瓶白蓝相间的塑料花已经变色。”这样的叙述在语法和逻辑上都挑不出丁点毛病,但读这样的叙述味同嚼蜡。小说的第一段,通过对几处细微事物的精确传神的描绘,把这个家庭的寒窘、沉闷、枯索和卑微,充分传达出来,为故事的展开做了很好的铺垫。接下来的几段,也叙述得十分精彩。母亲有时会望着亡夫的照片发些牢骚,一次次地诉说着生活的艰难,两个女儿对此有怎样的反应呢?“通常的,王蔷与王薇姐妹两个总木着脸,并不搭腔。好在母亲并不需要呼应,她其实也只是说说、打发时间而已——那些曾经渗出血丝的日子,似乎是别人的。”用“渗出血丝”来形容“日子”的艰难,这就足以让人眼睛一亮了,足以让人称奇叫绝了。仅凭这四个字,我们就可以想象出这母女三人多年来是怎样捱过每一个“日子”的。与其说她们是“相濡以沫”,毋宁说她们是相濡以“血”与其说她们是“相啕以湿”,毋宁说她们是相啕以“泪”。接下来,更这样写妹妹王薇的神态:“王薇一边听,一边侧着头吃瓜子,黑壳子在她雪白的齿间进进出出,一枚刚刚进嘴,另一枚已被双指拈起候在嘴边,如同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这分秒必争、有条不紊的忙碌里,有种化繁为简、诸事不管的超然物外。”把吃瓜子的动作观察得如此精细,这个叙述者不是一个匆匆忙忙的“赶路者”,而是一个左顾右盼的“散步者”。这样一个细节,就能让人品味良久。精细,是小说的基本特征。没有精细,就没有小说。而能否精细的描绘事物和能否描绘事物的精细,是检验一个小说家平庸与否的基本标准。
《墙上的父亲》是我读的第一篇鲁敏小说。它使我有兴趣对鲁敏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的探究。在较多地阅读了鲁敏小说后,我发现,鲁敏其实也是有着两种叙述心态、
两种叙述腔调的。并非所有的小说,都如《墙上的父亲》一般,以一种口语化的、不无杂乱但却鲜活灵动的方式出现;并非所有的小说,都能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美不胜收之感。也有一部分小说,是以那种较平庸、较俗套、毋须多费心思就能哗晔流出的语言叙述的。但鲁敏毕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用心之作,都显示了作者作为小说家的良好素质和叙述能力。
鲁敏的小说,一部分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这一类作品,通常以城市为背景,叙述着城市中最普通、最底层、最困窘的那一类人的生活故事。小说致力于写他们生存的艰辛,更致力于揭示他们精神上的病苦。《墙上的父亲》可谓是这类作品的迄今的杰出代表。此外,《暗疾》、《取景器》、《镜中姐妹》、《致邮差的情书》等,都在某种意义上可归入这一类。这一类作品,写出了城市底层的现实生活困境,但更写出了他们心灵上的困境。许多以底层为表现对象的作家,都致力于揭示底层生存的艰辛,并把其原因完全归咎于外在的社会环境。他们以满腔的同情叙说着底层的困苦,同时又以满腔的义愤谴责着导致底层困苦的社会。在他们的叙述中,底层往往是善良的、纯洁的、高尚的,他们的全部不幸都是无辜的。而鲁敏的一大特色,是并不过多地纠缠于导致底层困苦的社会性因素,而致力于揭示导致他们总是不幸的精神病灶。
《暗疾》虽然不是这类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但在揭示人们精神上的病苦方丽,却是最典型的。《暗疾》中,梅小梅一家四口,各人都有着自身的毛病,都有着固执的、难以改变的“暗疾”。这“暗疾”首先是精神性的,是各种各样的心理病状。父亲总是不合时宜地呕吐,“总是最不该呕吐的时候突然发作”,在梅小梅带同学回家聚会的时候,在商场挑选东西的时候,在送外地亲戚赶火车的时候,父亲都会突然呕吐起来。以节俭为最高生活原则的母亲,则对计账怀有极大的热情,她“对每样商品的价格都有强烈的兴趣。借助一个老而旧并掉了几粒珠子的老算盘,她详细地记录日子里的每一笔花费或进账。”由于对商品的价格有超常的兴趣,母亲会对每一个来客认真地询问他带来的每一样礼物的价格和客人身上每一件衣饰的价格。长期便秘的姨婆,唯一有兴趣的话题是大便,她会庄重地向每一个来客询问其大便的情况,即使在餐桌上,她谈论的仍是这一话题。同一家庭中的这些亲人,各以自己的“暗疾”折磨着其他人,谁都既是被折磨者,同时又是折磨他人者,这样,便谁都生活得不如意,谁都感觉不到多少生命的乐趣。例如,母亲记账的热情就这样地折磨其他人:“如果仅仅是自娱自乐倒也罢了,但问题是,母亲慢慢感到,她一个人记账,根本控制不了整体的局面,必须使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进入这个严谨的体系……父亲每日出门,身上带多少现金,当天有什么用度,哪一天单位发了奖金,存了多少进银行……以及,梅小梅,同样的项目。这样,她单独为父亲与梅小梅建了两个账本,并替他们计算每日余额,然后,分别与他们票夹里的钱数,一碰——平了!”有这样一个主妇,家中决不会啼饥号寒,决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然而,有这样一个主妇,家中也决不会有和睦温馨的气氛,家人也决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我注意到,鲁敏多篇小说中,都有这种以节俭为绝对命令的主妇形象。如果家庭经济能力使她们不得不那样俭省,那当然无可非议,那甚至是一种“美德”。但鲁敏让我们看到,她们的俭省与家庭的经济能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她们总是让全家在低于家庭经济能力的水平上生活。本来全家可以站着生活,她们偏要让全家都爬着度日。当节俭成为她们生活的意义时,当她们为节俭而生活时,就常常会为节约几枚硬币而让家人体验不小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
《暗疾》主要叙述亲人们的“暗疾”对梅小梅婚姻的影响。亲人们的“暗疾”,总会吓跑男友,以致于她对婚姻几近绝望:“每遇到一个可能成为结婚对象的异性,只要一想到家里的这三个亲人,不知为何,她突然就失去主动调情或被动调情的兴趣了。因为她知道她会白白花费时间,很难有一个男人会恰好适合她及她的家庭。不是他们太平庸或太出色,只是不合适。”后来,终于有了一个男同乡,不在意家人的“暗疾”,愿意与梅小梅缔结婚姻。然而,在婚礼上,新郎自身的“暗疾”却勃然而发。新郎的“暗疾”引发了梅小梅的“暗疾”,于是,婚姻在开始的时候结束,起点变成了终点。《暗疾》让我们意识到,往往是人们自身的“暗疾”,妨碍着人们的幸福。
鲁敏较多地写了城市底层精神上的“暗疾”,这决不意味着只有底层才有精神“暗疾”。我想,因为鲁敏对城市底层生活和精神状态有更深切的体会和了解,才把底层更多地当作叙述对象。实际上,在《取景器》这样的作品中鲁敏也写了并非城市底层的人精神上的某种偏执和迷狂,也正是这种偏执和迷狂,毁灭着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
将《暗疾》与《墙上的父亲》做一点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暗疾》在揭示人们精神上的病灶方面虽然更典型,但却并非这方面最好的作品。这方面最好的作品仍然是《墙上的父亲》。阅读《暗疾》的过程,远不像阕读《墙上的父亲》那样给人带来愉悦。其原因,就在于《暗疾》的叙述不像《墙上的父亲》那样用心、讲究。《暗疾》中少有那种一剑封喉、一击制命、一鞭一条痕的叙述,少有那种有着巨大表现力从而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精细描写。《墙上的父亲》则一路读来,风光无限。不妨再举几例。“母亲从未正式跟她这么要求过,可能是因为根本不必多费口舌:情况是明摆着的,这么个妇孺老弱之家,像一盘残棋,除了通过女儿的婚事来起死回生,还能指望什么?”“母亲这么一说,王蔷想起个疑问。这疑问,早埋在土里几十年了,这会儿,恰巧碰上合适的光线与干湿,一下子冒出来,细细的芽儿在空气中颤巍巍的。”把父亲死后的家庭比作一局残棋,而把女儿的婚事比作能够让残局起死回生的一着,这是十分精确的。把长期有意识地压在心里而终于压抑不住的疑问,比作破土而出的豆芽一般的植物,并且还“颤巍巍”,也是非常形象妥贴的。这样的比喻并非随随便便就能出现,它是思索的结果,是寻觅的结果,是细细体会的结果,是权衡比较的结果。拧开水龙头就放,是放不出这样的比喻的。《墙上的父亲》有一处写这一家三口拿曾经的辛酸、苦难取乐,把过往日子里渗出的血丝当作了笑料,甚至当作了甜蜜。在叙述了她们的此种情状后,有这样的议论:“有些往事就是这样,一个人时只会自斟自饮,成了苦酒,而一旦变成集体回忆,事情就滑稽起来,就会笑场。哈哈哈!她们相互取笑,毫无良心地添油加醋,并在上气不接下气的笑闹中迅速而愉快地失去对自己和他人的同情。”小说对母女三人满怀欢欣的回忆场面的描绘,已十分精彩,而接下来的这番议论则更表达出一种沦肌浃髓的体验。这样的议论,足以让读者思索半天。
鲁敏对人们精神“暗疾”的揭示,不同于以鲁迅为典型代表的“国民性批判”。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有着更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性内涵。而鲁敏所揭示的“暗疾”,虽然并非与社会性因素完全无关,但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性的东西,一种心理性的表现。它似乎植根于人性深处,或者说,也是“普遍人性”之一种。这样一种对人性的观察和把握,自有一种独特的价值。
二
我之所以说鲁敏那些揭示人们精神“暗疾”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因为这样一种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稍有人生经验的读者,大概都不难以自己的经验去验证鲁敏的叙述。人生中的许多痛苦,家庭中的许多不幸,社会上的许多悲剧,往往并非是那种重大的、山崩海啸般的原因造成的,而常常不过是源于人们精神上某种偏执、某种迷狂、某种难以理喻的癖好、某种非理性的乖张。“暗疾”给自己更给家人带来痛苦,却又使这种痛苦变得毫无意义,“暗疾”在社会上造成或大或小的悲剧,却又让这种悲剧变得滑稽可笑。
如果说鲁敏的这一类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那她的另一类作品则具有强烈的传奇性。这一类作品,通常以乡村为背景,故事往往发生在那个叫“东坝”的苏北村庄或小镇。《颠倒的时光》、《逝者的恩泽》、《思无邪》、《纸醉》、《离歌》、《燕子笺》等作品就属此类。像《超人中国造》这样的作品,背景是广州,但写的是在广州打工的乡下人,也可归入传奇类。或许有人难以认同“传奇性”这种判断。他们会说:鲁敏的这一类小说都很朴素实在,都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写的都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的事,并没有写飞檐走壁、白光杀人、降龙十八掌,有何“传奇性”可言?要理解这一类小说的传奇性,必须与前一类揭示人们精神“暗疾”的作品对照着读。我们知道,在鲁敏那类揭示人们精神“暗疾”的作品里,“暗疾”怎样把好事变成坏事,把没事变成有事,把幸福变成不幸,把安祥宁静变成鸡飞狗跳。而“暗疾”之所以为“暗疾”,就在于它是极其顽固的,是万难改变的。撼泰山易,撼人们心中的“暗疾”难。也许你可以让人和鬼都和睦相处,且彼此都感到快慰,但你却不可能让婆媳们都共同生活并相安无事,且大家都觉得幸福,也许你可以让长江从东向西倒着流,但你却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对他人充满善意而绝无恶意,也许你可以让沧海变成桑田,但你却难以让一个以节俭为生活意义的主妇把一碗剩菜倒进垃圾桶……
这些在现实中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鲁敏却在小说中做到了。她的那一类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人物都是那种没有精神“暗疾”的人,都是那种对他人充满善意的人,都是那种急公好义的人,都是那种极其通情达理的人。在鲁敏用叙述构筑的“东坝”,只有善而没有恶。“东坝”是鲁敏心中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坏事总能变成好事,有事总能变成没事,鸡飞狗跳总能变成安祥宁静,甚至不幸也不难变成幸福——这不是“传奇”又是什么呢?
在思想的意义上,其实那类揭示人们精神“暗疾”的作品是更深刻的。但我在总体上,却更喜欢那类表现人们的“善良”的作品,其原因,就在于后一类作品往往叙述得极为用心。阅读这一类作品,总能从鲁敏的叙述中得到不小的享受。我猜测,在写这一类作品时,鲁敏是比写那类揭示人们精神“暗疾”的作品更有热情的。鲁敏满腔热情地虚构着那些温馨的故事,满腔热情地建造着那个“乌托邦”。正因为满腔热情,所以叙述时也就不肯苟且、不愿马虎。鲁敏让笔下人物所做的事,都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所“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些故事仍然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然而,鲁敏让小说中人物所做的,却又是一般人“不可能”做到的。这里的“不可能”,不是指人的“能力”,而是指人的“意愿”。正因为鲁敏让小说中人物做着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这些故事又具有了强烈的传奇性。
这些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也可归入“乡土小说”之列吧。有些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其实是没有多少乡土气息的。我以为,不具备起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是没有资格被称为“乡土文学”的。鲁敏或许并非有意识地创作“乡土小说”。她只是要构筑一个“乌托邦”,才选择了她所熟悉的苏北乡村。然而,在对这个“乌托邦”的一字一句的构建中,乡土气息却扑面而来。像我这样在乡村长大的人,对这种乡土气息自会产生亲切之感。为什么一些号称“乡土文学”的作品却没有多少乡土气息,我以为原因就在于对于乡村物事没有精细、准确的描绘。而鲁敏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燕子笺》这样写初生的油菜:“确实,只要天气做了主,油菜啊,是个很懂事的作物,闷声不响的,没两个星期,撒过种子的那个小方块儿便绿了,先是矮矮的、齐整的,像毯子,很快,便乱了,叶子东一片西一片支棱着,十分地拥挤——这便是要移栽了……”又这样写成熟的油菜:“那瓢地里的菜籽啊,也都老黄了,胀鼓鼓、沉甸甸的,扶都扶不起,碰都不敢碰,怕把那菜荚给惊动得绽开来。”没有乡村生活的“童子功”,难以对油菜的生长与成熟有如此细致的观察与记忆,而如果没有叙述的热情,也不可能如此细致地叙述这种观察与记忆。《颠倒的时光》这样写乡村的大棚:“好在瓜苗是有情意的,长得很旺,藤叶密密匝匝,映得连大棚的四壁都泛起了青色,人走在里面,总有种恍惚之感,不知今夕何夕了。”乡村气息、乡村色彩,当然不都是那些好闻好看的东西,也有不那么好看好闻的一面。《思无邪》就写了这一面:“我们这里,每户的茅房下面,都有一个巨大的圆形粪坑,深约两米,男人女人,以及猪兔牛羊的排泄物都是集中到这里存放的——粪坑到了冬天,会结冰,就不大臭了。但在夏天,那臭是加倍的,里面的蛆虫翻滚着甘之如饴,眼见着就肥大了透明了,而它们的母亲,那些小小的黑头苍蝇更是满天满地地飞舞起来了。每一样吃食,它总要最先尝过,搓着两只前脚,尝一尝,再搓一搓。除了吃食,它们还喜欢一切有气味的东西,锅铲,出过汗的衣服,小孩身上的脓包,女人许久没有洗过的头,等等。”有人说,鲁敏的这类作品有汪曾祺的影子,这当然也能自圆其说。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也是以苏北乡村为背景的。但把恶臭的粪坑、肥白的蛆和黑头的蝇描绘得如此精细,甚至让人感到某种“诗意”,汪曾祺大概做不到。唯其如此,鲁敏的这类作品是比汪曾祺更富有乡土气息的。类似的对于乡村物事的细腻精准的描绘,在鲁敏此类作品中大量存在,也使得这类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浓郁得像乡村四月油菜花的芳香。
叙述这类乡村故事时更有热情,更不苟且和马虎,固然是鲁敏这类小说总体上更富有文学性的原因。同时也应看到,叙述语言的清新、灵动、准确,对于这一类小说是更重要的。那类揭示人们精神“暗疾”的小说,由于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即使叙述得平庸一点,也还有起码的可读性。而这类乡村故事,实际上不过是些“美丽的谎言”。“谎言”如果以很糟糕的语言叙说,那就非但不能让人相信,甚至让人不堪卒读。在这方面,《逝者的恩泽》最能说明问题。东坝的一个叫陈寅冬的人,父母早亡,又无同胞。他很早就外出做工。虽然回来娶了妻,且生有一女,但陈寅冬仍是跟着一个工程队在遥远的西北修筑铁路,只是每年过年回来几天。在48岁那一年,陈寅冬死在工地上。但令留在家里的妻女没有想到的是,陈寅冬在做工的地方,与
一异族女子古丽另组了家庭。一个冬日,古丽带着血缘可疑的儿子达吾提来到了东坝,找到了陈寅冬的家,要与陈寅冬留在家中的妻女共同生活。而陈寅冬留在家中的妻子红嫂和女儿青青居然接纳了古丽母女,而且这四个人还居然生活得异常和睦、幸福。这其实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丝毫经不起推敲。但小说却颇受好评。其原因,就在于鲁敏把这一“荒诞不经”的故事叙述得十分生动、饱满,用满纸的“花言巧语”把故事说得“像真的一样”,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时时得到语言的享受。在古丽母子刚来时,红嫂母女虽然接纳了,但内心并非没有保留,并非没有疑问。这是第一天晚上,“太多的悬疑与敌意仍在屋子里四处窜动,伴随着红嫂走来走去的身子。红嫂在收拾碗筷,红嫂在抹桌子,红嫂在整理凳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个饱满得快要坠下来的水滴,或是正在发酵的谷物,酝酿着无声的诘问与指责:你跟陈寅冬到底是什么关系?凭什么说这男孩就是他的儿子?今天找到这里来又是什么意思?寻亲么?认门么?闹事么?”这样短短的一段,把这天晚上这个家里的气氛写得极其真切,让读者顿生身临其境之感。红嫂什么也没有说,却又在不停地说。红嫂以前也要收拾碗筷,也要抹桌子,也要整理凳子的。表面上,红嫂不过是重复着往日的动作,然而,今天晚上的这些动作却又绝不同于往日。红嫂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发出强烈而又无声的声音。说悬疑与敌意在“四处窜动”,把红嫂的动作比作“饱满得快要坠下的水滴”和“正在发酵的谷物”,这感觉既新颖又准确。
红嫂本来每天走街蹿巷卖小吃。年轻许多的古丽住下并获得信任后,要求从红嫂肩上接过小吃担子。青青也主张由古丽担负起这份劳作。红嫂终于认可,在认可的同时:“红嫂扶扶自己的腰,好像突然间就疲惫了起来,这疲惫来得有些违心,又有些存心,总之,她想现在是应当累了,该回到屋子里了,那外面的天地,就给古丽去飘摇吧。”读到这里,我们只是想到五十多岁的红嫂,其实早就感到累了,早就力不从心了,只是以前有意识地压抑着这种疲惫感,强撑着每天出门奔波。现在,终于可以把担子交出去了,被压抑的疲惫也就活跃着、弥漫着、肆虐着。说这疲惫来得“有些违心,又有些存心”,也算得上是神来之笔。读到后面,当我们得知红嫂其实早已患上乳腺癌时,才明白,这其实是一处伏笔。再回过头来读这一段,就多了一层意思了。原来红嫂一直是拖着病体在早出晚归地劳作着。
《逝者的恩泽》通篇就是以这样的语言方式在叙述着这个传奇般的故事。不仅仅是《逝者的恩泽》,鲁敏的这一类作品,都具有这种叙述品格。这些作品叙述的故事,本身是美丽的。但如果叙述方式不美丽,那故事本身再美丽也不能让人感兴趣。鲁敏用美丽的方式叙述着美丽的故事,才使故事真正显出自身的美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