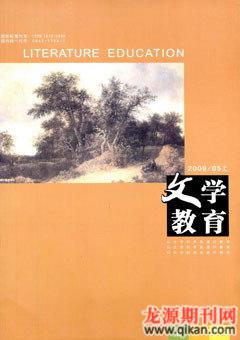《大寨在人间》探赏
傅金祥
在我的阅读范围中,很难找到像张正隆的报告文学《大寨在人间》(原载《解放军文艺》1984年第6期)那样充满刚性和力度的动人心魄的文字。这样的作品倘若选人教材,或作为阅读书目推荐给学生,它给予学生的,将不仅是思想的启迪和文学审美的感染力,它会激发你对历史、对生活,对生养我们的土地的敬畏感,并具有刷新和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这也是我常常将《大寨在人间》带进课堂的重要原因。
大寨,无论作为一个时代的中国农民可歌可泣的壮举看,还是从瘟疫过后的疫区及其康复过程看,作为巨大的历史存在,都是历史馈赠的不可多得的资源,都不该被忘却——值得庆幸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繁荣的热潮中。大寨没有被回避和遗漏,而由张正隆这样一位富有责任感又颇具理性与才情的作家选择了,而且写得如此感人肺腑。
1984年作者带着复杂的心情走近了大寨。当时的大寨刚从狂热的岁月中沉静下来。一切刚刚谢幕,整个历史舞台还未来得及彻底清理。可以想见,背负了特定的历史包袱的大寨不可能像安徽风阳的小岗村。一方面,历史的惯性还在顽强地作用着人们;另一方面,大寨又毕竟在痛苦的蜕变中一步三回头地掉转着方向。作者对这一切作了近距离的观照和扫描。作品着重叙写的自然是为世人所关注的,即今天的大寨如何,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革。从而真实地再现出在时代大潮裹挟下大寨人在痛苦与矛盾中抉择的艰难历程。要描写今天的大寨,不能不回顾昨天的大寨。探索几十年大寨的轨迹。于是。“人间——天上——人间”构成了《大寨在人间》历史与现实的深厚内容。
作者如实地描述了解放后大寨是怎样凝聚起炎黄子孙、太行儿女渴望温饱,追求幸福的愿望。苦战穷山恶水,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文革期间,又是怎样在“特殊化”、“绝对化”以及“七斗八斗”中被扭曲变形,从而成为一个杀气腾腾的样板,一个推行“左”的路线的典型。于是一个好端端的靠“出大力流大汗”干出来的大寨,变得面目全非,“朝历史的天平坠落了。”“一个失重的时代造就了一个失重的大寨,失重的大寨愈发加重了时代的失重。”
作者不仅仅满足于对大寨及学大寨运动的教训做出理性剖析,更要写出血肉之躯的大寨人的情感、心理、秉性和节操。“足踏在地上的大寨人”一小节,对贾进才老人的“手”的描写可谓一个精彩的片段。
作者以“立片言而居要”(陆机《文赋》)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从合作化到‘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粮食亩产量翻了两番,达到五百多斤;‘文化大革命中,又把这个数字翻了将近一番,达到九百多斤”。既然大寨推行了“左”倾路线。为何还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看似矛盾的命题将读者引入深深的思索中。
作者选取了贾进才老人的手,开始了浓墨重彩的描绘,从而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并不矛盾,因为有足踏在地上的大寨人……
我肃然起敬,紧紧握住老人的手。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呵!
人们通常用铜钱形容老茧的厚度,用蚕豆比喻茧花的大小,这两样东西我都见过。可此刻面对这双手若仍用铜钱形容的话,那掌心的老茧少说也有三枚铜钱厚;蚕豆则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那整个手掌和手指,就是一片硬板板的茧子铸成的钢与铁的平原和丘陵!瘦骨嶙嶙,青筋凸突的手背上。疤痕迭印,左手食指、中指与手背连接处的骨节,各凸起一个乒乓球大的硬包;十个指甲全没了“指甲盖”的含义,有的变成了粗糙的山岩般的骨疙瘩,有的像断指戳露出来的一节骨头。老人告诉我那两个硬包是锤子砸的,“砸了好,好了砸,聚筋了”;那十个指甲,原来的都砸掉了,多的砸掉十几次,只有右手无名指最幸运,只被砸掉三次。
二十余年来,每每在课堂上读到这些文字,我眼里都会噙满泪水,学生也无不啧啧慨叹。可以想见,当年作者握着老人的手或写这段文字时,心头翻涌着怎样的激情——是的,大寨取得的成就,只能归功于这样一双双手。正如作者所赞叹的:
“历史把大寨的真经和中国农民的一切精粹,都凝聚在这一双双手上。我从这一双双手上,看到了长城的巍峨、大运河的雄浑、葛洲坝的奇伟、引滦工程的壮阔……”
作者生发想象,将一尊雕塑矗立在虎头山上,定格在了历史的天宇:
“铁锤砸在钢钎上的声音,在我耳畔叮叮当当回响。在这山鸣谷应的响声中,我看到一位老人顶着北风,披着霜雪,坐在茫茫黄土高原的岩石上,一锤一钎,就像那位磨铁杵的老人,坚韧地开凿生活。执著地追求理想,饿了,啃口冻成冰坨的窝头;渴了,抓把浊黄的积雪;指甲掉了,捂撮汗湿的泥土……”
的确,学大寨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由于历史的扭曲而失重了;但是,大寨人永远不会失重,大寨人出的力,流的汗,几代大寨人渴望温饱追求幸福的愿望。永远不会失重。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在后代人的眼中,许多激情燃烧的话语和政治化的诠释,或许失去了原初的意义;但是,贾进才老人的“手”以及那一幅巍然屹立于虎头山的雕像,却像《老人与海》、《热爱生命》中的形象,带着强韧的撼人心魄的力度,化为一种生命哲学、人类学的具象,获得永恒的审美意义。
如果我们超越具体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视角,而站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生活以及人类探索未来追求进步的艰难卓绝的历程上看,大寨这出剧目,无论正剧、悲剧、喜剧的因素各占多少成份,这一切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大寨,这是一出充满了崇高与壮美的值得我们永远凭吊的气吞山河的史诗,人类将永远铭记着:当年的大寨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个永恒的符号和象征,就像科学探索中的每次成功、每次失败都令人尊敬一样。是的,我们的历史并不完美,每个人都不完美,然而,正是这些并不完美的人,创造了并不完美,却也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值得作家以全部的热情、虔诚和敬畏之心去书写么?历史是庄严的、神圣的,体认到这一点,你才有资格进入历史。你会觉得当你全身心融入一段历史,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一切随心所欲的点评或戏谑都是不负责任的,你会感受到,你手中的笔是如此神圣而又沉重。
我认为,《大寨在人间》的成功得益于下面两点:
其一,作者深深理解并遵循了“物、意、文”转化率。无论做什么文章,都存在这一问题:“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机《文赋》)。“物”即客观外物,客观世界或社会生活;“意”即“构思之意”,是作者要写作的文章的内容、思想、感情;“文”,即语言文字及表达形式。就《大寨在人间》而言,作者首先是带着足够的热诚、理性、责任感和敬畏情怀进入这段历史的,对环绕“大寨的历史变迁”的一切作了准确而深入的把握。作者面对的,是一棵盘根错节枝叶繁茂的大树,要雕塑好这一棵大
树并不容易,仅有勇气是不够的。作者对几代中国农民有着深挚的情感,对那段历史有着深切的感受。才会对人、事、境以及观念的、心理的、显性的、隐性的一切做了准确的把握和体察。从而达到了“意”“物”相称,即,作者在理性思辨、价值判断及情感把握上,最大程度地切合客观实际,达到了近距离反映生活难能可贵的准确度——即便今天,这一切都还能令人信服,经得住检验。的确,好的文章是能够经得住历史淘洗的。
深入采访,掌握多方面材料固然重要,但具有理性而中正的价值选择、价值判断,才可能使材料找到合理的位置,得到合理的阐释。面对复杂多面的大寨,作者的价值纬度、情感纬度都是多元的、立体式的。或肯定,或否定。或深深理解。获激情讴歌,或含蓄揶揄,或严厉警示。可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陆机《文赋》)。
比如,当写到文革中大寨在“七斗八斗”中,变成了“大灾”。从而“朝历史的地平线坠落”时,作者旋即切换场景,推出了以往岁月的镜头:大寨遭灾后,大寨人把国家救灾的钱和物资统统退了回去。而三年困难时期大寨人抓到邻村偷玉米的人,他们虽然自己饿得浑身浮肿,却请那人吃饭,让那人背上玉米,把他送到村口——读到这些,怎能不叫人热泪盈眶、唏嘘再三呢?“大寨呵,被扭曲,被阉割,被玷污了的一个好端端、活生生的大寨呵!”
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看来,生活与世界是全息的,而语言是拓扑的,语言不能够确保能准确地把握和表述世界。而就新历史主义观点看,一切历史阐释都是一种叙述。但是读过《大寨在人间》,你至少会承认,作者最大限度地把握了大寨的本真。这首先归因于作者继承了史家的优秀传统,不隐恶,不讳饰,秉笔直书;另一方面,作者灵活移动着价值坐标,从而获得了多元、立体的价值视角。同时,在语言表达上到位率也是极高的,这就确保了内容获得充分的表现。从而实现了“文逮意”。
其二,理性与才情的完美结合。《大寨在人间》无疑获得了哲学的深度、历史的厚度、新闻的信实以及文学的诗意和美感。这得益于作者的激情、理性和文采的结合。作者充分利用了报告文学长于抒情议论的优势,深化了主题,强化了文章的感染力。或深刻透辟,或激情澎湃,或凌厉峻拔,或挟雷裹电,或朴实醇厚,或文采飞扬,或沉郁,或叹惋……
请看下面的文字:
眼前仿佛划过一道闪电,一道历史的闪电,在那倏然的闪亮消失后,这山。这梯田,这“大寨楼”,这大柳树……都刷上了一层苦涩、苍凉、蓊郁的色调,溶进了一首已经逝去的无题的带泪的歌
我不会绘画,但我想画一幅油画;我不懂雕塑,但我想塑一座雕像:《中国农民》背负苍天。面朝大地,赤裸的脚掌踏着茫茫黄土高原嶙峋的山岩,那山岩般粗糙的臂膀上涌奔着力的波浪,抡圆的大镐吼着黄河纤夫一样雄浑的号子,满脸的皱褶里扑满风尘浪沫,瞳仁中闪亮着一个太阳
如果说世界上真有神灵的话,那么,我说贾进才老人和那些足踏在地上的大寨人的那一双双手就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所有如同他们那样的一双双手都是。我愿向这一双双手致敬!
因为有着坚实的叙事描写作为基础,这类抒情议论性文字也便没有浮泛轻飘之嫌。情感与理性调配得和谐自然。令人信服。通篇洋溢着壮美崇高的美学风格。在20余年后的今天,读到它,仍觉得一股股热浪冲击着心头。
每一代人都带着时代的胎记,都有特定的生活、思想、情感资源,都是不可替代的。比如刘白羽、贺敬之、峻青这一代人,在进入老年后自然还能写一些歌颂性文字,但不可能写出《大寨在人间》这类冷峻透视、理性剖析的作品;而像余杰、葛红兵、朱文这一代人,其与昨日决绝的姿态、解构传统的力度是充分的,但显然不会有张正隆这样热诚而深沉的情感。读过《大寨在人间》,由社会生活变迁想到文学变迁。不禁为那些年的沧海桑田之变而深深慨叹:正如大寨的变迁令人惊叹一样,从姚文元、池恒、梁效、初澜、罗思鼎、石一歌那类大批判文章,到张正隆这类文章,也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一个民族连同她的文学一起,从狂热、偏执、荒谬中清醒过来,迅速恢复正身,落到坚实的大地上——短短几年中,生活、思想、文学跨越了千山万水,这便是真理的力量,生活变迁的力量。这表明我们这个民族及其文化、文学,有着强大的自我矫正、更新和再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