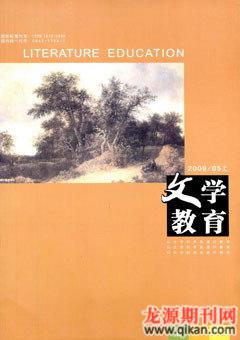张爱玲和苏青文学世界对女性神话的消解
李若飞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设专章论述了女性神话与女性生存现实的关系。女性神话把女性放在概念化的、超自然的观念的世界里,掩盖了分散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而事实神话的路对一个个具体的女人是堵死了的,每个女人归根到底还是得独自面对自己的存在。所以说,在现实中的关系越具体,就越少会被神化,丢弃神话,只是要将行为感情激情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正是以女性话语主体的真实言说,一步步走出了女性神话的幻影,从飘渺的太空落到了坚实的世俗生活的土地。
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较之她的前辈们最大的变化就是用写实的笔法。世俗的关照,消解了女性神话,还原了女性的原生性。在她的文学世界中。母亲不再总是神圣的,女儿也不再那么缠绵悱恻,她的女性人物以女性为性别,女人而非女性,时代环境已不容她们做传统淑女,而只能是生活生理意义上的女人。女性天然具有的妻性与母性,在出自乱世挑战男权的过程中,早已被剥落在世俗的泥潭里。“女人”的意义对她们来说成了一注赌本。她们揣着这注赌本,去铤而走险,去换得生存。张爱玲、苏青就是这样拒绝了超现实的家庭神话和虚幻的女性本质,以平静的写实揭穿了现实女性神话的虚妄。
作为女性,张爱玲、苏青以自身的故事解构了爱情神话。张爱玲出身显赫,有李鸿章、张佩纶这样的先人,特别是张佩纶与李鸿章千金的姻缘,一直广为流传。然而,张爱玲却对祖父、祖母的才子佳人式浪漫情爱表示怀疑。推论出此事的真相并无关本文宏旨,关键是张爱玲的“透彻”让我们认识到,她不要爱情传奇,不要爱情佳话。她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那么,具体到个人,张爱玲又怎样呢?她有过爱恨交集的恋爱婚姻,但这段情却正像她的小品《爱》一样空灵飘忽,转瞬即逝。张爱玲曾描述高更画作《永远不再》中那个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的女人,拿她和现实里的女人作比照,在那个社会里,年纪太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明净,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棕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对张爱玲而言,她未必能做到心平气和,但她明知挣扎无益,便不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惟其对飞扬的爱情觑得明白,却偏为情所迷,为爱所动,才有现身说法的凄惨,才有回归认同凡俗生活的悲哀无奈的舍弃和萎谢,才更令人生出宿命般的苍凉感。苏青没有经历过张爱玲的悲欢离合,她的情爱态度更接近凡俗人生。她要求丈夫要有男子气概,有架子,官派一点,还要有点落拓不羁。要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要容貌比她略差和大一些,免得麻烦,丈夫的职业性质能够常常有短期旅行等。正如张爱玲所评论的,这绝对不是过分的要求,然而,即便是如此平凡的理想。也还是不能实现,苏青只能叹息没有爱。而张爱玲看苏青就如同看到了自己,于是她感叹,生命是残酷的。看到她们自己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总觉得有无限的悲伤。
作为作家,张爱玲、苏青以一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情怀叙写现世婚恋故事,以贴近的方式还原了女性在情爱中的真实处境。两位女作家笔下的人物都生活在动荡乱世氛围中,在无法选择的时代里,生计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她们的主人公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于是,在男女情爱的游流中本应纯情的少女,变成了早熟精明的都市女郎。婚姻不过是生活的保障,恋爱不过是得到保障的手段。所有的真心交付不过是一场无聊的人性游戏。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常表现出对金钱物质的迷恋和不可自拔,如梁太太、白流苏、敦风等,尤其是七巧,我们不得而知《金锁记》中的七巧在进入姜家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激斗,然而她终于嫁给了姜家的痨病二少爷。这宗买卖婚姻虽然保障了七巧的生存,她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张爱玲看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必然的变异沦落。无论是死还是爱,它们终将让位于生生不已的生活。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是其婚恋故事的典型代表,这部小说中较为全面的包含她的人生观、人性观,也最贴近真正人生人性图景。就人物而言,范柳原、白流苏是标准的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但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也因此使平凡读者产生认同感。就情爱而言,保存着没有经过去芜存精的现实生活本身的原汁风味。范柳原只想自流苏做自己的情妇而不愿负责任结婚,而自流苏则只能以谋得范柳原的爱来谋生,这精微复杂的情爱游戏实则表明了现实人生中最朴素的爱情关系式:男人作为主体是以不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去爱人,女人作为主体是如何最机智地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才能得到男人的爱。就哲学意味而言,张爱玲把对人类特别是对女性的悲剧性把握体现得恰到好处:白流苏的成功并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香港的陷落意外的成全了她以爱谋生的计划。张爱玲用一座城市的毁灭来满足一个女人微小的平凡的日常生活欲求,这种艺术表达展现了张爱玲对人生悲剧性的哲学认识。因此,《倾城之恋》没有借助传统悲剧的激烈冲突的形式构架来运作,就已具有一切悲剧所必然的实质:在最终的结局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既显得不可一世,有挑战的意味,又显得毫无意义,终归于沉寂,但因为人类的努力介于这二者之间,它又显出了温暖的本性。显出了人类哪怕只有一种十分卑微的努力,也具有意义,并将其提升为生存的一种合理正确的追求。就这样,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与悲凉境地之间建立了独特的张力,既赋予日常生活形态以亲切感与合理性,又揭示其陌生感与荒诞性,从而构成一个来自日常生活却又指向人类终极思考的独特的文学能指系统。
如果说张爱玲的婚恋故事还企图在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一些形而上的观念形态的东西的话,那么苏青的婚恋故事就更倾向于用事实说话,让女性神话在凡俗琐碎中自动解构。苏青几部重头作品,人物的命运都是与婚恋紧密关联着的,《结婚十年》写女子不幸的婚姻和离婚的不幸,《歧途佳人》着重表现离婚女子误入歧途,《朦胧月》仍是述女子不幸的婚恋故事。这些作品的落脚点都是平凡女性的常态婚姻,具体说叙写妇女在婚姻中的所历、所感和所哀。《结婚十年》写“我”(苏怀青)十年婚姻的经历:父母包办的婚姻,夫妻间陌生又无奈的认同,姑嫂间的矛盾,婆媳间的生疏,生女受族人的轻视,夫妻自立门户的艰辛,油盐柴米的烦琐,丈夫的沾花惹草,自己的敢怒而不敢言的寂寞、怨恨等,这就是苏青小说的婚姻图景。苏青把这种中国女性习以为常的婚姻状态以自叙性框架结构推出,使作品具有了一条来自昨天、通向明天的生活本质潜流。中国妇女的婚姻生活就是这样古旧,这样琐碎,今天不过是昨天的延续,昨天又是前天的重复。正是在这循环往复中,中国女性在社会中、在家庭中、在情爱中被放逐的图景触目惊心地凸现出来了。
张爱玲、苏青的消解女性神话是无所不在的。在《忘不了的画》这篇散文中,张爱玲对林风眠一幅妓女的画议论说,普通女人对于娼妓的观感则比较复杂,除了恨和看不起,还又羡慕着,尤其是上等妇女,有着太多的空闲与太少的男子,因之往往幻想妓女的生活是浪漫的。这段近乎赤裸裸的陈述恐怕会触及某些自命为贵妇和淑女的痛处。它不再把女人截然划分为娼妓和贞女,而揭示出女性心理和感性世界的复杂而矛盾的内蕴。而这正是更接近于女人的天性中的某些本性的。针对母亲形象的神圣化这一现象,她们都有过相反的论调,在张爱玲看来,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苏青认同张爱玲的看法,母爱诚然伟大,但一半也是因为女子的世界太狭窄了,如果一个男人常陪着太太上馆子、看电影,或干些别的玩意儿,那时女人定会嫌憎孩子累赘,母爱起码得打个七折。针对五四时代为青年女性的离家出走所涂上的“娜拉情结”、神圣色彩,张爱玲用自己离家出走的实例说明,她完全出于精细的盘算,而非神圣的目标,并认为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苏青则议论道,娜拉可是易卜生的理想,不是易卜生太太的理想。身为女子,怎可轻信人家谰言,不待预备好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便瞎嚷嚷跑出家庭,跑出家庭呢?
可以说,张爱玲、苏青不仅消解传统女性文化的神话,也消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树立起来的新神话。她们以日常生活的内容和逻辑,对爱情、母爱、家庭以及自由恋爱、新女性等理性化、神圣化了的文化现象和概念都给予了质疑和嘲讽,为一切理想的价值神话蒙上了“一种污秽”。而这一切恰恰是女性自我意识苏醒后而又无路可走的现代女性悲剧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