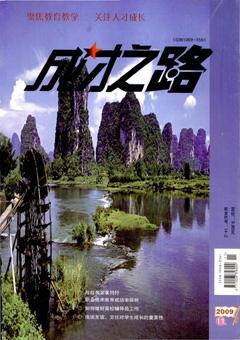论李梦阳文中的商人形象
张建霞,宋德志
摘要:我国古代文人文章中出现的商人形象多为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的负面形象,而明朝李梦阳文章中的商人形象多为善良、正直、有道德的正面形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明朝商业经济发展和李梦阳自身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梦阳;商人;商业经济
明朝中后期,商业经济扮演了较为瞩目的社会角色,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士商关系由对立逐步走向契合。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文学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商业的渗透和影响,商人逐渐成为文学作品创作的对象。如明朝著名文人李梦阳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自己的文中,创作了一系列的商人形象。
一、 李梦阳及其文中的商人形象
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阳)人,是明代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称,“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发轫于“前七子”的文学活动,而李梦阳正是“前七子”的领袖。
他提出著名的“真诗在民间”之说,是其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气息。与反映庶民生活相联系,一些市井人物也就成为他文学表现的对象。李梦阳一生与许多商人都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文章中出现了不少的商人形象,颇为引人注目。其《空同集》中卷四十五《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卷四十五《梅山先生墓志铭》、卷五十八《鲍允亭传》为兰阳商人丘琥、徽商鲍弼和鲍允亭等商贾而作的传记、记事作品,还有为士而商、商而士者的诗文集所写的序记等,如卷五十八《潜虬山人记》、卷五十一《方山子集序》。文中的商人多为善良、正直、有道德的正面形象,李梦阳对他们也多褒扬之词。
写作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专于对这些商人形象的分析,而是要依据文学创作的主客观性质理论,从李梦阳文中的商人形象创作来看明朝商业经济发展和李梦阳自身思想变化两方面对李梦阳创作的影响。这样的分析,并不是强说李梦阳在文章中所进行的商人形象创作必有所为之,而是借助这样的分析从侧面揭示当时的主流社会现象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并从新的角度了解李梦阳。
二、 影响李梦阳文中商人形象创作的客观因素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的反映。从表面上看,文学创作是作者个人在他的书房里单独进行的活动,完全出自作者的自愿,并受他的主观意志的支配。但在实质上,文学创作又绝不是作者个人的随心所欲的活动。写作活动本身与周围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受客观条件影响的。没有作者例外,李梦阳的创作亦是如此。
文学中出现商业元素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然而,从那时起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诗经·邶风·氓》),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业文学的发展却一直是步履蹒跚的。到了唐宋元三朝,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人们逐渐发现商业的不可或缺性,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开始解冻。但由于传统“本末论”的根深蒂固,思想解冻仅限于少数人。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商人的价值观及其商业行为并未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文学家受“重义轻利”观念的浸淫,耻于言利,因此,文学作品中有关商业的内容仍少之又少,即便有,也多是抱着批判的态度,以嘲弄的眼光看待商人及其商业行为。至明,上文已经列举,明中李梦阳文中已出现不少的商人形象,写作者自己与商人的友好交往,多是溢美之词,并无贬斥之意,商人形象得到很大改观。可以说,明中后期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为李梦阳文中不同以往的商人形象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外在客观条件。原因分析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明中叶以后,都市经济的加速度繁荣,市民阶层的勃兴,都使有关商人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世风已然突变,以至于“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人们的观念也一变而为“商贾何所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的同情之语和赞美之辞。观念的转变反映于文学作品中,商贾形象被重新定位,他们的职业得到首肯,人格受到尊重。同时更出现了一些周身散发着人性光辉的“良贾”“儒商”。在可谓晚明市民文学的代表作的“三言”“二拍”中,就出现了不少的商人形象,重商思想愈加明显。他们多数已不是贪得无厌之徒和为富不仁之辈,而往往是一些善良、正直、淳朴,而又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的正面形象。如“三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小店主刘德“平昔好善”,赢得了“合镇的人”的“欣羡”。《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长途贩运,历尽艰辛,终于发财。正如作品中有诗赞道:“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新兴商人所获之利都被蒙上了传统道德之“义”而显得温情脉脉和天经地义。而李梦阳为兰阳商人丘琥撰写墓志铭《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中写道:“经营四十余年,遂起家至千金。顾尽散诸弟男女及族若所识贫乏者,已而金辄复集,集而复散,终不为自计。尝起第大梁东门,结亭莳木芙蓉菊亭旁,更为诗,先后所为诗积万余数。”记叙的亦是商人丘琥乐善好施的行为。
2. 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商人总体地位提高
明中叶以后,都市经济加速繁荣,商人阶层拥有的商业资本日益雄厚。明朝时大江南北形成了十几个大的商帮,其中徽商、晋商最为活跃。他们资产雄厚,尤以盐商为巨。万历年间因国有大役,出兵征讨,需要军费,这时徽籍盐商吴养春愿输纳银三十万两。皇帝为表彰吴氏,一天之中竟特谕吴氏家中五人任中书舍人,资力之雄厚可见一斑。加之人们观念的改变,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商人地位的提高,不仅是因为拥有了雄厚的商业资本。据日本学者田隆信先生的统计,从正统戊辰科(1448)到崇祯癸未科(1643)山西商人进士出身的计有37人,新安商人中进士出身的有71人,可见这时的商人的地位已不同于前了。明朝商人出身,或家中祖父辈有从事商业的大官僚颇为不少。如李梦阳,进士出身,曾任户部郎中、江西提学副使,其祖父李忠就是拥有巨资的商人。
如“三言”中,经营买卖已被视为正当的职业,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客商凭着金钱的力量,已在百姓的心目中建立起仅次于官员的地位。“二拍”中的重商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中写到“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人生的价值就以得利的多少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所写的主人公程宰与海神女结良缘、发大财的故事也意味深长。历来在文学作品中只有文人雅士或在民间故事中勤劳诚实的农民能得到的仙女,如今却移情于一个“经商俗人”了。这充分说明了生机勃勃的商人正在取代读书仕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这也是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
3. 士商关系的契合
商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旧的社会体制已失去了可依赖性。自程朱以来几百年思想上的禁锢,在文人中形成一种逆反,随着社会发展,文人们终于冲破了这种禁锢。王阳明及其唯心主义哲学,高扬个性主义,主张人欲的合理性。而商业经济极度发达又为人欲追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渐渐形成纵欲主义的社会风气。对享乐的追求打破了旧的礼教和秩序,人们的注意力朝向金钱和享乐,拥有巨资的商人已成为人们的羡慕对象。以此为基础,商人与名士各展其长各有所好。商人因其地位,风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本身颇有儒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更易与文士诗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也常趋之若鹜。
商人遍交四方大夫名士,附庸风雅者自不待言,一旦得贵人名士只言片语,珍若璧瑜,以抬身价。最为普遍的是旨在培养子弟,经商谋利是为了打下科举应试的基础。大夫名士饱读诗书,门生故吏遍天下,商人除在礼请馆师之外,再让子弟日游其门,成为通向科举成功之路的常见途径。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视商人为衣食父母、居住主人、赞助对象。在商人看来,商人凭才智经营谋利,文士凭文化文字谋生,其途虽异,其旨相同。因此,“良贾何负鸿儒”。觥筹交错,览胜赏景外,撰写寿文志铭,成为另一文士与商人往来的重要内容。文士大家如归有光、唐顺之等或为徽商,或为宁波商人等撰写过充斥褒美之辞的寿文志铭等。名士以商人为经济后盾,可以照样风雅;商人由名士捧场,化俗为雅,于士人关系进一步融合。虽说并非所有士商之交皆以此为例,但由此却可看出士商关系契合趋势。
以上几点,可以说,构成了李梦阳多有商人形象创作并多溢美之词的社会背景。
三、 影响李梦阳文中商人形象创作的主观因素
从文学创作所必须接受的那些客观的规定、约束、限制方面,我们看到了文学创作的客观性质。但是文学作品又不是从那些客观的规定、约束、限制中直接产生出来的,而是经过作者的大脑反应、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过程、耗费了大量的脑力和体力而创造出来的。总之,文学作品是在作者受到他“涨满”的心灵的鼓动之下,直接从作者的心灵中流淌出来的。从这方面看,文学创作又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质。李梦阳的自身思想意识,构成其商人形象创作的内在主观条件,主要有以下两点。
1. 一方面,受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影响,李梦阳在艺术精神层面的自省与自赎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例如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的富商刘从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的商人之子扬州奴等。《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第二折中的富商刘从善唱道:“则俺这做经商的一个个非为不道,那些儿善与人交。都是我好贿贪财,今日个折乏的我来除根也那剪草。我今日个散钱波把穷民来济,悔罪波将神灵来告:则待要问天公赎买一个儿,也等我养小来防老。”诚然,富商刘从善等在财富的积累之中,既有他们的辛劳与智慧,也沾有老百姓的血汗,他们在“好贿贪财”、盘剥发家之中带有“原罪”。正因为如此,刘从善要“回心忏罪”,“舍散家财,毁烧文契,改过迁善”。最后,喜得“老生儿”。这从宗教层面来说,带有因果报应的意味;但从现实生活的层面来说,则是生动地反映了富商忏悔的心态及其赎罪的行为。这对元明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如主张文学复古的李梦阳,他同其他一些主张复古的士儒一样都有一个从自守到自省的过程。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李梦阳是明中叶复古派的开创者,又是自省与自赎的先驱。他自省乃至自赎,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主要是受到商贾忏悔意识的影响。早在正德五年(1510),他就在《庚午除日》诗中写道:“于今将四十,始悟昔年非。” 这样的自省与自赎,其动因之一是他深受到商贾忏悔意识的影响。李梦阳的祖父王(李)忠“为小贾能自活,乃后十余岁而为中贾”。正因如此,他的《空同集》中 ,寿文志铭、文本传序塑造了众多商人形象。例如,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所写“文显之为商也,善心计,识轻重,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助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故终其身弗陷于井罗。”并引晋商王现的话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由于坚持“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因而“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在义利兼顾的层面上沟通了文人与商贾的心灵。与之相关联的是,李梦阳也将文学上的自省自赎提升到追求“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的审美境界。
2. 另一方面,是直言敢谏、豪放坦直的性格,几度沉浮的经历
李梦阳直言敢谏,“不平则鸣”。《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中记“十八年,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末言:‘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 张氏即张鹤龄,孝宗张皇后弟,时封寿宁侯。李梦阳向皇帝刚直进言,揭露了张的恶行。寿宁侯匆匆反扑,抓住梦阳奏疏中最后一句“厚张氏者至矣”几个字,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手法,硬将揭露张国舅之“张氏”说成是讪骂张皇后之“张氏”。当时“皇后有宠,后母金夫人不已。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虽明知这样直谏得势者会遭报复,仍坚持不改。孝宗明白李梦阳所言属实,很快就将李梦阳放了,并召张鹤龄进宫训斥了一顿。但李梦阳受此屈辱,怒气不平,“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在与权豪势要的斗争中,李梦阳冒着杀头的危险,直言上疏劾奏国戚,甚至于事后还怒打权势。直言敢谏的直率性格可见一斑。
武宗即位后,原在东宫的一帮旧阉当权,干扰朝政、横行霸道,朝中正直官员多所不满。户部尚书韩文得内阁三老臣的支持,令梦阳执笔代作疏劾宦官,率群臣请诛刘瑾等八虎,此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李梦阳代韩文草拟的,就是有名的《代劾宦官状疏》。此疏九月上呈,十月,韩文率廷臣力争。谁知正德皇帝却在这个月让刘瑾入司礼监,“罢户部尚书韩文,勒少师刘健、少傅谢迁致仕”。刘瑾“勒罢公卿台谏数十人,又指内外忠贤为奸党,矫旨榜朝堂”。以“五十三人党比,宣戒群臣”。梦阳自然在五十三人之列,但由于当时刘瑾并不知劾章出自李梦阳之手,便将他在正德二年(1507)春二月放归田里。第二年五月,刘瑾得知劾章是李梦阳代草,又矫旨将李梦阳从开封抓到北京下狱,必欲杀之而后快,幸“康海为说,乃免”。直到当年八月,受尽折磨的李梦阳才被赦出。李梦阳再次对权豪势要的斗争,更显示出他倔强的性格和惊人的胆略。
被撤去官职后,“梦阳既家居,益弛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二十年宦海生涯,他指斥国戚、弹劾阉竖,曾几番下狱、数次罢官,可以说清节不渝、胆气过人。而在宦海的几度沉浮,更让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上流社会的污秽。正是这样的性格,才可能使他走在思想潮流的尖端,在士商契合的社会背景下比别人更早地融合进去。也正是这起伏波折的经历使他和庶民阶层的商人坦诚相处成为莫逆之交。与商人们的密切交往,为他的商人形象创作打下了基础。
作为我国古代一位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李梦阳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自由论证的精神,综合以上创作的主客原因,李梦阳笔下的商人形象散发出另外一种光芒,这是社会发展趋势的产物,也是作者自身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周虹.明清小说中商人形象浅析[J].传播学论坛,2006(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J].江海学刊,2002(1).
[4]陈书录.士商契合与文学思想的改变[J].文学评论,2007(4).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李梦阳诗学观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