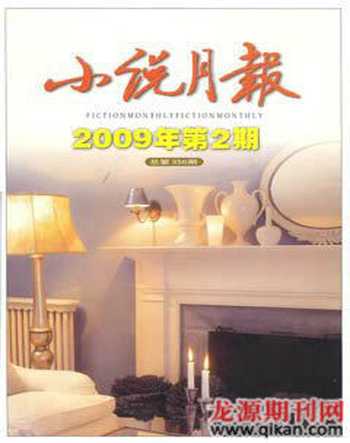发芽
我不喜欢黑骡子,甚至讨厌它。讨厌的原因很复杂,能说得上来的,最重要的是我怕它。我对它怀着很深的惧怕。我的形体与它相比,我简直就是一只贴在地面上的小蛤蟆,看它的时候我得仰起头。趁它乖顺的时节,我站在远处比划过,就算我拼力踮起脚尖,也只是勉强到达它的眉毛处。黑骡子的眉毛粗重而长,不比我的一头黑发逊色多少。可以说这头牲口在我眼里是又雄伟又高大,几乎就是庞然大物。
正是这头远比我高大雄伟的骡子,春种的时候,种到山洼上那片最陡的坡地时,爷爷忽然叫我拉着它去摆耧。爷爷一连喊了三声,我才回过神儿来。爷爷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火气,说,你聋了吗?叫你拉骡子哩。我当然没有聋,只是我一时真的回不过味儿来。黑骡子不是由碎巴巴拉吗?与那个庞然大物打交道的事怎么会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拉着黑骡子,我们开始摆耧。扶耧的是我的三爷爷。同我一样,他也是个惧怕黑骡子的人。在我们这几户人家里,不惧怕黑骡子的人只有两个——爷爷和碎巴巴。黑骡子就是爷爷买来的。爷爷喜欢黑骡子远远胜过了喜欢我们——他的任何一个孙子。每逢赶集,或者有其他事,需要出门走远路的时候,爷爷就会提前给黑骡子喂好料,临走,拉出来披上小棉被,绑上鞍子,是那种样式小巧,专门能骑人的红木马鞍,两边还各坠一个黄铜色的镫。爷爷到大门外,踩住门边的一个树桩骑上了骡子,手里拽着缰绳,拍一下黑骡子的脖子,它就出发了。去哪儿它似乎明白,不用爷爷吆喝,铃声叮当地响起,我们就知道黑骡子驮着爷爷去了。
黑骡子就是听爷爷的话,骑了几年也没出什么事,倒把爷爷侍候得神气十足,难怪爷爷看着父亲不顺眼的时候就吼,呸,养儿顶屁用,还不如我的黑子。黑子是爷爷为黑骡子起的大名。黑子确实叫爷爷在我们村庄里的老人中出尽了风头。别人赶集都是吭哧吭哧地用双脚板儿丈量那十几里山路。年轻人还骑个自行车,上了年纪的老汉没几人会骑那东西。再说,大多是山路,上坡时推着车,那个吃力,远比车骑人吃力。有人学爷爷的样,骑上了自家的毛驴。老汉们的毛驴与爷爷的黑子比,形象猥琐多了。毛驴上道坡,张着鼻孔出气;下坡时,臭棍勒紧,那屁就一连串地放,四个蹄子乱踢,身子一颠一颠的,弄得驴上的人紧张万分。再看黑子背上的爷爷,双脚套进镫里,身子放松,神态安稳悠闲,任凭黑子自个儿往前走。下坡时黑子的脖子高高仰起,骡子的背上简直与平地上一样平。爷爷不用猴子一样猫腰弓背,与平地上行走时没有什么两样。阳光照上,黑子的毛色像上了油,黑灿灿一片光滑,跟缎面一样。爷爷还弄来一串铃,出门前给黑子套上脖颈,这样,爷爷与黑子所过之处,一路铃声叮当,像有千军万马奔腾而过。爷爷在老汉们眼里几乎成了英雄。爷爷将自己的日子过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爷爷确实不是每个老汉都能学上的。他前半辈子当木匠,攒了几个钱,后半辈子不想干那叮叮当当的活计了,就拿出积攒的钱买了骡子,一来帮家里耕地,二来也可以给他当脚力。我们庄里养骡子的并不光爷爷一个,但将骡子调教到这个份儿上,骑出这样风光的,方圆似乎只有爷爷一个。别人的骡子只为耕地而饲养。他们不会给牲口大升大升地喂豆料,不会有空就守着骡子刷毛,拍打蝇子,伺候皇上一样伺候骡子。只有爷爷这样做了,还日复一日,坚持不懈。耕地的时候,骡子和老牛套一对,爷爷老偏心,鞭梢子雨点子一样落到牛背上。黑子竖着耳朵,有些惊吓地斜眼瞧着。老牛永远是一副雷打不动的蔫牛派头,怎么打也是逆来顺受无所谓的样子。打老牛惊骡子,骡子灵得很,不要打它,惊惊就行了。爷爷对耕地的人喊,生怕他的黑子吃了亏。黑子就骄傲得不行,耕地也高高仰着头,养得油光水滑的毛光滑得苍蝇趴上去也跌跟头。它不无骚情地抿抿耳,甩甩尾巴,还不时冲老牛打个响鼻。黑子还会看人行事,在爷爷面前它比新娶的媳妇还乖顺。碎巴巴拉它它也服帖,拉到沟里饮水时,碎巴巴踩一个地埂,噌一下蹿上了它的背。黑子有点儿兴奋,狂跳几下,碎巴巴死死揪住鬃毛不放,黑子就乖顺了,驮着碎巴巴一路小跑,到泉边喝了水,又跑回家。
我是从不主动跑去接近黑子的。我已经能拖动铁锨打胡基了,拉牛的活也干。可是,这一天,爷爷忽然叫我拉着黑子摆耧。爷爷的口气不容置疑。爷爷的脾气远比黑子的暴躁,动不动就给人一顿劈头盖脸的鞭子。我放下手里的牛缰绳默默走近黑子。原本我帮父亲拉牛,在地的另一边摆耧。老牛慢腾腾的,像架年深日久的老机器,已经老得快散架了,没有脾性与火气。我拉着它慢腾腾走,它拖着身后的木耧磨磨蹭蹭走。蹄子踏进土里,发出咯咯吱吱的沉闷响声,好像它的蹄子正在碎裂,化成无数的碎片。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挨近黑子。
摆耧拉牲口,就得拉着牲口的缰绳在牲口前面走,起的主要作用是牵引牲口,让它乖乖地顺犁沟拉犁,到了地头上,拉着它顺顺当当调过头。如此来来去去,往复不尽,一大片地就被耕种过了。我在黑子前头跑,小心翼翼地小跑着,手抓着缰绳的末梢儿,只怕跑得慢了黑子碗口大的蹄子会踏上我的脚。三爷跌跌撞撞地在后头扶着犁。三爷一向是个出了名的懒汉,身体不大结实,走路总是猫着腰。他一捉上木耧就哆嗦着说,叫我和黑子摆耧,这黑子我还是头一回使唤,这灵吗?它听我的吗?地实在是太陡了,在这样的地里即便什么也不干,只是空着手走走,以耕地的速度走上百八十个来回,人也会累得气喘吁吁,一不小心会栽个大跟头,何况是用性子焦躁的黑子种地。如果我们在这块地里种了洋芋,秋天挖出的大且圆一点儿的,总会骨碌碌滚向山下。山下就是我家的场地,洋芋它们等于自己跑回了家。好几次,我走不稳,被大胡基一磕碰,差点儿也像洋芋一样滚下去。山下的地里,碎巴巴正跟着爷爷和父亲学习摆耧。爷爷决定从今年开始,叫他的小儿子学习干重大的农活。他说要是碎巴巴今年考不上,就回来种地。
碎巴巴在中学里念书,念了好多年了,从拖着鼻涕念到现在的半大小子,听大人说现在到了紧要关头。爷爷不止一次用筷子敲着碗沿儿说,你挣破了头也要给我考上,考不上就回来打牛后半截子!打牛后半截子,就是跟在牛的屁股后面下苦干农活,当一辈子吃苦受穷的农民。碎巴巴小声地应着,眼睛眨巴眨巴地动,不去学校的时候,他就夹一本书躲在闲房里一个人叽叽咕咕念。碎巴巴念书的声音像滚得欢快的洋芋。
山下学习摆耧的碎巴巴把裤腿子挽起老高,白白的腿杆子不像个下苦的人,他捉耧的动作也不像。与真正的庄稼汉比,他像个闹着玩儿的娃娃,样子别扭极了。沉重的木耧不听他的使唤,他使劲儿地拧着耧把儿,弄得一身的尘土。爷爷在一边不住地喊,冷劲儿摇,放冷劲儿摇,稀了——稀了——他的意思我们都听得明白,摆耧的时候劲道用得不匀,种出的粮食苗儿稀稠不匀,影响产量。爷爷手里提着鞭子,好像随时会抽碎巴巴几下。看来碎巴巴今儿的遭遇不比我拉骡子强多少。
要是碎巴巴今年考上,就会到远处的城市里去上学。他去了还会回来吗?就算回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跟我们一起混吗?到那时候他就是大学生了,大学生是多大的学生,我们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年,我们附近还没有出过大学生,二十里外的李家庄倒是出了一个。听说那娃娃自从当了大学生,从城里回来,得他父母套上牛车到十里外的公路上拉他。家里人当皇上一样地侍候他。到那时候,碎巴巴也会那样吗?那样的话,还不如不要考上,回来当农民,我们大家一块儿种地,过日子。
爷爷的怒吼像平地滚过的炸雷,吓得我直哆嗦,惊出一身冷汗才弄明白他发怒的缘由。他用鞭子指着我和三爷说,你们站住,回头看一看,你们种的麦子,像人干的活计吗?
回头去望,我和三爷种过的地,简直就是娃娃刨土耍过的迹象。一道犁沟与另一道远近不一,忽远忽近,有些地方耕重复了,还有没有耕到的地方,干巴巴的地皮丝毫未动地放在那儿。如果不是回头看,真不敢相信,这些地是我们种过的,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这是块未耕种的荒地呢。黑子一拧一扭,忽东忽西,我和三爷几乎不敢对它咋样,全然由着它的性子走,加上地陡,我们种的地实在不像庄稼地的样子。
吃屎的货,一对儿吃屎的货!爷爷冲上来夺去了三爷的鞭子,碎巴巴也上前接过骡子的缰绳。他冲我挤眼努嘴,我明白他的意思,赶忙跑开去,到山下继续拉我的老蔫牛。只怕跑得慢了,又挨一顿爷爷的鞭子。爷爷的骂声还在继续。他这回干脆下了结论说,像你们这样种地,只怕有一天连吃屎也没有人愿意给你们屙。
他们从头开始,重新耕种那片地。我和三爷的劳动等于白白忙活一场,不但徒劳无功,还招来一顿臭骂。
种完麦子,种过豌豆,种完所有的庄稼,碎巴巴背上一袋干粮上学去了。爷爷也离开了我们的扇子湾,到一个叫红寺堡的地方去了。爷爷想骑着他的骡子,一路铃声叮当直达那个不知道有多远的红寺堡。父亲听后哈哈大笑,第一次毫不客气地挥手打断了爷爷的话。父亲的肚子都笑疼了,盯住爷爷说,骑上黑子啊,骑上黑子去红寺堡啊,你是想省下那笔车费啊,呵呵……你老人家知道红寺堡离咱们有多远吗?上千里路,远得在天边边上呢,搭车光路费就得好几十,你想累死黑子?爷爷睁圆眼,想了半天,终于决定不骑黑子了,把黑子留在家里。
过了些日子,爷爷回来了,话语里夹了些我们从未听过的口语,这是只有在大集市上的外地人嘴里才能听到的。爷爷说和他一块儿打交道的是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的人。爷爷对父亲感叹地说,不出门不知道,出去了才知道外头的世面有多大。幸好听了你的话,没有骑上黑子,骑上的话,可把麻烦弄下啦。父亲无声地笑笑,笑声里有一丝得意。
爷爷看看黑子,看看老家,交代一番又走了。他现在真正忙起来了,他在那个红寺堡为我们弄了一个新家,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连家带营搬走,永远离开这偏远的穷山沟,到川道地方过日子去。在搬去之前,爷爷得先为我们种地,盖房子,把那儿收拾得像个家了,才敢将老小十几口人全搬走。
到时节黑子怎么办?我们几乎同时想到了黑子。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其他的牲口,单单记起了黑子。其实我们养的有生命的东西不少,比如与黑子朝夕相处的老牛,老牛生的仅仅三个月的小牛,羊圈里的三只绵羊,满院子转悠的七只母鸡,一只整日耀武扬威的大公鸡,还有栖息在崖顶上土窝里的无数麻雀。当然,还有躲在幽深处偶尔露面的狡猾的老鼠。细细想来,在这个老家里,我们生活过上百年的地方,其实到处都有生命在活动。到我们搬家走的时候,它们可怎么办?能带上它们吗?然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黑子。想来想去,其他的就卖了吧,变卖成钱装在口袋里,既方便又轻松,不能卖钱的就任由它们去吧。只有黑子,不能不叫人多为它想想。黑子是爷爷的得意脚力,爷爷会舍得把它卖给别人吗?
爷爷隔上五六个月就回一趟老家。他将我们这儿称作老家,给人感觉我们这儿已经很老很老了,老到头发全白,牙齿松动了。爷爷回来不为别的,是来拿钱的。只有足够的钱才能在那个地方为我们建设家园,开始生活。爷爷感叹着说那个地方啊,干啥都得花钱。坐了一天车的爷爷显得神情委靡,疲乏不已,但当说到红寺堡还是兴致勃勃的,给我们描绘将来的美好日子。
爷爷装上我们凑起的钱就匆匆走了,连黑子也没有顾得上多看看。黑子由父亲喂养。父亲忙的时节,母亲会给它添草料,母亲是拿着棒小心翼翼添草的,但没人敢拉着它到沟里去饮水。碎巴巴在学校里念书,念到最紧要的关头,几个月也不会回趟家。桀骜的黑子,我们不敢放它出门,拴久的狗一旦出门都会胡乱咬人,狂奔不已,何况是原本就威武的黑子。饮牲口的活计一般由娃娃担当。父亲忙于农活,我们就想出了个折中的法子,两个娃娃把水从沟里抬回来,倒进盆子里,再端给黑子喝。这样虽然我们很累,可省去了不少麻烦。黑子只好整日与老牛为伴。以前,黑子总是一副意气非凡,不屑与老牛为伍的神气,它天天出门,披挂整齐蹄声嘚嘚地奔走于四方,几乎走遍了方圆的集市与人家。这对于老蔫牛是不可想象的事。
谁想得到爷爷会心血来潮,跑到那骑上黑子也不容易到达的地方去了。黑子这回没有理由继续逃避农活了,它得与老牛一起干活。老牛肚子大的时候,父亲干脆让它歇下,让黑子一个拉单套。黑子毕竟是吃过几年豆料的,独自拉单套一点儿也不含糊,远比与老牛成双时快当。父亲喜得不行说,看来把老牛卖了,养黑子一个也行,咱的三十几亩地随便就耕种了。
粮食种子埋进土里,大地就复归于平静。喧闹了一个春天的土地在安安静静一心一意地准备发芽的事情。碎巴巴临走之前,带我到崖顶上去,我们用铲子把一片地挖了一遍。不大的一片地,大人看不上,撂在那儿成了荒地。三年前,碎巴巴和我,我们一点一点开了荒,开辟成一片自己的田地,然后种上了豌豆,还背了一背篼粪土撒上了。那年雨水足,豆子居然开花结果了,结了一大捧豆角,我和碎巴巴一会儿就吃完了。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香的豆角,毕竟是我们自己种的。最后碎巴巴拍着屁股上的土说,这是生荒地,还没肥力,再过几年就成了熟地,那时节咱种啥丰收啥,美死咧!
去学校前,碎巴巴就带我种上了我们的地,照旧种的是豌豆。正是种麦子的时节,种豌豆还早了点儿。豌豆不比麦子耐寒,出苗早会冻死的。但碎巴巴要念书去,时间是不等人的,我们就在一个刮春风的下午种上了豌豆。碎巴巴临走说,照料豌豆的事我交给你了,操点儿心,发芽出苗时节给上面苫一抱胡麻柴,霜冻过去,就把柴揭了,过七八天就会发芽的,操心啊……
碎巴巴的一个肩膀上背着一个大书包,另一个肩膀上背着一包馍馍。两个肩膀同时负重,一颗头独独立在中间,使得他的头显得突兀孤立,让人觉得他的头长在那里是件很突然的事。
碎巴巴走了,爷爷也走了。春天真是个充满活力的季节。尽管天气一直旱,开春以来一滴雨也没有落,麦子还是靠着冬天积存的那点底墒发出了芽。我天天都在看我们的豌豆。这是我们给自己种的粮食,大人不会来过问,更不会插手多管的。给家里种地实在乏味得很,常怀着愁苦无奈的心情。不干活是不行的,每一个人都得干活,累得死去活来。不干的话,大人的棍棒便会追上来噼里啪啦地打着屁股。可是我们自己种地,极少的一点儿地,种的过程充满了乐趣,我和碎巴巴都乐呵呵的,感到信心百倍,其乐无穷。
麦子发芽了,刨开地皮,土里的麦子变得胀乎乎的,白白的细芽从麦粒身上的裂缝里挤出,同时挤出的有一根带须的芽,看来是将来的根须。该去看看豌豆了。豌豆似乎在土里正睡得香甜,不愿意露出面目。我们当日撒下的干豆子,现在变得软和了,却没有发芽的迹象。都好多天了,它们怎么还没有动静。我有些担忧,再刨几颗看看,还是这样。只好对自己说再等等吧,说不定明天早上它们会苏醒过来,记起来赶紧发芽的事。
这天下午,正当我对着迟迟不肯发芽的豌豆不知所措时,听见崖下传来咣当声,不由得将目光转向崖下。崖下正是我家的后院。后院里一边是牲口圈,一边是茅厕。我看见牲口圈的木条门在晃动,后来被撞开了,一个黑色身影跑出来——是黑子。我张大了嘴,第一反应是赶紧喊人关上大门,可是嗓子眼儿里像被塞上了棉花,急死了就是发不出声,眼睁睁看着黑子径直冲出了大门。它的身子被大树挡住,看不见了。我忙向崖下冲去。父母他们到哪儿去了?黑子出了门他们知道吗?然而,我看见路上腾起一团土雾,挟着一股巨大的风,黑子向下庄方向狂奔而去。不分大路、田地,还是巷道,黑子它横冲直撞而去。父母闻声跑出大门,黑子已经不见了。
我们循着土雾追赶过去,不少人也闻声跑出家门。黑子冲进了一个巷道。我们似乎听到巷道深处传来女人的尖叫、娃娃惊恐万状的哭喊。母亲忽然大哭起来,哎呀呀,万一踏上人家的娃娃咋办哩?我们没法儿活了呀!父亲顿时面如土色。大家急惶惶赶上前去。黑子像离弦的箭,裹着恶风直冲过去,那么突然凌厉的冲击谁也躲不及的。我们好像看见四只碗口大的蹄子高高扬起,踏在了娃娃的头上,头顿时就开了花,鲜血四溅。母亲瘫倒在地上,连哭声也发不出来了。
忽然,黑子出现了,从那个狭长的巷道里出来了。它高高仰着脖子,冲天的鬃毛哗哗地抖,它眨巴眨巴眼,看看我们,忽然瞅着一个方向跃了开去,跑进了一大片庄稼地。耕过不久的田地,麦子在土里做着发芽的梦,黑子却张开四蹄兴奋张狂地打起旋儿来。跑几圈子,停下,看看远处发愣的人群,又狂奔起来。如此不断反复,仿佛在和人们开着一个长长的玩笑。早发芽的麦子被蹄子践踏,露出白生生的芽子来。
父亲眨巴着眼到巷道里去查看灾情有多严重。他小心翼翼地跑着,显得忐忑不安。一个女人哭叫着跑出巷道。众人的眼睛顿时直了——是李文义的女人。她用巴掌拍打着自己的大腿冲着父亲喊道,我的麦子呀,把我的麦子糟蹋完了……马撒巴你把先人咋拴的?可把我害苦了!
我们睁大眼细瞅,李文义女人的全身上下,胳膊腿儿全好好的,头也不是血水四溅开了花的可怕景象。她还在哭叫,扑向父亲,一副要把这个叫马撒巴的男人撕碎的架势。
我们却一起高兴起来,骡子没有伤到她,她只是在哭自己家被糟蹋的麦子。这时巷道里拥出大批女人娃娃来。大家闻声看热闹来了。女人们个个笑着,娃娃也好生生的。父亲把他们从左边瞅到右边,再从右边看到左边,没有意料中的头破血流哭天喊地的场面。大家都好好的,黑子没伤到人。父亲一拍大腿也哇地哭开了,哭声之大,把李文义女人吓得止住了哭声。娃娃们笑嘻嘻地看着这个罕见的场面,一个大男人会像女人一样喜极而涕,当众大声地哭,这真是件稀奇事。
有女人尖叫,拿盆子来,端盆豆料哄哄,骡子会听话的。喊声提醒了大家,姐姐立时跑回家去,端来半盆子豌豆。父亲簸着豌豆,嘟儿——嘟儿唤,慢慢凑近黑子。黑子跑乏了,索性躺在一片地里打起了滚儿。它躺倒也是很大的,四条腿像柱子一样那么有力地朝天晃着,打完滚儿,站起身来,怔怔地盯住围观的人看。看来它的狂性发作得差不多了。
父亲继续呼唤,绿色的豌豆在铁盆子里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黑子看了一阵儿,忍不住缓缓靠近前来。父亲伸长盆子小心递过去。黑子用鼻子嗅嗅,犹豫一阵儿,嘴伸进盆子大口吃起来。父亲一手端盆子,一手凑过去,慢慢抓住了笼头。原本带着的一截缰绳早就不知到哪儿去了,可能在狂奔中被踩成了零碎。人们围上前纷纷议论着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大家纷纷感叹今天幸运,那些平时在巷道里玩耍的娃娃,今天的这个时刻,商量好了似的,没有一个留在巷道里,全部回了家。要在平时,今天的祸事是不可想象的,肯定被骡子踏坏不少人。这景象想想都叫人后怕不已。有人认为,骡子是在家里拴久了,猛一到外面欢喜得不行,才发疯地狂奔,父亲应该常拉它出来遛遛的。是人关久了也会心慌的,何况是自由惯了的骡子。也有人说黑子毛色大不如以前,有些干,脏不啦唧的,影响了它的外貌。父亲苦笑,他和母亲忙地里的活计,从开春忙到现在,忙得脚不沾地,昏头转向,哪还有闲工夫陪着个牲口溜达呢。
那就拴牢实些。大家提议。那些被踏了麦地的人脸色明显阴着,显示着内心的不舒服。李文义女人撅着大屁股,一个一个去刨那些坑,把露在外面的麦子埋起来。她口里一直嘟囔个不停,马撒巴不把他先人拴牢靠些,放出来故意糟蹋人的粮食呢。她的叽咕我们都听见了。父母面带愧色,拉着黑子赶紧回了家。晚上灭灯后,他们在被窝里说了半夜话,都是关于黑子的。看来这黑子得加倍提防了,又商量了一大套防备的法子。夜很深了,睡梦里翻身时,我还听见我的父母在庆幸,带着后怕的庆幸,说要是真的踏上了娃娃咋办呢,麻烦就弄大了。这个黑子。
我想到了碎巴巴。我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想他,非常非常地想念。从他背上书包走的那一刻,就开始依依不舍地想念起来。碎巴巴他想得到吗?黑子会闯这么大的祸。他该回来遛遛黑子了。父亲当夜就把一条拴过狗的铁链子给黑子当了缰绳,把黑子牢牢地拴在槽边的大木橛上,还给门框又钉了几条结实的木板。黑子现在一动弹铁链子就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响声不断,好听极了。可是第二天我们就厌烦了。黑子打个嘟噜链子响,黑子毛梢儿抖动它也响。看来黑子得永远活在这单调的永不止歇的哐啷声里了。老牛带着它的儿子到另一个槽上吃草。这下老牛可以安下心过好日子了,再也不用发愁会被驱赶得走投无路。添给老牛的草料,黑子无法抢上,老牛慢悠悠长时间品尝着。黑子霸王一样的日子画上了句号。
日子安静下来了,我的心里却总是无法踏实,我焦急地等待我们的豌豆发芽。春风已经很暖和很柔软了,刮了一个冬天的西北风里总像带着细小的尖利的刃片,丝丝缕缕划割我们的肌肤,让我们皮干肉糙。春风里至少含上了阳光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柳树枝头隐隐透出一层绿意,麦子的苗破土而出。老远望去,地面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绿。而我们的豌豆还是一副沉稳不动不谙世情的模样,仿佛它们留恋土里的温暖,不愿拱破地皮,向上长出绿色的叶片。我真的没有足够的耐心继续往下等待了。母亲把鸡蛋和鹅蛋一起放在母鸡的肚子下,放着放着,蛋皮破裂开来,钻出一个个小鸡小鹅。生命的开始,就像发芽,小鸡小鹅就是蛋发的芽。小家伙们暖干了身子,身上的茸毛舒展开来,就成了一个个滚动的毛线团儿。母亲眉开眼笑,把它们卖给庄里的女人们。接着攒蛋,让母鸡继续孵蛋,让大大小小的蛋在母鸡的肚子下慢慢发芽。
下雨了,星星点点的细雨居然连着下了两天半。别看这小雨来势微弱,时间长了,总有润物细无声的功效。母亲到地里看了,说土里湿下去四五寸呢。春天的雨比油还要金贵呢。天刚一晴,大家就套上牛抢墒耕种了,秋田类庄稼可是一样还没有种呢。大家盼的就是这场雨。老牛和黑子重新套成一对。母亲拉着,父亲耕种,姐姐撒籽儿,我跑腿打零杂。反正我们忙得脚不沾地,一连忙了七八天。
忽然有一天,记起我们的豌豆来。我跑到崖顶上去看,地面上竟然长出了绿绿的叶芽,正是豌豆初出土时的样子。大多数地方出苗了,稀缺的地方,我刨开土看,一个个白芽正往上长,嫩白的芽子怕羞似的蜷缩着身子,我赶紧重新埋上土。它们得以发芽出土,看来是这场雨水的功劳。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有几棵正顶破地皮往外拱的芽子,像调皮的娃娃把身子藏在土里,头上顶着土块,然后探头探脑向外张望,张望外面的世界。似乎正在犹豫,犹豫该不该从土里钻出来,来到外面的世界。我盯住它们笑。我知道它们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谁叫叶芽已经拱破了地皮呢。都半张脸露在外面了,还想回去吗?回得去吗?见过从娘肚子里生出又回娘肚子里去的娃娃吗?
春雨竟然隔三差五地下。夏天时候,还落了几场暴雨。真是少见的好年景。麦子长得泼了油一样,墨绿墨绿的。豌豆花儿开过,很快就挂出一身大刀似的豆角。我和碎巴巴的豌豆也结出了豆角。豆角鼓起来能生吃的时节,碎巴巴回来了一趟,拿走了一些钱,他要考试了。他匆匆来,又匆匆去了,居然没顾上看一眼我们的豆角。我觉得豆角吃进嘴里没有往年的脆嫩与甘甜,苦巴巴的。碎巴巴在就好了。他吃豆角的样式可多了。剥了皮的豆角泡在凉水里,泡得全部打起卷儿,一个个绿卷儿,咬一口清脆极了,那感觉,凉快又清爽。我学着碎巴巴的样子泡了几回,却一点儿也不好吃,有种说不出的苦涩味儿。
割麦子的时节碎巴巴回来了。我们的豆角已经长老了,变黄了,我用手拔了它们。碎巴巴始终没有问过我们一起种下的豌豆怎么样了,他回来时豆子几乎收割完毕。大家一心收割麦子。黑子也被带出来了,拴上长长的缰绳,把木橛打进割过的麦地里,让它绕着圈子吃草。有碎巴巴照料,黑子乖顺多了。
割罢麦子,碎巴巴骑着黑子出了趟远门。他回来的当晚,我们围着父亲,全家在院子里的月色下坐了好半夜。父亲乐呵呵的,因为碎巴巴考得不错,这次去填了志愿,过不多久就该上大学去了。父亲有些陶醉地说他没有看走眼,碎巴巴是块念书的料。碎巴巴像个大姑娘,低头抠脚缝里的泥。月亮底下看不仔细,可以料想他的脸是红的,有些不好意思承受这么郑重的夸奖吧。
碎巴巴报的是师范大学,一张叫做通知书的纸到达我们家的那天,已经是玉米棒子成熟的时候了。麦子豌豆胡麻一类庄稼我们全碾了,收成不错,父亲乐呵呵的。我们按照通知书上要求的数目准备钱。父亲早就有准备了。开春种了十几亩胡麻,这是粮食里头价钱最好的。我们把红灿灿的胡麻晒干扬净装进口袋,放进牛车里,由黑子拉着,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去卖。我们总共卖了两车子胡麻,一车子麦子,一车子豌豆,父亲数着钱说这回差不多了。母亲从一开始就有点儿不大情愿,背着碎巴巴在父亲跟前嘀咕,人家苦死苦活种了一年庄稼,总不能连口粮也卖了吧,全叫他拿走了,咱明年开春庄稼咋种?买不买化肥了?父亲笑着说,你这婆娘还真的没个长远见识,咱供养大学生呢,不吃苦咋行?母亲想了一阵儿,笑了,说有个大学生当兄弟,还真个不一样,庄里的女人都眼热我哩。
就在我们为碎巴巴准备行程的时候,黑子病了。它是什么时候病的,我们没有留意。当时我们一边忙于收割秋庄稼,一边耕地。父亲吆着黑子和老牛耕地,每个早上都得去耕一趟。
有一天母亲一大早嚷嚷说添给黑子的草料咋没见少。父亲不太在意,随口说它可能太乏了,缓缓会吃的。第二天还是这样,却是没命地喝水,总也喝不够的样子。父亲拌了些豆料端去,黑子伸鼻子闻闻,吃了几口,想吃又不大想吃的样子。父亲说明儿耕完地到集上看看,可能病了。
第二天耕地时,黑子大不如以前。腰身缩成一团,怕冷似的,使劲儿地抽搐着;毛分外地长,颤颤地抖着,粪末子草屑子早挂满了全身。黑子没心思抖落它们,也没有心思拉犁。父亲狠劲用鞭子抽,它还是颤巍巍有气无力地晃悠着。这可不是黑子那一向雷厉风行的做派,神威凛凛的黑子从不偷懒的。父亲摸一把它的脖子,汗像水一样往下淌。父亲立即解下套,和碎巴巴拉上黑子去看,十几里外的集市上有专门为牲口看病的兽医站。黑子在父亲他们的拉扯下走出了我们的视线。它走起路不怎么利索,一直怕冷似的,发着颤。临出门,母亲把一片旧毡披在它身上,说黑子怕是着凉了。
下午时分父亲一个人回来了。黑子被打了一针,走路慢腾腾的。父亲等不及就及早回来了,地里的一大摊子活计等着去干呢。我们戴上草帽,提一壶水下地了。
在地头上磨镰刀时,母亲闷头问了句,黑子到咱家几年了?算上今年,有五个年头了。父亲不抬头,说罢,噌噌地割他的糜子。
日头一点一点挪向山畔。秋天,随着庄稼的收割完毕,秋草显出苍黄的颜色,世界一下子辽阔空旷起来。山野间的风呜呜地叫着,秋天的日头显得慵懒多了,似乎它赶一天路,也困乏得不行,乏乏地移到西边的天空,缓缓地沉下山去。看着落日,人已经能感觉到寒冷了,深秋的冷意十分明显起来。父亲看一眼远处的山路,再看一眼,看了无数遍,就是不见碎巴巴牵着黑子归来的身影。父亲终于不敢等了,交代几句,又踏上了通往集市的那条山路。我们在心里一起犯嘀咕,碎巴巴和黑子迟迟不回来,到哪儿去了呢?
日头终于跌下山窝,西边的最后一点儿红光被山峦吸收干净。父亲披着暮色回来了,身后跟着碎巴巴。碎巴巴手里拖着一串铁链子,却不见黑子的身影。
黑子到哪儿去了,咋没有回来?
死了。父亲拍拍身上的土,故作轻松地又说,死了好,这牲口原本难养,弄不好还给人闯大祸哩。
话是这样说,一家人的脸上还是禁不住流露出难以说清的情绪。
碎巴巴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着头上炕就睡了。他睡着了,父亲才幽幽地说,这个瓜兄弟啊,心思重得很,我碰到半路,黑子早死了,他守着黑子哭,眼睛也哭肿了,没命地拽着黑子的缰绳,叫黑子起来,起来一起回家。
母亲叹一口气说,他还是个娃娃嘛,再说,养了这么多年,谁心里也不好受。这一年,咱连一升好料也没舍得喂它。
第二天一大早,碎巴巴按父亲的吩咐走了,去叫附近的汉民,让他们把骡子拉去,到时候给我们留张皮就行。当天碎巴巴就把皮子拿到集上卖了。卖的几十块钱,父亲让他拿到学校零花,就当黑子为供他上学出的最后一点儿力。这个黑子,原本准备叫它出大力的,家里出了大学生,用钱的地方多着哩,它这么早就溜了。碎巴巴捏着钱,眼睛里头红红的。
晚上,碎巴巴在灯下给爷爷写信。父亲边思索边口述:我们好,都好,收成好,只有黑子不好,它害病了,碾完粮食耕完地就病了,没看好,死了。我们围成一圈儿听,看看父亲的神情是认真的,听他的口气是严肃的,不像开玩笑,就把一点儿失笑压进肚子。父亲他分明把黑子当成了一口人。
碎巴巴上学走了。他揣着一疙瘩钱,由父亲陪着走了,到遥远的大城市里上大学去了。他这一去,什么时候才回来呢?回来还会和我一块儿种豌豆吗?我不知道,将来的事谁也不知道。我用小铲子把那片地挖了一遍,拍平整了。明年,不管碎巴巴回不回来,我还得继续在这儿种豌豆。这块地不能叫它撂荒了。
我常常望着远处跌宕起伏的山峦,禁不住思念一个身影——黑色的闪电一样的身影。
【作者简介】马金莲,女,回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人。先后发表小说、散文随笔二十余万字。现居宁夏西海固,为《黄河文学》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