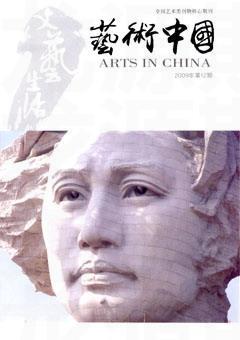淡泊自然绘人生
鲁 琼

在谈及湖湘文化时,不少人都认为“蛮”是其中的一个特质。有人甚至还说一个蛮字可以概括出湖湘文化的特质。如罗敏中先生就说,蛮是湖湘文化之源。今之湖南,古之楚地,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楚人,不封闭,善吸收;楚人敢破格。常超越,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
湘人民风彪悍,邵阳又是其中翘楚,而生长于此的莫高翔先生却完全没有丝毫“湖南蛮子”的“匪气”。无论是与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或是交往甚久,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位极其温良谦和、让人心生敬慕的师长,但偶尔遇事还是难免跳脱。先生平日生活随性。不拘于繁繁踵踵之琐事,但对于画事却执着得近乎任性,这恐怕也是骨子里湘人的“蛮”劲使然。
莫高翔先生生长于湖南邵阳某一偏远山村,那里有葱郁的青山绿水,有肥沃的梯田坡土、错落有致的农家村舍;两条清澈见底的溪水绕村而过,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成了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联络。据先生回忆,前前后后有两百多名大学生由那条被磨得光亮如镜的石板路走出山村,先生正是其中之一。不记得谁曾说过,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实则根植于农村,他们仍恪守中国千百年传袭而来的古老文明。先生故乡的乡民正是如此,倔强淳朴、勤劳善良,有着崇文尚礼的习俗和尊师重教的风尚。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那里的生活仍是按照一种特有的文明力量在自如运转。那种山明水秀的自然意蕴和那种古老文化所积淀的内涵,无疑是先生成长的主要养分。他崇尚“包前孕后”的艺术繁衍之说,尊重传统中具有永恒生命的艺术,不管周围的艺术是如何风起云涌变幻无常,他都始终如一,重视自己的体悟,潜心静穆,从容坦然且坚定地走着自己选定的路。
先贤中,屈子爱兰,广植九畹;陶公爱菊。遍采东篱;老逋爱梅,钟守孤山;与可爱竹,胸藏千亩;敦颐爱莲,出泥不染,皆因性致相近而好之,而能入画的闲花野草之于先生亦是如此。在莫高翔先生的画作中,你极少能看到造型夸张颜色艳丽的奇花异鸟,取而代之的是大自然间饶有生趣的野逸之物,如一丛山花、几支芦苇、半亩包菜、一墙牵牛、数颗芭蕉等,点缀其间的也只是三两只山雀、鹭鸶、秋雁或游鱼。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在先生的笔下、画中常常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平时并不起眼的质朴之美。幼时在田间林中嬉戏玩闹耕种劳作自然于脑中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们与先生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更为亲近,更为贴切。但我以为先生淡泊随性的性格才是一直选择此类题材的重要原因,即所谓在绘画中亲近自己,回归天性。
自明清以来,工笔画的地位逐渐边缘化,被人诟病的恰在这个“工”字之上,它与相较随性畅意的写意画似乎略显刻意为之的雕琢痕迹。莫高翔先生的工笔花鸟画对“工”字做另外的探求,工在活,工在生动,追求自然清新与淡雅质朴。曾有人以“天工与清新”来评价他的工笔花鸟画艺术。这里所谓的“天工”不仅仅是技艺高超的概念,它还有无斧凿痕的自然意味,悉心经营却又能不露半点痕迹,可想而知其造诣之高。
莫高翔先生朴素平实的审美倾向不仅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更表现在其绘画是色彩语言当中。他用色单纯。淡化和简化了自然色彩,这种主、客观色彩的置换,使画面呈现出清新的艺术形式美,也与他的性格交相辉映。所以即使是描绘清丽的荷花、冷艳的芙蓉,也将其色彩反复过滤成淡淡的浅红、浅黄或洁净的白色,甚至将翠绿的竹也画成黑白的墨竹。常用的颜色是墨和花青、白色,因为黑色、蓝色、白色最容易让人产生清和静的联想,偶尔画绿色、红色。但多以大块的墨色为衬托,使之不火不煤,倾向于清静。工笔画的美感特质主要源自渲染的效果,因此,他反复探研各种不同的渲染方法,如干染、湿染、碰染以及他自己独创的皴染方法。这些染法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使画面形成了极为浓重的彩墨效果,既典雅庄重又韵味盎然,传递给观者独特的艺术语言美感。
莫高翔先生的花乌画之所以动人,还有一个因素是在构图上的新颖与巧思。纵观其作品,几乎找不出与前人或他自己互相雷同的构图,即使画的是同一对象也力求有全新面目。先生认为,构图不是简单的位置经营,相应地说也是一种抽象的构成,是对画面整体形式美的设计。
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其对大势的设置、主次的剪裁、节奏的控制、疏密的安排、虚实的处理都十分精妙独到,尤其是对空白的布置和运用,几乎达到完美之境。
自五代以来,中国工笔花鸟画开始分化为华丽富贵和澹泊野逸的两大体系和风貌,而莫高翔先生的花鸟画可以上期五代野逸派之遗风。在观摩先生众多画作之后,更多的是令人感到那扑面而来的质朴、率真和坦诚,还有那秀丽清隽的风度。那遍地落叶、满目杂草和独自灿烂的山花被先生描绘得十分趣致。他在层次复杂与丰富深远中营造出了温馨与冷寂、热烈与淡雅、丰富与单纯同在,并融为一体的诗情画意。这些都是经历了由外至内、因物动情,进而由内至外、寄情于物的转化过程。所呈现的是天趣与人的内在精神关系,是奇造化而移精神,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自然纳入自我,而自己又消融在景物之中,完全贯穿和表达了中国艺术精神中“天人合一”、“复归自然”、“形神兼备”的艺术哲学观,创造出无我之境。
古人云“人物传神,山水留影,花鸟写生”,花鸟画自唐宋以来被称为“写生”,意为“写之欲生”。“写生”是对花鸟形神的一种艺术境界上的追求,是对自然的深化与升华。在宋代众多画论著作中都以“生意”评价称赞画意之高。莫高翔先生在日常教学中反复强调不仅要“应物像形”。更要“写其生意”,不仅是在写生时,更要在平日留心观察和体味,这样才能对世间万物微妙的变化有所感悟,才能让作品更生动,更能打动人心。
无论对于读书做人或治学,有一颗善感的心都是最为重要的,他就曾在某篇随笔中写到:
“感悟。感在前,悟在后,有感方有悟。故感悟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在其远,贵在其行。读万卷书既贵其读,更重其悟。”悟在读书明理,澄怀散抱。清人沈宗骞云“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日清心以消俗虑;二日善读书以明理境;三日却早誉以几远到;四日亲风雅以正体裁。”具此四者,自然通达。
每个人的生命伊始都是伴随着哭声而落地,没有哪一个婴孩生下来就能读会写出口成章。因此道理再明白不过,无论出生如何,起点都大致相同。但随着年龄增长,何以会出现能力的参差不齐?究其原因大概是在于后来的治学态度。古今中外诸位先贤都曾说到做事不应以功利为先导,耕耘本身就是收获。做事,有时仅仅出自天性。当很多人在学“四两拨千斤”的技巧时,莫高翔先生却主张聪明人应下笨功夫。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学都应勤勤恳恳,事无巨细亲历为之。现在这个社会聪明人容易做到,笨却很难实现。随着年纪渐长,我的某些观点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看到孤独的人玩味自己的孤独,沉默的人张扬自己的沉默,多情的人抒发自己的多情,智慧的人炫耀自己的智慧,心理便会莫名抗拒。现在的我更倾向于认为,活力和魅力来自反差,来自另一端、与之相反的那些特质。比如,聪明人应该笨一些,或者说。一个人能笨下来,就自然聪明了。人同此理,事同此理。
工笔画源远流长,其形式技法至唐代已趋成熟,至五代臻于完善,至两宋时已达炉火纯青的高度,最能代表工笔艺术成就和技法高度的是两宋时期的工笔花鸟画。不论是对初次接触工笔的本科学生还是对已有创作经验的研究生,在教学上莫高翔先生都十分重视对宋画的临摹和深度解读。而他自己钻研传统工笔画数年,尤其是对宋人的工笔花鸟有过深究,其精深的程度,无论是审美理念、构图特点、技法形式、造型方法等几乎都了如指掌。而且不仅仅是知识性的认识和掌握,更有实践性的领会和运用。历代书画名家,没有一位不是博采众家之长后吸收以为己用,要能吸收前人经验,继承传统就要做到临摹古人,求用笔明各家之法度,论境界知各家之胸臆,用古人规矩抒我胸意,即要具古以化却又不能泥古不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继承的基础上谈到创新。他是这样教导学生,也是在数十年的艺术道路上身体力行不断探索。“以书入画”也是先生平日所强调的,他常说学习国画之人不仅要把书法当做曰课刻苦研习。还要博览群书,因此这里的“书”也指的是读书。不仅要熟读专业理论技法专著还要对于文史哲各科都有广泛涉猎,即所谓功夫在画外。只有这样才能有理论作为支撑,才能使作品具有更强的精神力量,使自己的艺术道路更为长远。在这个一切都可以以利益来衡量的时代,在这个艺术家与街边叫卖的摊贩无异的年代。先生依然还能安坐于那间冬冷夏炎且并不宽敞的画室内,对求学若渴的众多学生——悉心指导,并以此为乐。
先生常说:“画为心声,画如其人”。画的是花鸟,但必须见人的思想、人的品格、人的修养、人的情感。做人毕生追求澹泊自然,为艺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