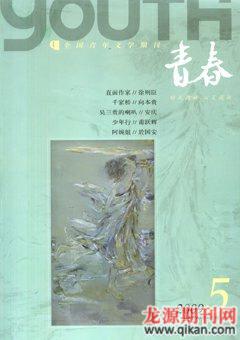失踪者的旅行
楼下的小巷
这是一个临街的小区,打开窗户,外面的喧杂人声便传递上来。小贩的吆喝声就响在窗根下面,每一天,都响在窗根下面——他们多是一些收垃圾为生的外地人,同我一样,没有在这城市里扎根。这里的老居民或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从早到晚,摸不准什么时辰,就会有推着平板车的人从巷子里走过。他们在这里走了多少年,一拨一拨的,搞不清谁是谁,更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我在半梦半醒中,始终分不清声音的来处,更不知道这将是我生活中的大半构成。我在这里住的时间还不够久,或许终将不够久。我在这个城市里动荡流离,迁徙的次数足够多了,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日子还将持续到什么时候。
夜晚很深的时候,我终于有时间久久地站在这里了,纷乱的思绪却无法收拢。日子过于忙乱,这里的一切,连带我的三十岁,都很轻易地被岁月吞没了。我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开始锈蚀,然而我还没有到老的地步呢。出租车像一条爬虫,在夜的肠胃里蠕动,我从三层楼这么高的地方望下去,几乎可以看到车里坐着什么人,甚至在灯光一错的刹那,还能够捕捉到他们脸上的表情。
夏季的夜晚,可以匆匆地走失无数人。站在这里看去,许多人与事情都没有停留。就像我刚刚下班回来的路途上所看见的一对乡下夫妇,他们露宿在午夜将至的街头,微风掠过他们的脸庞,他们舒适的睡姿如同在家中无异,然而他们从此远离的村庄,已经成了难以返回的故土。
在白昼,我还遇到类似的沉睡,是从午后两点到四点这个时段,我到这个城市的南边办事,就从楼下这条巷子的一段石阶前往返,一个脸朝墙面睡着的男子一直未醒,并且从始至终,似乎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他的身后,是一条可以并行两辆轿车的狭窄的城市马路。偶尔有一辆货车轰隆隆地经过,树木的枝条被拖住了往前一拽,然后一股大力将叶子扯断好些,纷纷扬扬落了一地。
如果长时间在忙碌,我常常看不清岁月。是一种惯性在催促着自己前行。身在物外,非但记不起了许多固有的生活需求,更将曾经做过的事情忘个精光。只有当事情告一段落,我才能够定下心来,看看自己置身的这段生活。
有一个午后,阳光变得那么明亮。蓝天白云就在头顶,似乎并不很远。穿堂的风从屋子里经过,把放在书桌上的稿纸一页页吹落。还有报纸和杂志,上面发表了我的几首诗。我想起自己在深夜里的写作,仿佛已是远年的光景,它们与现在的一切并无关联。有一些时候,我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回忆,才能够让最近几个月的光阴重新在我的眼前变得清晰。
已经从我们的生命里逝去的那些日子,将从另外一个角度组成我们新的生命。对此我总是深信不疑。从现在我所住的这个小区出发,向西南方向行不多远,便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广场。我在那里辗转多次,对于它的感觉,也类似于对自己命运的理解一般。它或许便是我生命的一个中转甚至支点。
我在这广场附近的一个单位里上班,大约是三年前的事。那段经历到后来变得无比重要,迄今我都一次次地借故跑到那里去,看看曾经熟识的人。许多同事早已离开了,现在仍旧在职的员工,我多半不识。然而,在那里,我曾经做过的许多事情一直延续到今日;我生命中最为贫病的一段时光,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当然,我生命中最大的转折,正是从那种懵懂的生活中生发。
我总是在事后多年,才可以想象到当初的场景。似乎是,连续数月的欠薪,使所有人的信心丢失了;对于我,这种想象甚至形成了生活中的一个顶点,我无可选择,且不加回避,其间种种曲折,如今想来,已经宛若浮云。我的同事们,后来都风流云散了,多数都不知所踪,极少的几个,居然成了今天的新同事。
但这些陈年旧事,同这条巷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我们的思想有一个巨大的回流,那盘旋的部分或许会与此相对应。可事实上,除非我们什么都不去做,否则任何可能性都难以被排除。因为即使从那段生活开始算起,至今也已经形成了多少空白,何况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只这三年呢。此前此后,都有多少光阴是这种生活的发端或者延伸的部分。
就是我来到这里,似乎都有许多轨迹难寻。所以,对于一个人生命的记述,我觉得完全不可凭信。我大多时日其实连回味的空闲都不曾有,好在每天上下班,能够看到这城市里的人群。在许多类同的小巷里穿行时,我庆幸自己与人间这最本源的生活没有丝毫疏离。
许多感觉,都是在观察他人的生活中得以强化的。我每天经过的巷子口上,有卖水果、鸡蛋、粮油、蔬菜的,还有卖烙饼、面皮、灌肠、凉粉的,有理发铺子和小超市,甚至还有一个性保健商店。黄昏的时候,我路过的好几个铺子前,都摆着一张桌子,四五个人围坐着在打扑克牌。这个场景丝毫都不稀奇,然而我有时想起,觉得生活里如此平缓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不由得总会对那牌桌多打量几眼。
这巷子是条曲巷,从巷子口到我所居住的小区,大概有三四百米,回来时一路下坡,我常常会碰到一些年龄大约在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骑车带着他们的女友疾驰而过,因为路况本不太好,为防止碰撞,我会放慢速度,如此,就有机会看看行将过去的那一对对男女。
他们,有的看起来尚且像在高中或者大学里就读,男的个子高大,大腿尤其粗壮,女的通常戴眼镜,表情单纯朴素,肩背上挎书包,双手伸向男子的腰部,这样一种亲昵的动作做出来相当自然;有时,会有大车从对面过来,这就免不了会有一个急速的错车,男子把车把一拐,动作优美自然,女的就势向前依偎,神态轻松自如。我有好几次看到这一幕,就单腿支地停下车来,一直扭头看他们远去。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一些异乡来的打工青年在这里穿行。我熟悉他们,如同熟悉我的兄弟姐妹。我也一直相信自己身上有着与他们太多的相似性。我们在互相对望的瞬间可以证明这一点。我看得到他们过分亲昵的表情中隐藏不住的兴奋。
那男子多半瘦弱,这一点不像城里人,因为有许多打工生活的烙印。而且许多人的神情酷肖。他们虽然不再是拘谨的,但总不至于张扬,而且给人的感觉也不流畅,大抵是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里的缘故。女的则多数健壮,说不上来什么缘故。她们的身上穿着在饭店里或者超市里的工作服,手里抓着手机或者端着一个饭缸。有许多回,我都希望自己能停顿下来,同他们聊几句乡下的事情。
但是,我总是没有做到,而且一旦产生这样的念头,就觉得自己矫情。他们歪歪扭扭地越过去了,那身形同我的弟弟妹妹是相似的。有多少时候,我想起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的种种,大约也会受到弟弟妹妹的同情呢。他们居住在家乡,也各自成家立业了。对于他们的生活,我从来未曾帮得上多少。
然而对于自己的生活,我总还是有一些自足的地方。就是这纷纷扰扰的街头,我也是喜欢的。这不像是在更遥远的地方,我的心始终是悬着的,在这里,我安定地骑着车子,晃晃悠悠地出去买菜、购书,有闲暇的时候,还会到大超市里逛一逛。儿子回来的时候,每逢下午六七点钟光景,我会和妻子抱着他下楼,我相信儿子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甚于我。我知道这里的人与事情,都会在他的生命中扎根。
尽管他还小呢,离懂事的年龄尚且有好几年。五、六个月大的儿子,当我们抱他下来的时候,他做出四处逡巡的样子。他壮实的小身体在我的怀抱中动来动去,他太好奇了,即使我与他搭腔,他都不会像在家中那样对我的话语立刻做出反应。他的注意力在别处呢。
在这条巷子里,我慢慢地留下生活的痕迹。我往返的次数累计起来,会渐渐地超越自己的部分想象。我生活中的每一次动荡,都已经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痕迹。然而我始终认为,这并不是一些必须的经历,如同我们上一辈人所遭遇的磨难一般,我们在属于各自的时代里走了许多不得已的弯路。如果有可能,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直至今天,我们都有一些自视非轻的成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或者感觉到的那样,在我们的父辈中,有许多未完成的人生,然而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情形再出现在自己的身上。但这些问题像一种重荷,已经越来越重地压迫着我们的肩头。
在这条巷子里,有着比我以往所观察到的更加亲切的人生。4月下旬的一天,当我第一次从这里走过的时候,路边的树木已经一片葱茏,可是,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我没有特别留意到它们是怎么一点点地融入到这个夏季的。我只是注意到每天中午,总会有几辆平板车停靠在楼底的树阴下,袒胸露背的男子简单地吃过午饭后,就在收来的一堆书报废纸中小憩。有一天,我居然在他们的交谈中听到了一缕乡音。
我或许在这里还将看到新的风景。但是,目前与我近在咫尺的就是这些人了。他们每天上午八点左右开始从楼下的小巷里走过,直到黄昏时候隐匿无踪。周而复始。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的他们的踪迹已经被我铭记,但除了可以辨别乡音的几位,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自哪里,我并不清楚。
我清楚的只是,日升日落,昼出夜伏,他们已经与这里的一切融合为一体。
火车站
火车站附近原有一些居住了多年的老市民们,因为车站广场屡屡扩建的缘故搬迁出去,此处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我指的是午夜时分,这里寥落的情境让人觉得可怖,似乎有置身蛮荒时空中的嫌疑。但是这样的时分又极其少,所以这空洞只是一个巨大的幻觉罢了。可假如我们是从半空里向下俯视,除了多数时候熙熙攘攘的人头,我们还看到了什么?栏杆、电线、拥挤的车辆和破碎的心情?这都是真实的,因为我曾经多次看到了惆怅的远行人在车站前方的空间里抽泣。在太原、南昌、广州、宜春,甚至匆匆而过的阜阳,这种情形都见证了火车站的特异功能。它输送着一种古怪的情绪离开此地,但哪里才是这些远行客的终点站?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弄明白。有一天,我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个狂妄的想法罢了。因为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我自己就曾经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决定过自己的去向。这是在最为炎热的八月。杂乱的广州车站。表姐夫让我立刻确定去深圳,或者就待在此地(广州)。毋庸置疑,对于此地的陌生感让我产生了一种畏怯心理,于是我宁愿做一个抽签式的茫然选择。作为异地的深圳是一个遥远的年轻的城市,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它的距离感可以对我的心理形成一个缓冲。是在旅途中我才建立起对南方的适应性,这是六年前,南方酷热的气候把我带向了一段崭新的旅途。
火车站开敞的空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诱因。我们是在这种诱因里抵达一个新城市的。无论在多少年后,这个城市变得有多旧,那最初的部分都足以支撑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全部记忆。到了后来,我们逐步对这个新的目的地熟悉起来了,往事历历,才产生了许多新的疑问。譬如对于广场的探索就时时萦绕在脑海里。这里聚集的人群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根深蒂固的居住者都到哪里去了?当然我们后来只是在发问罢了,求解的欲望泯灭在一次次无果的探访中。有一年的秋季,我站在太原火车站南部的一座校园里,稍一仰头就可以看到火车站那巨大的烟囱。再登到高处,还能够看到列车的轨道,它们或平行或交叉地矗立在我的视野中,是被“观察”到的。似乎有些错乱。但平静而固执。我曾经以为自己的骄傲也来源于一次次从此地始发的远行。在那时我同这座城市的关系非常疏离,不,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可言。我从这里出发的时候天降小雨,好几次都是,仿佛是为了安慰我低沉的情绪似的。在候车大厅里看不到前程。更加明确地说,我不知道我远行的意义何在。如果说对于家乡的厌倦也可以算做解释的话,那在几年后我甚至准备辗转回乡的想法就有些矛盾百出了。我在否定之否定中看到了我的出路。火车站记载了我的心理变迁。
但每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这是2007年,我已经在太原蜗居多年后的直接感受。也许是在此地居留过久,我觉得自己就要成为一个老居民了。我可以走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小巷子里都不迷路,这简直难以设想。十年前,我连在老家县城转一阵子都会找不到出口,因此我一直觉得那个小城的格局酷似迷宫。当然,我在那里居住了四年,直到像个老熟客似的可以自在地出没于任何一家高档消费场所。但是,我把这种心理移植到了省城后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种自足的、封闭式的感觉消失了很久,我以为它们永不会再来了。因为我在这里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征服它。是的,那时我确实想到了“征服”这个词。的确是这个巨大而妄想的词语救了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才没有被混沌而喧哗的城市浪潮淹没掉。但就在这种浪潮中,我同时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像一个内心的暴徒似的,我以一种克制的力量维护了自己在日常交际中的尊严。可是,这同整个城市有什么关系呢?它依旧那么庞大,尽管我们时时都以嘲讽它为能事,可作为被淹没的对象的,只会是我们。而这里同南部城市有什么不同?这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发展史的辨证,被一再地提出来。
是火车站以它的发散式思维来告诉我们。
那些风尘仆仆的远行人带来南来北往的消息。这消息在不同的车站之间流传,像被携带的旅行包似的。作为聆听者,我们从他们的方言中获得一种新奇的快感。如果是简短的等候,这种快感甚至可以延续整个过程。一直等到上车,在列车轰隆轰隆开启的刹那,我们都可以沉浸在这种难得的情绪里。对于那些远方的城市,我们所产生的念想非常明显。但这种念想显然是被束缚和压制的,因为过多的情绪流露会带来旁观者的注目,我们的快乐有可能被这注目消解掉。那么,就在我们悄悄地独享这一切的同时,见多识广的人们谈论他们刚刚经过甚至逗留的这个城市。作为“老居民”,我们细心地琢磨着这些谈论中的各种意味。赞赏的、鄙夷的,都与我们密切相关,又似乎完全没有关系。火车站已经不是单独的一地,它连接起我们所要抵达的一个个高傲之地。如果是目的清晰的旅行,我们的心情也会与将要抵达的城市达成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已经把曾经的居留地排除在外了。似乎是,我们在将要抵达的某地所展开的哪怕是一小段生活才是最真实的,而我们行将离开的城市,晨钟幕鼓,已成虚幻。这种心理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流浪者的身份感叹,因为“老居民”的确定性,不属于朝秦暮楚的我们。
当然,屡屡行经异地升华了我们的生活,火车站开启了美好生活之一端。无限的憧憬是火车站赐予我们的。站在车站广场那无限开阔的空间里去观望远方,尽管我们的视野尚且不及,可心灵的触角已经先行抵达了。因此我看到了那一对携带着臃肿的行李的夫妻,他们的脸上带着笑,他们怀抱中的孩子离我很近,他以自己未经世事的眼睛看着我。看了很久,他忽然说话了:“叔叔,你要去哪里?”我抚摩着他吹弹得破的脸部肌肤,微微笑了笑,并没有直接对他的疑问做出回答。他的提问没有解除,于是继续:“叔叔,你要去哪里?我在问你话呢?”这次我有点难以招架了。继续微笑着,但仍然不准备回答。最后是他的母亲出来打圆场:“叔叔要出去赚钱啊。和爸爸妈妈一样。”他带着天真的深情疑惑地追问:“叔叔,你是要出去赚钱吗?”这真是一个简单而准确的回答,于是我说“是”。他还在追问:“叔叔,你赚钱做什么?”这真是一个难缠的孩子,幸亏是孩子。他的母亲带着歉意说:“叔叔忙得很。叔叔要赚钱养家。宝宝不要缠叔叔。”我带着会心的笑转身,想,这孩子像谁呢?那一对夫妻带着大包小包离开了,他们的孩子却一直将目光向后转,我与他又对视了一下,他忽然向我招手:“叔叔再见。”我也向他招手。然后,他们走远了。
事实上,我是来送人的。事后,我继续逗留的这个城市似乎正在扩张。许多路面都被拓宽了,一些民居被拆毁。这在十多年前就于别处演绎的一幕在这个城市里被繁殖了。道路的畅通把世界变成无限。现在从火车站出发,无论到达何处,都畅通无阻。我们从异地归来,身上的风尘劳顿被这个新空间吸收了。这个城市新近树立的巨幅广告牌正在把我们的视觉带往一个记忆的空间里去。然而那记忆的空间如此久远,简直成了上世纪的旧梦。我曾经逗留的南部城市里有无数的巨幅广告牌,艺术墙和主题公园遍地皆是。对于南部的热爱正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然而我不久后就离开。在深圳火车站前的立交桥上,我走过了几十个来回。那里如梭的车辆如同时光那失真的面孔。因为一种深切的异地感把我真正地触疼了。我没有继续漂泊下去。数年之后,在这个北方车站前的时钟下面,我在想那时候,幸亏再没有漂泊下去。我现在悠闲的步履与那时不同,看着这个城市街头时的目光也与那时候不同。作为“老居民”的荣耀感是在一个个瞬间里得以恢复的,然而这与我一向标榜的流浪者身份不符。是的,我的户籍还不在这里。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但我在这里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似乎是为了确证这一切,我还需要通过数年的奋斗来巩固自己在现实方面的成就。2007年秋季的某一天,我站在车站广场前的人流里,这里每一个陌生的面孔都匆匆地过去了。沉积的往事于是被唤醒。六年前,我也曾经站在这里,那一次我只带了五本书,装在一个简单的行李包中。我是懒散的,似乎准备随时回来。大概因为我的包不够沉重,所以看起来,我并不像一个真正的远行人。一路上都有人要我“让开”。让开,让开,他们毫不客气地喊道。我被挤在一边。快速地落到了人群的后面。我几乎真的就要返回了。无数次回头。我看着自己的身后。我已经过了剪票口。开往阜阳的列车再有二十分钟就要到站。外面的世界突然向我开放。然后我在回头。恋恋难舍。无限犹豫。几天后,我对弟弟说,没想到我跟着你,到了这么一个地方。我的悔意依然浓厚。然而我毕竟从此出来了,从此后,我其实无法回头。每一次经过一个新车站,我都要仔细地观察那站牌。他们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两个指向。这两个相背而行的指向导致了我们的人生。它们循环往复,永无尽时。
作者简介:
闫文盛,男,1978年生,曾在《散文》、《山花》、《青年文学》、《天津文学》、《红豆》、《百花洲》、《文学界》、《红岩》、《山西文学》、《延安文学》、《诗刊》、《布老虎散文》、《星星》、《美文》、《诗歌月刊》等刊物发表作品100万字。有小说连续四年入选《中国青春文学年选》,散文入选《2006年中国散文精选》、《新散文百人百篇》等数十个选本。著有《花间词话》等长篇小说及散文集《光线》、《失踪者的旅行》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