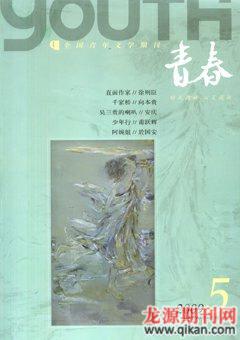阿婉姐
於国安
部队开进来时,她18岁,我才8岁,或者更年轻。这么说吧,我对7岁以前的事没几样是记住的,我甚至不晓得我是哪地方人。南村人都笑我,每当这她会过来帮我,替我挡架,我喜欢她。她叫阿婉,是我娘娘家的小女儿,我叫她阿婉姐。人多时我不叫,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叫。我叫,阿婉姐。她笑,面孔红红的笑,她的笑像朵花。不,比花还要好看。她笑的时候,我也笑。她会说,笑什么呢?傻傻的,难看死了。她越这样说,我越笑,最后我们都笑得岔气了。
娘娘家,就在我家左斜角,拢共起来只有十几步远。但这十几步远,并不那么好走。小辰光,娘娘总是拒绝我们的到来,她爱干净。庭院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扫帚啊,锄头什么的都堆得斯斯整整。据母亲说,她一天到晚,桌子、凳子要擦三道。我问母亲,那你怎么不擦三道。母亲叹口气道: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福气是修来的,我们是做坯,下辈子吧。母亲的话里有着宿命的哀怨。我不懂,我总是盼望着,夜头快些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去娘娘家了。我去娘娘家,我就可以见到阿婉姐了。见到阿婉姐,我就可以见到她的笑了,对了,她的笑里有香气。可是,阿姆总是不让我去,每次都要骂我,是那种没心没肺的骂,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骂我。
部队开进这个村子里,主要是打个海塘。那时,修海塘修得热血沸腾,家里有劳动力的都出工,往往是一家好几口人都泡在海塘上。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做海塘,中午饭可以白吃,大队里有补贴。下午午歇时还有包子发,白白胖胖的包子,我在邻居家结婚、上梁等好日子里吃到过。因此,对小孩来说,做海塘是欢喜的,好像是又过了一个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人多,大人也管不住小孩,小孩就有更多的自由和放松。对小孩来说,没有比没有约束的窜来窜去更有吸引力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搞不清爽为什么要做这个海塘?抗台?养殖?……
我要说的阿婉姐,其实是从一个夏天开始的。一个夏天的午后,一个小当兵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
——老乡,要粥吗?起先谁也听不懂。我奶奶慌里慌张地爬出来问什么事。我穿着短裤也奔出来。见一个戴着解放军帽子的年轻后生,站在门口。奶奶有些慌张,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
——老乡,是粥,白米粥,可以吃的。我们部队里吃不完,倒了可惜的。我们领导叫我来问一问。说着他移开盖子。我头一张,真的,是白米粥。奶奶推了推我的肩胛,意思说不要乱动。奶奶说,我们家有饭,吃你们的东西罪过。我连忙插了一句:我们家是番干饭,没有白米粥。奶奶撸了一下头:小鬼头,有吃就行了,还想吃白米饭。
那个小兵看出我的意思来,说,奶奶,没有关系的,我们是主动送的,没有关系的。经他一说,奶奶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她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可真是摸不透了,不知是接手好,还是不接手好。我叫了声:
——奶奶……
奶奶看了看我,还是有些举棋不定。我探着身子,头使劲地张着小当兵的桶沿,喉节骨碌碌地像青蛙似的乱转。我在心里说,奶奶快答应啊,奶奶你还磨磳什么呢?
——老乡,莫关系的,反正你们不要,我们也要倒掉,倒了挺可惜的――
——哇,是什么东西啊,介客气。阿婉姐。我叫了一声。奶奶见有人来了,连忙把事情一五一十倒了出去。倒干净了,奶奶掸了掸布衫,说,这个小鬼头,馋痨煞了,好像八辈子没吃过似的。
——是没有吃过,过年才吃一次。我嘟囔了一句。
——奶奶,我看也没有关系,就算是我和小弟两个人要吃吧。她一边说一边对我眨了眨眼。我也冲她笑笑。不知怎么回事,在我心里,我觉得阿婉姐比自己所有亲人还贴心。
实事求是说,那顿粥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好的饭食,直到现在还忘不了。放了白糖的白米粥,蜜甜蜜甜。我想,那粥,对阿婉姐来说也是蜜甜蜜甜的。
我一直认为人与人的相知相识是有缘分的。否则你怎么也不能解释我与阿婉姐,对了还有阿婉姐与张园。
张园的名字是我后来知晓的,以前人们都唤他豆腐郎,真名字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张园是个湖南兵,大约也是十八九岁当兵来了。在南村的时候,大约靠廿岁了吧。我记得那个下午,他嘴唇上长出了绒绒的细毛,额上沁出了一层层汗珠。
阿婉姐说,你放下担子吧,这么站着,不累吗?
小当兵嘿嘿一笑,顺从地蹲了下来。那个下午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个的下午,我们三个人靠在院子的荫凉地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从屋里拿来三只碗,盛上粥,张园说,我吃过了,你们吃吧。阿婉姐说,你不吃,我们倒真像讨你吃似的。小弟,我们可不是讨吃是吧,我们是做好事,对不对?说着她又对我努努了嘴,眉梢向上抬了抬。我含糊道:是的,是的。其实我满口塞住了,他们根本听不出我说的话。看我这副样子,阿婉姐笑了出来,她一笑,张园也笑了,说,慢慢吃,当心噎住。我鼓着腮停了下来,大约我这幅样子他们觉得更有意思吧,给他们一逗,我也忍不住了,一口就喷到张园身上。
很多年后,当我在小菜场打豆腐遇见他时,我向他询问了这事,我说,张园哥,你还记得吗?他摇了摇头。我说你还记得那个下午吗?他还是摇了摇头。我接着追问:那你总该记得阿婉姐吧。
他停了停,又缓慢地摇了摇头。我重复了一句:南头山的阿婉姐啊。他说,记得不记得又有什么用呢?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我说三十年了。他说老了。我说现在南头山都变成废墟了。他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他说的话我听不懂。
其实,那个下午发生的事,对我来说也似懂非懂,但最起码来说,那个下午对我来说打开了一扇窗户,我知道山外面还有山,海外面还有城,在这个世界上,比南头山大的地方有很多。我问:叔叔,这么远的路,你怎么来的。他说坐火车啊。我问:火车是怎么样呢?张园说,很长很长,他比划着。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问:阿婉姐我们也去坐火车好吗?阿婉姐笑。那不我也成了湖南人了。我说湖南人有什么不好,可以坐火车啊。轰隆隆,轰隆隆,多威风啊。我说,阿婉姐,我们都变成湖南人好不好。
这以后,一有空,阿婉姐总带我去部队营房玩,反正每次去的时候,张园总在,他带我们白相,部队的角角落落我们都去过。那个时候,部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挺好的。晚上经常放电影,每次我总是第一个知道消息,比方说,放少林寺了,放高山下的花环了,还记得放过一部外国片,叫什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什么的。我和阿婉姐去不用抢位置,也不用背凳子,正厅永远是我们的。叫我烦的是,阿婉姐总和张园有讲不完的话,两个人还咯咯地笑,放完了,他们不好好走,专门从后背山上翻过去,有时候我困了,张园就驮着我。我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晃一荡好像在船上。
阿婉姐结婚时,我已经上小学三四年级了,人闹闹哄哄地,娘娘好像很高兴,她老早就和我娘约好了,给她帮忙。我呢,顺便也可以吃喜酒了。可我搞不清楚地是阿婉姐总是哭。我问阿姆,阿婉姐怎么了。阿妈说,新嫁娘都是这样的,哭是代表对娘家的依恋,不哭才不好呢。我说,介复杂,高兴应该要笑啊,哭什么呢,应该笑才对啊。阿妈说,小孩子懂什么,老规矩不能破的。我说,将来我结婚时,一定要笑。旁边的邻舍都笑了:你又不是女的,再说到那时节也不由得你了。有人接茬道:那也不一定,时代变了,他们这一代都是新派了,我们也做古了,管不着他们了。你看出在电视上男男女女一见面就相嘴,搂抱。还赤卵赤膊跳舞呢?
按理说,像我这样外人是不许进阿婉的闺房的,况且娘娘平时也不许我进他们家的卧室。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去找阿婉姐借小人书,喊了几声,没有应答。我踅了出来,想想还不死心,兴许是她没有听见。娘娘不在,我胆子大了不少。于是我跨进门槛,从橱房里闪进去,想偷窥阿婉姐的闺房。步子还没迈进堂屋,里面就有声音传来,像是打架摔跤的。我以为是遇到小偷了,忙大喊,谁。声音随即消停。过会,阿婉姐声音出来:谁啊。我说我啊。隐约中阿婉姐低声说,没事,是小弟。她挑开窗帘出来,面孔红红的。我说,原来你在啊。我刚才这么喊都没有应,我以为是贼骨头进门了呢。我头向前伸想看看她的卧室,阿婉姐一把把我拖了出去,拽得我手臂生疼。她沉下脸说,小男孩不许看。我央求道:阿婉姐,就让我看一眼。我还想进去。阿婉姐有些愠怒了:不许就是不许,再这样闹,以后你别来我家了。打我认识阿婉姐开始,我从来没见过她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有些委屈,瘪了瘪嘴,悻悻地走了。可这次阿婉姐不把我当成外人,她特意给我准备了一包食货,还叫我到她的房间里去拿。娘娘说,你阿婉姐对你最好了,看来你们两个人还是有缘分啊。我到了阿婉姐的房间,没有说,眼泪跑出来了,我轻轻地叫了声:阿婉姐。本来想说,阿婉姐你真好看,但我没有说。阿婉姐说,要期末考了吗?我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