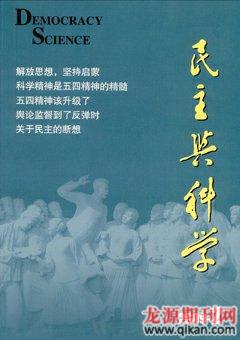多元化的五四思潮
罗银胜
“五四”、五四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课题。一提起“五四”,人们就会想到“民主”、“科学”、“民族主义”、“反传统主义”等各种名词。的确,它们构成了“五四”的基本形象。因为“五四”是一个思想活跃、主义丛生的时代,围绕人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重建问题,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近代启蒙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相继涌入国门,被启蒙先驱们作为救亡图存的文化资源进行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标举“内圣外王”“格物致知”的儒家传统,在西学东渐和社会结构急速变动的双重夹击下,虽然发生了严重的信仰和道德危机,但其中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却顽强地延续着,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在西方思潮冲击下,何以会保持鲜明的主体风格和勇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其实,五四运动是一场多层多面的复杂的运动,它具有多元复杂的思想面向,“五四”思潮和“五四”思想的全部内容绝非几个名词所能涵盖的。
“五四”精神,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众多的仁人志士投身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建设的双重变奏之中,激情、亢奋、呐喊、困惑、质疑、彷徨、纷争、搏斗、批驳、解说……扑朔迷离,难以尽述。
对于“五四”精神,林毓生有一大体的评价,他说这是由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所促成。这种精神承接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这种精神发展到最高的境界便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因为有了使命感,“所以我们有所归属”。“这种入世的使命感是令人骄傲的五四精神”,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继承“五四”精神就是发扬这种精神。
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年代,这个时代的变局不仅意味着中国政治社会建制处于由大一统王朝帝国、宗法家族制度向现代性政治社会制度转变,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处于由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这两种转变之中由于存在着“质”的变化,进而引发了两种危机:前一种转变所显现出的便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后一种便是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近代中国,正是在这两大危机的互相激荡、冲击下蹒跚前行的。“五四”所处的历史氛围,如张灏先生所云,是一个“转型时代”,即“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张灏:《思想与时代》)“五四”则是这个转型时代关键时期,它的思想变化处于高潮:1915年《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刊,四年以后又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中国历史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开始漫卷全国,各种外来的、本土思想文化、思潮学说互相碰撞、交融。在这个“转型时代”,即从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的时代。这意味着,这一“转型时代”是20世纪与已往历史联结和沟通的桥梁,正是从这里出发,形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命题。
五四运动的概念是庞杂的,对此有必要加以厘清。“五四”研究专家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而“这一切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促发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有严密组织的运动,而是许多通常具有不同思想的活动的结合,尽管这个运动并非没有其主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因而,“五四”是多种层面、色彩斑斓的运动,自身有其复杂多变性。唯有把握其复杂性,才能多视角地认识“五四”思潮与“五四”精神的实质。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殷海光:《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是17世纪以后西方各种思想的大杂烩,他们接受的新思想中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其中不仅有洛克、斯密、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而且有尼采、马克思、帕格森、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启蒙和后启蒙思想家的学说。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想,构成了“五四”启蒙运动的多元思想资源。
不仅如此,甚至这些具体思想也有不同版本。如个人主义,亦有英美式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尼采式的贵族个人主义、易卜生主义、泡尔生式精神个人主义、中国式个人主义等多种思想类型。另外,对于同一种主义或价值理想,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比如“民主”和“科学”,《新青年》同人对他们的理解并不一致:陈独秀把近世文明归结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而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来自法兰西革命;李大钊则认为近世文明来源于俄罗斯革命;胡适则崇拜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张灏曾把“五四”思想的多元复杂的性状,用“两歧性”来名之。张灏先生认为,在“五四”启蒙思想内部,具有深刻的两歧性,他指出,“五四”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急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又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问题的复杂性。“五四”思想中这些对立发展的趋势,就是所谓的两歧性。张灏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
“五四”的理性主义是最显而易见的,因为“五四”自始至终强调发扬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目的。在“五四”的思想世界里,浪漫主义的比重,不下于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主要包括激情、热爱、无限奋进的精神和乐观精神,这些使“五四”变成了一个乌托邦思想弥漫的时代。
(2)怀疑精神与新宗教。
“五四”知识分子在提倡理性主义的同时,提倡怀疑精神,他们认为在现代世界,宗教迷信与玄学幻想,都是偶像崇拜,应该清除。但同时由于“五四”时期有着政治秩序和取向秩序的双重危机,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切地追求新的价值观与宇宙观,即新的信仰。“五四”对新信仰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他们人道主义的宗教情怀上。因此,“五四”不仅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也是一个信仰的时代。
(3)个人主义与全体意识。
大部分“五四”知识分子都信奉个人主义,追求个人解放,这成为“五四”宣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最突出的特征。与个人主义相伴而来的是与之相矛盾的群体意识,“五四”早期几位领袖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群体意识。在整个“五四”时代,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的对立之势始终存在,构成“五四”思潮的重要一面。
(4)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甲午之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大规模的散布,至“五四”而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但另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却刻意超越民族意识而宣扬世界主义,追求大同主义,“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正表明了世界主义的这一趋势。(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
“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不仅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它的相互矛盾在其它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
(1)“五四”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强调进化论,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们也正是用这一武器去攻击旧信仰、旧传统的。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接受这一理论的同时,也提倡克鲁泡特金、新村的互助论,并将这两个矛盾的学说很好地结合,他们认为生命是由竞争维持的,而互助则是在竞争中培养人性的最好的方式。
(2)人的分裂。汪晖先生认为“五四”知识分子在揭示旧社会的罪恶时表达了一种乐观理想,但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抗却导致了其对自身的悲剧性理解即人的分裂,这也是十分矛盾的。因此他有这样的说法:“与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的乐观精神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从事‘改造国民性的事业时充满了一种深沉的悲剧感。就鲁迅而言,他摒弃了乐观的希望,又拒绝承认绝望,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从而以‘绝望的反抗作为他的人生信念。”
(3)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思潮的一部分,但它与“五四”早期的思潮有许多相冲突的地方。它的传播动摇了启蒙主义的基本信念,即民主;它的经济决定论动摇了启蒙主义的文化决定论;它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动摇了启蒙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李大钊等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想结合,但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4)无政府主义与启蒙使命的冲突。无政府主义几乎影响过整整一代启蒙思想家,无政府主义在反对专制和反对封建伦理的斗争中,与启蒙主义有着共同的对象,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常常把老子及其小国寡民的生活奉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和社会理想,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和中国墨家的“兼爱”思想相提并论,把“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孔子的“大同思想”混为一谈。无政府主义一面反对封建专制,一面对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心存恐惧,他们的那种绝对自由的思想和虚无主义态度与启蒙主义的理性是相对立的。(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五四”思潮虽然错综复杂,但无外乎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开药方”、求出路。明乎此,王元化先生在《谈掌故书》里所表露的:“我也一样觉得自己思想光亮太少。我实在觉得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论聪明,论才智决不后人。百余年来,仁人志士为此家国,舍身忘己,忍大苦难,仍无法力挽狂澜,促其新生。瞻望未来,茫茫不见光在何处,每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王元化:清园夜读》)这真是一语中的,发人深思。因此,倡导对“五四”进行反思的王元化先生质之于词:“‘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以免真正的“五四”精神被形形色色的“五四”思潮所隐没。
在这场轰轰烈的运动中,将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各种思想纷纷登场亮相,向社会展露风姿。原来表现为“新”与“旧”的知识分子两大阵营出现了空前的分化,每一个人都拥抱着自己的理想,幻想着中国的明天。很难将这简单归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肇始”或“传统的断裂”,“五四”给予了各种各样的人以截然不同的思想滋养,给每种言论以互不干涉的空间。那是政治史上的混乱年头,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又是最坏的年代”。正是在这种“众声喧哗”中,“五四”的意义才得以凸现。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