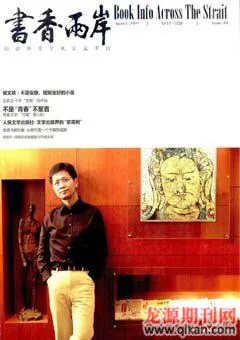四余读书记
编辑平台:
本刊之“副刊”栏目内容由台湾地区《文讯》杂志提供,并同步刊行。
散文的“四有”
我多次被人问起怎样写出很好的散文,这些年我总是引用张春荣教授的话来回答:散文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趣,言之有味”。这是他在《修辞新思维》中指出的方向。大概是因为引用的次数很多,有人当做了我的主张,趁此机会声明:我每次引用都注明了出处。

言之有物,文章要有主题内容,言之有序,文章要有组织结构。这两条容易明白。“言之有趣,言之有味”,倒是有些费解,“趣味”连成一词,我们用熟了,用惯了,认为这是一件事物。“四有”之说一出,提醒我们“趣味”也和行动、明白、清洁一样,两件事物合成一个大范围,同中有异。
“趣”和“味”有什么分别呢,依我体会,趣在当时,味在事后。妙趣横生未必回味无穷,越想越有味的故事讲出来未必有哄堂的效应,研究喜剧的人介绍过来一个名词叫“笑点”,这个“点”就是刀口上,节骨眼,快一秒慢一秒,增一分减一分,都不能发生喜剧效果,“趣”就是这样一个“点”。
“味”是一条“线”,仅仅有趣也能流传众口,它有折旧率,能产生免疫力,所以有些笑话我们不想再听第二次,“味”则是一种秘密的得意,深藏心中,反复玩索,历久弥新。所以我为“四有”作注:“言之无趣,行之不广,言之无味,行之不久”。
趣和味在四有之中占了两条,可见张教授情有独钟,力有专注,见有独到,也可见要想做到,难度很高。以我体会,有物和有序偏重功力,有趣和有味恐怕属于风格神韵的范围,偏重自然,作者他得先是一个有趣有味的人,而且他得能够分别什么是高级趣味,什么是恶趣、劣趣、肉麻当有趣,慎勿因追逐趣味坠落了文格。
七十岁的少年
《春天窗前七十岁的少年》,隐地兄最近出版的散文集,封面书名旁边有他一张少年时期的小照片,与“七十”两个字并列。乍见之吃了一惊:怎么你也七十岁了?
打开书本,我的心马上沉静下来。
七十岁的隐地,好奇心还没丧失,求知欲还没满足,美好的想象还没模糊,单纯的善意还没污染,感觉依然丰富而锐敏。他把这一段人生安放在春天的窗前,不是十七岁的春天,是七十岁的春天,也不仅仅是七十岁,乃是“七十岁和十七岁的合金”。我也有过十七岁,我也有过七十岁,可是我的七十岁中没有十七岁,而我的七十岁在十七岁时就出现了,我仔细读了隐地这本书,吸收其中的经验和境界,我需要补课。
这位“七十岁的少年”,用追念的语气提到多位作家,我读来最是亲切有味,也唤起我无量的联想。他慨叹刘枋大姐去世,新闻媒体没有报导,文友也仅有丘秀芷女士一篇悼念的文章。我想起小说家南宫搏生前交游广阔,1983年去世,我费了许多力气,只找到阮毅先生有篇文章吊唁他。某大亨去世,悼念文字有百篇之多,我一一拜读,达官贵人写的固无论矣,根本是秘书签办的公文,作家写的竟也都是陈腔滥调,虚应故事。而今人情淡薄,吊挽之词已非文人发抒真性至情的题材。
隐地兄写他两次参加街头的群众运动,一次有五十万人,还有一次人数更多。记得当时消息传来,我很担心,根据我的“大陆经验”,这样的场面凶险,可是连一双鞋子也没挤掉,我庆幸人民大众成熟了。当年我写下“游行示威是这一代的瘟疫,下一代的勋章”,幸而言中了,我珍惜隐地兄留下的文学纪录。
全书读完,试作七绝一首题于卷末:
画满春窗歌满弦,
文心落纸有新篇。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精勤比少年。
附记:古人“三余读书”:“夜者昼之余,雨者晴之余,冬者岁之余”,我加上一条:“老者生之余”,合为四余。
王鼎钧
笔名方以直,1925年生。曾任《中国时报》主笔、人间副刊主编。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论述、诗、小说及广播剧本等,擅用小故事烘托主题,以生活化语言与读者心会神通。著有散文《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