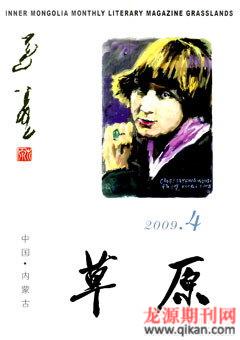假如它们不是书
郭雨桥
整整忙活了一上午。把散落在各处的书归整到书架上,看着屋子里顿时整洁了许多,书们都抛头露脸,一排排整齐地站在书架上。我心里舒坦,又想起许多事,想吐一段文字。
都说文人清高,那是自我感觉。人家房地产开发商,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看现在的现房或期房,都是客厅占的面积最大,卧室占的面积最小。根本不考虑我们这些文人的实际需要。从商从政的人客人多,客厅当然大点好,有些高档书在四面摆摆,不过附庸风雅,而根本不看。我们这些人,买了书是用的,最好能在身边,甚至坐在椅子上就能探取。所以跟人越近越好,使用起来越方便越好。我这个家132平方米,按说也不小,可是客厅就占了40多平方米,平时大部分时间闲着,而利用率最高的(每天至少在十六小时以上)的书房,却是面积最小的。
这就注定我一开始入住的时候,就要人来迁就居室。我把一面墙的书架,全部安排在阴面那个卧室,放平时不用的闲书,数量上也是最多的。当然我也可以住在这里,因为这里面积稍大一些。可我是个爱在野外疯跑的人。在家里也喜欢阳光,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书房。其实那就是一间小卧室。说书房是自个儿哄着自个儿高兴。我把它变成书房。委实进行过一番别出心裁的改造:整体装修窗户的时候,把两侧改成了有高没宽的书架,共有四层,最上面一层取书需踩凳子。在包暖气的时候,也在两边隔出两个柜门子,于是也成了书架。还有衣服立柜。也三分天下有其一,让我给装上隔板作了书架。还有床头柜,抽屉里面和上面放药品。下面也做了我的书架。这样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它的主人已经把它改造成了一个不是书房胜似书房的地方。把我所有有用的所谓“忙书”,都放在这个书房里。但所谓忙书和闲书。也是相对而言的。当时觉得它是闲书,过后要写一本什么书,忽然觉得闲书里面有许多有用资料,于是就把一面墙里的书倒腾到这里,渐渐地许多闲书都加入了忙书的行列。这几年走蒙古地。摄像摄影的材料和书籍。无意中又添加了不少。再加上这几年老来红,创作势头特别旺盛。书一本接一本写,内容各不相同,还要配不少照片。每次都得加一些新照片和新书,每次都有些闲书变成忙书。还有开会给的,别人送的,自己看见好买的,书房就显得憋屈起来。于是又出新招,扩大书架的领地。原来我坐的写字台跟窗户之间,留着一小段空隙,也是为了从暖气上那个柜门取书方便。但柜门里面有暖气管道,放不了几本书,取书时爬起跪下挺费劲。于是干脆把它废了,把写字台往门口挪了挪,空出一点地方做了一个书架。和写字台一般高。在床脚靠窗户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暖气旁的另一个柜门,也弃之不用,下面加了四根木头,上面铺块木板,高低与床脚平齐。这样又挪出来一块地方,下面塞破东西,上面放书。我记得毛泽东经常这样放书。咱也来一个领袖风范。这样一来,就暂时缓解了有书没处放的矛盾。
我这一辈子,什么也没有攒下,就攒下一大堆书。而且到现在还在不断增加。如果我这话是象征主义的说法,那就意味着它们就是知识。并且武装过后代,可以称得上是一笔遗产和财富。然而我那些书籍,除了文学就是蒙文。我有四个子女,也算成绩斐然,可是居然没有一个继承我的文学细胞。所以我的那些书籍,在下一代身上再没演绎出什么故事,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了一堆纯粹白纸黑字的印刷品。于别人可以说一无所用。但我自己却爱得不行。回想自己这辈子的经历。基本上就是用书串起来的,一开始看书,后来又写书,写书给别人看,买回书来看别人,一个怪圈转不完。至今见了好书迈不动步,尤其是合口味的好书。一定要据为己有,好好拜读。我有些朋友就不这样,人家退休以后,就把一切看淡了。节奏放慢了。谈到买书。人家就说:“要轻装上路了,沉甸甸地背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我现在就没有这种想法,见了好书,感觉还跟二十年前一样。只要自己感到需要就买。从来不想到我还能活多少年,对后辈儿女还有没有用。我总是由着性子去做,根本不考虑生前身后的许多事情。
但是好景不长。虽然居室做了一些改革,辟出两处放书的地方。开始还感觉良好。好像书都各得其所,需要时我也能各得其书。但只过了两年。书又放不下了。特别是2007年,我一口气完成了《成吉思汗祭祀全书》、《细说蒙古包》、《过节吃喝信天游》三部书,每一部书都有300多幅照片,还有自己的笔记和参考书,一摆就一大堆,书籍像洪水一样漫淹,侵占了桌上、窗台、床上,最后在地上还堆起了几个敖包。床头柜堵了,衣服立柜堵了,门也被堵了半个。别人进我家须见缝插针,查找一点东西得倒腾半天。有时候气得想哭。有时候恼得真想一脚把书踹倒,事到如今,再不想办法不行了。
于是我瞄准了写字台靠门一侧的塑料架。这个架子不大,买回来以后。上面只放一些打印纸、一部电话和杂物,利用率很低。且已经老化,有几股已经断裂。我就想把它老人家请出去。换一个新的。原来想到马上就要下乡,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干脆等过年回来一并倒腾吧。这几天稍微清闲了一点,看到地上堆的东西心烦。那天查一句唐诗。居然得摊倒一摞书,找完还得一本一本再摞起来。最后干脆下了决心,马上让这个破塑料架提前退休。
这就是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所干的事情。原来怕挡住墙上的电器开关。买了一个三层木头架子,今天早上一看不碍事,又去换回来个五层的。好家伙。就一些木头档档,居然花了800元,我过去打一对板箱才30元。好在样式还算可以,材料也可以。我索性来了个全面清理,把那些像汶川灾民一样打地铺的书籍弟兄,全都请到架上,把床脚上急用的书籍也搬过来一部分。家里顿时整齐干净多了,进家开门、找书换衣服都互不影响。境由人造,心里高兴,颇多感慨,就记下了这段经历。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到了刘文彩。这个四川大邑县的大地主,他是靠一块一块蚕食周围的土地。把自己的家业逐步扩大的。我个人的事业发展。按说也还顺利和迅速。书籍的数量在不断膨胀和强占空间,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写作的丰收和事业的兴旺。对于我来说,应该感到满足和欣慰。可是又一想,如果它们当初不是书,比如说是石头,或者最不起眼的尿壶,四十年前我要是这么积累和扩展,恐怕也成为一位富翁了。可它们是书,我贪婪了一辈子,积累了一辈子,甚至写作了一辈子,如果减去时代进步给我的改善。绝对财富几乎和二三十年前一样。所以我就想到,从投入和产出来说。最不划算的职业就是买书与写作。于是一些古人的诗句,比如“人生识字糊涂始”,“百无一用是书生”,“儒冠曾把身误”等等,一时间竟涌入脑海。
责任编辑任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