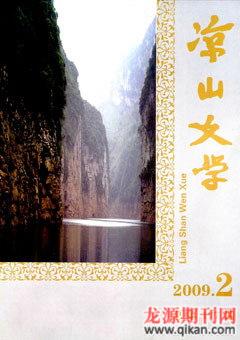安子的故事
华 洁
从这里望过去,原野很开阔很空旷。
密密丛丛的庄稼恣肆烂漫地铺排开去,径直伸向天边。绿色旺盛得扎眼,瞅一瞅就会让人头晕目眩。
安子在地里薅草,她身后是那间破败不堪的草房。
安子的儿子点点正在房前玩耍,乔大正用一只毛绒绒的虫子逗他。那虫子足足有两寸长,全身长满了猩红的绒毛,绒毛上泛着刺目的寒光,就象一个全副武装的斗士。
那虫子一步步朝点点的脚下爬去的时候,点点吓得嚎啕大哭起来。
“妈!妈!”点点捂着脸朝安子惊乍乍地喊着。
“哭啥呢?”安子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那声音跟早晨清新的空气混杂在一起,显得特别清爽。
“乔爸用虫子咬我。”点点带着哭腔说。
“他不是乔爸,他是乔叔。”
安子还是没有抬头,但声音比刚才更加高亢清亮。
“哦哦!别哭了,别哭了,点点是个勇敢的乖娃子,乔叔再也不吓你了。”乔大飞起一脚把地上的虫子踢得老远,然后把点点抱起来,用唱歌般的话语宽慰着他。
“乔赖,乔赖,你有那份闲心逗点点,还不如帮我干点活。”安子直起腰笑盈盈地说。
乔大把点点放下,端了一碗水,噔噔噔朝田里跑去。几缕尘土从他脚下飞腾起来,在他身后慢慢散开去。
“安子!你歇着吧!让我来干。”乔大直直地站在安子面前,把一碗水晃晃荡荡地递上去。
安子接过碗,把水喝了,抹抹汗又继续干她的活儿。
“乔赖!你用不着这样整天围着我转,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吧!”安子说。
乔大接过碗朝安子笑笑又回到房前去了。
乔大把点点抱起来,抱到一丛草旁边,指着上面的几只小毛虫说:“点点你看,这些小东西都是懦夫,哪有我们点点威风……”,
点点看着那几只粘附在草叶上的毛虫动作迟缓,就跟瘸了腿少了胳膊一般,心里自然镇定了几分。他站在原地,呆呆地看了那几只小毛虫几分钟,终于觉出它们不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他利索地脱掉裤衩,掏出自己的小鸡鸡,一条热腾腾水柱划着弧线就朝草叶上的虫子冲将过去。草叶颤抖着,很快,几只小虫子都纷纷从上面跌落下来,掉进潺潺的溪水里冲走了。
乔大立即欢呼起来,手掌拍得脆响:“胜利啦!胜利啦!点点胜利啦!”
点点也跟着欢呼道:“胜利啦!胜利啦!”
安子刚从地里回到屋里,乔大就把一大碗香喷,贲的面条递到安子手里。
安子的鼻头一耸,轻声问了一句:“哪来的猪油?”
“我刚刚才从集市上买来的。”乔大说。
“你也吃吧。”安子说。
“我跟点点都吃过了。”乔大把点点抱起来,点点拼命朝安子的碗边凑,嘴里还哼哼唧唧地嚷着还要吃。
安子夹了一根长长的面条喂进点点的嘴里,点点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不再哼唧了。
乔大轻轻地抹掉了点点嘴角的面汤,说:“看你嘴馋,填不饱的猪肚皮……”
外面的阳光很好,微风轻轻吹动着,四野呈现出一派单调的绿,但出奇的干净。
点点又跑出屋外玩去了。
安子看着点点欢快的背影,舒心的笑在脸上荡漾开来,安子美如花朵的笑脸使乔大看呆了。
乔大走过去,轻轻地把门关了,屋里顿时一片漆黑。
“别关门!”安子下意识地朝门口冲去。
但乔大墩实的身坯就像一堵墙,安子被严严实实地挡了回来。
黑暗中乔大不由分说抱起拼命挣扎的安子,温湿的舌头在安子的脸上乱抹,然后又拼命地朝安子的嘴里挤。
“乔赖!你不怕吗?”安子问
“求求你!别叫我乔赖,叫我乔大。”乔大的双眼紧闭着。
“乔赖!你不怕达贵吗?”安子又问。
达贵是安子丈夫的小名。
乔大的手像触电一般,在一瞬间松开了。他呆呆地立在原地,喘着气,两个眼珠如两团跳动的火,在黑暗中贪婪地灼烤着安子。
安子平静地走过去,轻轻推开了挡在面前的乔大,把门吱嘎一声打开了。
屋里一下子亮得刺眼。
安子理了理自己的头发,伸手在乔大的腋窝处狠命地拧了一下。
“坐吧!”安子说。
乔大耷拉着脑袋蹲在地上,两行泪珠顺着腮帮子流淌下来。
安子走过去,双手托起乔大的脸,热乎乎地在乔大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原谅我,乔大!我这身子是达贵的,不能给你……”安子说。
见乔大无声地流泪,安子的泪水也出来了。
安子想起了自己的男人达贵,想起了两年前那场横冲直撞的洪水。达贵在点点刚满两岁的时候就到沿海一个叫不出名的地方打工去了。发洪水的时候,达贵离家刚好一年。安子的母亲、哥哥和嫂嫂都被滔滔的洪水吞没了,安子和点点的性命是乔大捡来的。那天乔大正朝着高高的河堤上逃命时,恰巧看见安子抱着点点惶恐地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杈间。点点的哭声尖锐刺耳,安子的呼救声撕心裂肺。浑浊的洪水像一只猛兽在安子和点点的脚下奔腾咆哮着。乔大来不及想啥冲过去背起安子和点点,涉着齐胸的洪水,趟了几百米,终于趟到了河堤上。当乔大跌跌撞撞地把安子和点点放在地上时,三个人都已累如一滩泥,仰面躺在那里,好半天一动不动。
乔大缓过气来用手轻轻推了推身边的安子时,只见湿漉漉的单薄的衣衫紧贴着安子发烫的肌肤,两个乳峰挺挺的,仿佛要从衣衫里面蹦出来。
乔大的心里禁不住“咯噔”了一下。
四面的洪水就像千军万马,呼啸着,嘶鸣着,气势汹汹地朝前奔去。一副势不可挡的样子。
安子把点点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哭得乔大不知如何安慰才好。
后来,乔大帮安子掩埋了亲人,帮安子盖了这间临时遮风避雨的草房,又帮安子拓荒垦地,种上了庄稼。还把政府发放给他的救济金分了一大半给安子和点点。有一回,点点发高烧,烧到了四十度,乔大背着点点跑了二十几里山路赶到乡卫生院,才算保住了点点的性命。
安子的心中对乔大充满了感激之情。
乔大家也遭了洪水,房屋没了,但一家老小还算平安。乔大是村里的会计,三十出头了还没娶上媳妇。乔大一直住在哥哥家和哥哥侍奉着年迈的老母。
自那次洪水以后,乔大心中又多了一份牵挂,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安子和点点的命运跟自己连在了一起。每天他都抽空朝安子家跑,看安子家有没有什么活需要帮忙。
安子的心情也很矛盾:自己的男人达贵不在身边,一个光棍男人经常在自己家里进进出出的,难免遭人闲言,但她不忍心拒绝乔大。
“乔大!今后你别天天朝我这里跑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安子曾鼓起勇气对乔大说。
“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好艰难啊,”乔大说,“等你男人达贵回来了,我就不再来了……”
“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安子问。
“我怕什么?你我身正不怕影子歪。”乔大说。
见乔大那副伤心的模样,安子想缓和气氛:“乔赖!去帮我把点点找回来。”
乔大像个听话的孩子站起来抹抹泪水走出门外去了。在屋里呆久了,乍一出门,外面的阳光变得异常眩目。乔大只得半眯着双眼,把视线从一片蓬蓬勃勃的庄稼地里慢慢向上移,然后才敢正视蓝得透明的天空和爬了一丈
多高的太阳。
“点点!快回来!我给你捉虫子玩。”乔大的声音在寂寥的庄稼地里回荡。
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着,有一天达贵真的就回来了。
达贵一脚门槛里一脚门槛外手把门框站在门口,只见他皮肤黢黑,无精打彩,脸上的胡子又粗又长,头发象被胶水粘在了一起,一小团一小团乱蓬蓬地朝上打着卷儿。
达贵说:“安子!你们什么时候搬的家?我一路打听才找到你们……”
安子见几年不见的达贵这副落魄潦倒样不敢相认,她目不转睛地打量了一阵达贵,然后一下子猛扑上去,给了达贵重重的两耳光后,边嚎啕大哭边骂道:“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啊,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都三年了,你连一句话都没给我和点点捎来……”
达贵像一根柱子,任安子怎么摇晃,一动也不动。
“你知道吗?你知道这几年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娘和哥嫂都没了啊……”
安子的嚎啕声震得屋顶的草也在打颤。
“发大水那年你在哪里?你个没肝没肺挨刀的东西,我和点点差点就见不着你了,你知道吗?”
正在这时候,乔大抱着点点进屋来了。点点在乔大的怀抱里不停地挣扎着,嘴里像只山雀一样不住地嚷嚷着。
乔大看见一个男人的背影堵在门口,便侧了身进到屋里。回头一看,原来是达贵!乔大倏然间紧张得脸上一阵阵发热。
“哦!达贵你回来啦?”乔大的眼睛不敢正视达贵。
达贵的目光无神地扫过乔大的全身,然后从嘴里挤出几个字来,不仔细听根本就无法听明白。
达贵说:“乔大你串门来啦?”
乔大边讪讪地应着边侧身往屋外走,最后含含糊糊地留了一句话:“你们一家子慢慢聊,我先走了……”
点点本能地走上前去,抱住达贵的双脚摇晃着说:“你是我爸爸。爸爸你的衣服好脏啊。”
安子一把将达贵拽进屋来,按在凳子上坐下,然后倒了一碗水递给他。
“达贵!你知道这几年我跟点点是怎么过来的吗?”安子问。
达贵用手抹脸上的泪时把手上的尘垢汗渍全抹上去了,五个手指清晰地印在腮帮子上。
“安子!”达贵眼泪汪汪地问,“你娘和哥嫂真的就没了吗?”
“你就不想想我能拿娘和哥嫂的生死跟你开玩笑吗?达贵啊达贵,外出三年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你真让我心寒……”
达贵顿时嗡嗡地蒙面大哭起来。
达贵哭了好一阵才停住了。他抹掉泪猛地站起来,从门后抓起一把锄头就往门外走。
莫名其妙的安子跟在达贵身后问:“你要干什么?”
“我到地里干活去。”达贵头也不回。
“你瞎了眼吗?田里的庄稼已长那么深,你拿锄头挖啥……”
“我铲铲田埂上的草……”
达贵说着话的时候已经走老远了,安子追不上,便停了下来。嘴里还在嚷:“达贵你疯了吗?你有使不完的劲儿明天咱们家就盖房……”
达贵已在田埂上铲开了,安子远远地看着他一锄一锄有力地挥舞着板锄,把田埂上的泥土溅得老高。四面的绿色庄稼在微风中恣肆摇曳弥漫,达贵在阳光下就象这广袤的原野中的一帧剪影。
安子叹了一声回屋张罗晚饭去了。
吃过晚饭以后,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一阵凉风从遥远的天边吹到屋前,吹进安子的家里。在满天星斗的夜空下,田野显得愈加辽阔而沉静。
安子把房门关了,点亮了豆大的油灯。
诓点点睡熟以后,安子靠在床头上凝视着心事重重的达贵,眼眶里的一潭秋水在闪烁。
“达贵!”安子说,“你还不想睡吗?”
达贵不言语,这是将手肘撑在桌子上托着腮,望着豆大的灯光发呆。
“达贵!”安子又说话了,“你愁个啥嘞?人回来了比啥都重要。”
达贵把头耷拉下去了,几乎埋在了双腿之间。
“达贵。”安子说,“这三年我为你守住了身子,你知道吗?守得好难呀!”
达贵哭了。
“达贵!别发呆了,来,歇下吧。”
达贵仍然没有上床。劳累了一天的安子困极了,不再管他,不一会儿便睡熟了。
半夜安子醒来时,摸摸身边还是空的,起身一看,达贵和衣蜷缩在地上。
油要燃尽了,灯光开始暗淡下来。
安子从床上下来,使劲地把达贵摇醒,嘴里不停唠叨着:“没出息,出门三年回来比大姑娘的脸面还薄。快起来上床睡去。”安子边说边把达贵朝床上拖。
达贵醒来,见安子正费力拖他上床,紧张的他连连摇头摆手说:“求求你了,安子!我不上床,我不能上床啊。”
“这是你的家,我是你媳妇,又没犯哪家王法,咋就不能上床啦?”安子说。
达贵“唰”一下脱掉裤头,露出自己的下身,“你看吧!安子,我得了那种脏病,花完了所有的钱,怎么治也治不好,我可不能传给你呀……”
安子惊呆了,张着嘴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达贵穿好衣服从门后拿了把锄头,开门出去了,嘴里说道:“我现在只求你让我在家里呆着种粮食、收粮食,其它什么也不想了……”
“深更半夜地你要上哪去?”安子追了出去。
可达贵就像没听见,打开大门消失在黑夜中。
安子还是回不过神来,这时传来达贵“咚咚”的挖地声,那一声比一声沉闷的挖地声就象一锄一锄挖在安子的心上,将安子的心给挖碎挖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