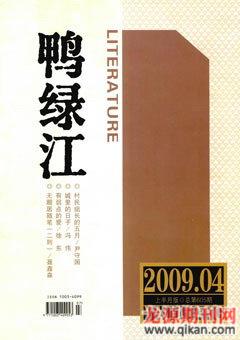村民组长的五月
尹守国
美丽河在辽西这疙瘩也算一条大河了。由于受阻黑龙山,在合庄附近打个死弯后,就一溜烟地向西北窜去。河的上下游,村镇毗邻,皆因受到这条母亲河的润泽而不同程度地繁华起来。惟独合庄,似乎是一个体单智弱的弃儿。
合庄不过是一个自然村。自打生产队那会儿,王俭就当队长了。人民公社胖成现在的黑龙镇政府,王俭却由原来的队长瘦成村民组长了。
五月节刚过,王俭去村上开会。村主任葛秃子在总结各村春季打井情况时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不再靠天吃饭了。我们要和天斗,斗不过天,我们就和地斗,斗不过地,我们就要在人上下功夫。总之,我们不能老实地呆着。说着,他扫一眼下边的人。见大伙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喝水,有的在交头接耳地扯闲篇,还有人把腿放在椅子上,正用手抠着脚丫子缝里的泥巴。葛秃子攥起拳头,往桌子上重重地擂两下,说,你们现在能不能老实地呆一会儿,听我说两句。
会场渐渐地肃静下来,葛秃子继续讲话。他说,在这场战天斗地的打井战役中。前庄的王小手和胜利屯的王大眼镜做得不错。他们发扬王进喜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男女老少齐上阵,仅用两个月的工夫,就凿出四眼井来。而且个个都见水,他们真不愧是铁人后代。葛秃子说到这儿,朝坐在前排的王小手和王大眼镜点点头。并首先鼓起掌来。王小手和王大眼镜也跟着鼓起掌来。
虽然大伙都没响应,葛秃子仍旧习惯性地向下边做了个停止鼓掌的手势。他说我这个人讲话,就不愿意说“但是”这两个字。但是,不说又不行。我们在表扬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我们中间有极个别人,对打井这件事情。认识得不够深刻,人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使我们美丽村,在全镇的春季打井运动中,没能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因为一个虱子,烧了皮袄,因为一条臭鱼,搅了一锅汤。这个人是谁,在这儿我就不点名了,以后自己寻思着办吧。
葛秃子的话刚停顿下来,整个美丽村十三个村民组长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王俭。有瞅着他呲板牙的,有瞅着他挤咕眼的,还有几个皮笑肉不笑的。
王俭被他们瞅得有些来气,他想辩解几句,可刚要张嘴,就见葛秃子朝他做了个拍球的手势,意思是让他稍安勿躁,他还有下文呢。王俭环视大伙一眼,最后把目光锁定在葛秃子的秃头上。
葛秃子感觉王俭的目光像蚊子一样,盯在他的脑门子上。他抬起右手摸了摸,语气有所缓和。他说,其实合庄的表现也不错,老王带领全村老少爷们,奋战两个月,只是没挖出水来罢了。按理说,这事不能怨老王,老王不是龙王爷,他也不知道哪疙瘩有水、哪疙瘩没水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年代,你没打出水来,就等于没打。这就和强奸一样,你没挨着女人的边,她咋说也给你赖不上。关于这点,老王你耍有个正确的认识。同样的土,同样的地,同样是铁人的后代,为啥别人能挖出水来,而你不能,这是个问题呀!你回去后,要深入细致地研究研究,也可以上别的村子取取经,找王小手给你们把把脉,争取在秋季大会战中,打出成绩来。
王俭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把手里的半截烟头扔到地下,用脚来回地碾着,直到把烟头踩成了土,才停下来。这期间,葛秃子又说些啥,他根本没听见。
接下来葛秃子讲到计划生育问题,他刚开了个头,大伙又把目光投掷过来。这次王俭把头低下了。他觉得在这件事上。无论葛秃子咋说,他都没啥委屈的。去年,合庄的李二歪趁着在外面打工的机会,神出鬼没地生出个娃娃来,而他这个村民组长,还在家里好心好意地找人帮李二歪莳弄过庄稼。尽管这件事情是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作为合庄的当家人,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负这个责任,这就像孩子在外面惹了麻烦,家长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一样。为了这件事,一直想当组长的李老疙瘩,还特意到村委会告过王俭的黑状,说他在变相地支持李二歪超生。村上的妇联主任去调查过,只是没查出个子午卯酉来。孩子既然生下来了,谁也没办法再让他缩回到他妈的肚子里去,最后村上只能是罚点钱,也就算了。
但这次葛秃子没批评哪个村民组,他只一味地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他说,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首要任务是抓计划生育。只有把男人和女人裤裆看紧了,人们才能把精力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他的话刚出口,王俭又抬头瞅葛秃子一眼,跟着撇了一下嘴,随后把两只胳膊支在桌子上,抱着脑袋,也顺便把耳朵捂起来。他觉得葛秃子的话说得都不如放屁有味,超生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看裤裆能解决的事。至于怎样解决,他也说不好,反正不像葛秃子说的那么简单。不过王俭这一系列动作,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葛秃子并没发现,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妇女主任裙子下边露着的半截大腿。
终于捱到散会,王俭连个招呼都没打,推起他的那辆破自行车,就稀里哗啦地出了村委会。他不屑去和任何人计较,在他的眼中,在座的那些人,包括葛秃子在内,都还是些嫩秧子。在他当队长那会儿,他们都还背着小书包冒着鼻涕泡呢。
在回家的路上,只顾低头骑车的王俭,差点给镇上的邮递员撞上。邮递员叫住他,说,老王,这儿有你们庄上一封信,你给捎回去呗。说完,立好自行车,开始在他那个钱褡子似的帆布袋子里翻拾着。
王俭简单地和邮递员客套几句,邮递员刚走,他就迫不及待地把信拆开了。作为目前合庄最有文化的人,王俭知道私拆别人的信件是违法行为。但凡是经过他手的信,他都在所不辞地拆看了。他一直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是助人为乐的表现。
这几年,庄子里那些识字的人,都去外面打工了。在家里的,基本都是些不识字的。邮递员只负责把信送到村上,整个合庄,只有王俭去村上的机会最多,每次都是他把信给大伙捎回来。以前谁家里来了信,他把信交给人家后,人家都得找他给看看写的是啥内容。久而久之,他觉得那样做属于脱了裤子放屁,便自作主张地省略了那道程序。现在他每次都是先看完信后,再把信交给收信人,并告诉人家,你家的啥亲戚来信了,说了个啥事。收信人接过信来,有的看一眼,有的连一眼都不看,直接撕成一寸多宽的纸条。当成卷烟纸了。
王俭回到合庄,已经是十点多了。他没顾得进院,直接奔王秋生家去了。
老王家这些人,都是一个老祖宗繁衍下来的子孙。王俭在他们这辈上排行老五,王秋生他爹排行老二,他们是叔伯兄弟。
王俭把自行车立在王秋生家门口,没好气地砸着他家的大铁门。王秋生的媳妇跑出来开门,说,五叔,你有事啊?王俭沉着脸问,秋生呢?王秋生媳妇赶紧回答,说他上山干活去了,一会儿就回来。王俭把目光自上而下地移动~截,瞅一眼侄媳妇微微隆起的肚子,转身推起自行车走了。他走出几步,回头冲着侄媳妇说,等秋生回来,让他上我家去一趟。王秋生媳妇答应着,说,五叔,你不上屋呆一会儿?王俭像是没听见似的,骑上自行车,又奔李志平家去了。
李志平家的大门开着,王俭直接把自行车骑到了人家的当院。他在当院转了个圈,把车头挑过来,脸冲着大门口。他没下车,一条腿支着地,另一条腿
搭在自行车的横梁上,他扭头冲着屋里喊了一嗓子,家里有人吗?
李志平老婆从屋里跑出来,王俭把手里的信递给她,说,信是你们家二丫头写回来的,她在北京打工挺好的,还处个对象,是河北廊坊的,问你们两口子同意不同意。要是同意,给她回个话,她领回来给你们看看。王俭说完,支在地上的那条腿蹬一下地,人就坐到车座上了,一副要走的架式。
自行车刚刚启动,被李志平媳妇抬手拽住了。王俭身子一歪,赶紧用左腿支住地,另一条腿从车上迈下来。自行车倒在地上。王俭回过头,冲着李志平媳妇嚷道,你他妈的彪呀,差点摔着我。
李志平媳妇站在那里呵呵地笑,她说看你刚才这架式,不像是五十来岁的人,比兔子还灵活。你忙着走啥?我还有事想跟你讨个主意呢。
王俭弯腰把自行车拎起来,靠在跟前的一棵杏树上。他抬手从树上捏下一枚青杏,用手抹几下,扔进嘴里,连皮带核一起嚼着。青杏只有麻雀蛋大小,王俭酸得可着劲地吧嗒着嘴。王俭说,啥事,你说吧,我听着呢。
李志平媳妇抖了抖手中的信,说,就这事呗,你说咱们同意还是不同意?
王俭说这事你跟你们当家的商量啊,跟我商量有个蛋用,我又不是你们家当家的。
李志平媳妇说,我们当家的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啥事都没个主意,跟他商量有个蛋用,你不是咱们村子大当家的吗?你就帮老嫂子拿个主意吧。
王俭犹豫一下,说,这事没啥可商量的,丫头大了终究是人家的,嫁到哪去还不是一样,就让孩子把人领回来看看吧。要是小伙子是那样的,拿得起放得下的,远点怕啥?嫁到国外去才好呢,说明咱合庄的闺女有能耐。我是没去过廊坊。但我从电视上看过。那地方咋也比咱这大山沟子强多了。
李志平媳妇点头应答着,她说,那好,我就听你的了。我让二丫头把人领回来,你过来看看,你见多识广,帮我们把把关,真要是各项事情都遂心,你就给他们当个媒人。虽说他们是自己处的,真要是到了成的时候,咋的也得有个媒人好看点。
王俭说,这事还八字没一撇呢,你着啥急?成不成两说着呢。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跟嗑瓜子似的,两个人在大道上随便瞅一眼,就能对上眼,还没等弄明白对方叫啥呢,又黄了。
李志平媳妇走过来,在王俭的背上拍了一巴掌,说看你说的,哪能那么随便呢?咱们孩子你还不知道根底,见了人都不敢说话,能在外头自己处个对象,我都不大相信。
王俭点点头,说我指的不是咱们二丫,像二丫这样的好孩子,现在真是不多了。不过这事还是慎重点好,咱们丫头是好孩子,谁知道那小子啥样?还是等到见着面再说吧。说完,他推起车子走了。
王俭刚回到家里,王秋生就来了。他进门就问,五叔,你找我有啥事?王俭耷拉着眼皮问,你媳妇怀孕几个月了?王秋生说,好像有四五个月了。王俭扬起脸来,声音变得有些不耐烦,说到底是四个月还是五个月,这事你还叫不准吗?王秋生寻思了一会儿,说应该是五个多月了。王俭啪地拍了一下大腿,大声地骂道,你他妈的比李二歪还笨,你这不是成心给我上眼药吗?
王俭骂完侄子,气呼呼地从兜里掏出烟来,他自己点燃一支,把烟盒和打火机顺着炕上一推,扔到侄子跟前。王秋生没敢去拿,他打小在王俭跟前,总显得很拘束。他从兜里掏出旱烟口袋,自己卷了一支,从炕上拿起打火机点着了。
爷俩都低头抽烟,王俭把脸扭向炕里,给侄子个脊背。王秋生等了半天,见五叔也没有再跟他说话的意思,便悄悄地站起来,顺着炕沿往门口挪动着身子,在接近门口时,闪身到了外屋,跟在外屋做饭的五婶吐了吐舌头。他并没急着离开,而是站在门框边上,从对面墙上的镜子里看着五叔。过了老半天,见五叔没啥反应,还是勾着头在那儿抽烟,这才跟五婶点点头,溜出院子。
当天下午,王秋生便赶着驴车,把女儿送到老丈人家去了。连同女儿一同送走的,还有一头小猪和十几只母鸡。傍晚时,他是一个人走着回来的。
王秋生两口子离开合庄三天后,王俭开始抓劳工。他刚出院子门口,就发现东头小卖部门口集着一帮打扑克的。他信步走过去,在打扑克这些人身后转了一圈,见这四个打扑克的,有三个是他本家兄弟。跟前十好几个巴眼看热闹的人中,也有两个是他们本家。他停在王老七身后,用脚踢了踢他的屁股。王老七以为是谁跟他闹着玩呢,回头刚想骂,一看是王俭,便不好意思地问,有事啊,五哥?
王俭说你们挺大个人了,不干点正事,大白天的玩的哪门子扑克?老七听后,辩解说,地里的那点活早就干完了,没啥活要干的了。王俭嗯了一声,说你家没活,那帮我去干点活吧。
几个人停下扑克,老七问,你地里的活不也干完了吗?王俭看看周围坐着几个老李家的娘们,其中就有李老疙瘩的老婆。他说不是地里的活,是院里的活,我家的猪圈墙倒了,帮我砌上。说着进到小卖部里,拿了两盒烟和几瓶子啤酒。
老七哥几个跟着王俭来到他家里,进院后,老七就叫起来,说五哥。这猪圈不是好好的吗?王俭冲着老七笑了笑,说,咱们哥几个今天没事,帮着秋生把北大地的那片谷子耪出来。他们两口子出去打工了,咱们这些当叔叔大爷的,不能眼看着他的地荒废了。
来的这五个人,都有些情绪。老七挠着头皮说。要我看,五哥,你多余管这事,去年你帮李二歪家张罗一通,也没捞着好,还差点让人告了,咋还不长记性呢?
王俭的神情显得很严肃,他说你们还是没转过这个劲来。这是两码子事,咱们先别管人家出去干啥了,咱们是庄稼人,地就是咱们的命根子,也别管谁家的地,荒废了咱们都心疼。再者说了,这回跟李二歪不一样,这回指定能捞着好处,不光是我,你们也都能捞着好处,这个好处还挺大的呢。
几个人一听有好处,便有了兴趣,把目光都集中在王俭的脸上。老七问啥好处?王俭说,好处指定是有的,咱们先干活,等干完活,我告诉你们。说着他就招呼大伙套上他家的马车,车上装好干活用的工具,他把那几瓶啤酒也放到车上。老七问,该不是就这几瓶啤酒吧?王俭说不是,那个好处比这可大多了。
等中午干完活了,老七又问起好处的事来。王俭嘿嘿地笑起来,说,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咱们替秋生干活,他干啥去了?大伙说这还用说吗?他躲出去生孩子去了呗。王俭拍着大腿说,这不就得了,再过几个月,又有一个娃娃管咱们叫爷爷了!你说这是不是好处?这孩子从下生那天起,就管咱们叫爷爷,一叫就是一辈子。到咱们死的那天,得来给咱们跪着磕头;咱们死后,他路过咱们坟地时,也得说这是他五爷爷或者他七爷爷的坟,你说这个好处大不大?
几个人听后都苦笑,说理是这个理,就当是做义务工了。王俭听后立即纠正,说这可比义务工强多了。干义务工没人搭交情,这好歹还有人搭交情呢!他又发了一茬烟,给每个人亲自点上。他说二哥死得早,秋生跟前没啥至近人了。孩子出去干啥,咱们管不着那么多,在家帮他照顾着点地,于情于理都是应该应份的。以后大伙上山干活时,谁的地离秋生家的地近便,都想着点,帮他搭把手,人心一杆称,等以后
秋生过好了,忘不了咱们的。在场的几个人都纷纷点头,说,这点活,如果大伙一起下手,算不了啥。
王秋生走后不到一个星期,镇妇联就到合庄来找他了。来的人见他家锁着门,便来找王俭了解情况。镇妇联的人问王俭,知道不知道王秋生离开合庄的事。王俭说知道。镇妇联的人说,那你为什么不拦下他?王俭说人家两口子出去打工了,庄上出去打工的人多了,我一个小小的村民组长,有啥权力拦下人家。镇妇联的人说,你不知道他媳妇怀孕了吗?王俭说这个我可真不知道,没人跟我说过,我也好几个月没见着他媳妇了。镇妇联的人往前上了一步,说,那咋有人举报说你知道呢?王俭听后哈哈地笑起来,他说照你们的逻辑,如果有一天,出来个人说我知道本·拉登在哪藏着,你们也得逼着我去找他吗?
镇妇联的人不再吱声了,村上的妇女主任问王俭,说,王秋生走后跟你联系过吗?王俭说联系过,打过电话,打过好几次呢。我是他五叔,他能不给我打电话吗?妇女主任问王秋生是从哪个地方打的电话?王俭说,第一次好像是在河北,第二次是在湖南,第三次在深圳。镇妇联的人气得直跺脚,说照你的这个速度,他再给你打电话时。八成已经到外国了。王俭听后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有这个可能,现在国内工作不好找。有些地方还拖欠农民工工资,年轻人上外国试试有啥不好。
镇妇联的人从王俭这里没得着好话,他们就朝村妇女主任发脾气,说,你们咋让这样的人当组长,一点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村妇女主任一脸的无奈,她说,选组长的事不归我们管,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这个老王当组长好几十年了,群众威信还挺高的,我们也拿他没啥办法。
镇妇联的人走后,王俭蹲在门洞子里接二连三地抽了四颗烟。他也觉得自己今天做得确实有些过分,有损于他这些年当队长的声誉,但不这样做,他叉没有别的办法。在开会那天,大伙都看他时,他真想把王秋生的事捅出去算了。可话到了嘴边,他还是没张开这个嘴,且别说是自己的侄子,就是庄子里的任何人,他也做不出这种事来。在见到王秋生之前,他还在想好好地劝劝侄子,说现在农民有了合作医疗,有病也不犯愁了;现在丫头都能当家作主,能养活爹妈了,动员侄子主动去医院把孩子做了。可见了侄子后,他想好的那些话,竟然一句也没说出来。他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想到把组长的位置让给李老疙瘩,他觉得抓计划生育这个活,还不如打井容易呢。
当天下午,有人又告发王俭的消息在合庄传扬开了。人们首先把怀疑的对象集中到李老疙瘩身上。全村子的人,别说是老王家的了,就连老李家的一些人,都不搭理李老疙瘩了。李二歪站在东头小卖部门前,当着很多人的面,骂李老疙瘩不是个人,说从此再也不认他这个本家叔叔了。
话传到李老疙瘩的耳朵里,他便来找王俭撒火,两个人在当街吵了起来。不一会儿,便集结一街筒子人,大伙听明白事情的因由之后。都围在王俭的身后,目光齐刷刷地瞪着李老疙瘩。有几个不怕事的老娘们,推着王俭往前去,说五叔,你揍他,到时候我们一起给你证明,说是他先动手打你的。回头你再讹他,我就不信整不老实他。王俭回头瞪那几个娘们一眼,说你们还嫌事不大呀?超生是啥好事啊?李老疙瘩的老婆一看要引起公愤,这样僵持下去,李老疙瘩也不会赚着便宜,便赶紧扯着他回家了。
五月二十那天,是王俭五十五岁的生日。早晨,王俭刚起来,王秋生就来电话了,说他在外边挺好的,已经安顿下来了,告诉王俭不用惦记着他们。这是王秋生走后,第一次给王俭打电话。王俭听到电话里有杂七杂八的声音,知道侄子是用公共电话打的。王俭哼哈地应答着,他心疼电话费,便问侄子还有别的事吗?王秋生说没事,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王俭微微地笑了一下,嘱咐侄子在外面要多长个心眼,遇事不能冲动。他挂断电话后,笑着对老伴说,秋生出去这么几天,长出息了,还知道给我打个电话祝寿呢!看来哪个孩子都不白疼。
王俭刚吃过早饭,李二歪两口子就来了。李二歪的老婆抱着小儿子,领着大闺女走在前面,李二歪在后边拎着一篮子鸡蛋。他们的到来,让王俭感到很意外。李二歪把孩子抱到王俭跟前,说快让五叔看看,我们一家老小现在能吃上饭,多亏您老人家照应了。
李二歪和王俭家本来没什么直接的亲属关系。但一个村子的人,七拐八拐的便都拐出点亲属关系来。李二歪的表嫂子是王俭的叔伯侄女,这样他便跟着他表嫂子管王俭叫五叔了。王俭接过孩子来,他都好多年不抱这么大的小孩子了,所以抱起来有些滑稽。他不是抱着,而是用两只手兜着。因此,他看到的只是孩子的头顶。孩子的头发不好,仅有的一点头发还黄毛拉瘦的,这让王俭自然想起葛秃子的脑袋。他便顺口说了一句,这孩子长得,可比葛秃子强多了,将来一定比葛秃子有出息。他的这句话,说得李二歪两口子莫名其妙的。五婶赶紧奔过来,从他手里接过孩子,说我看看这个大孙子好看不?
李二歪抽完一支烟,便张罗着回家。王俭看着地下的鸡蛋,说你拿回去吧,心意我领了,现在你们家孩子大人都需要营养,给他们补补,把孩子拉巴得壮实点,我看着比吃啥都香。李二歪说家里还有,够吃了,十来只鸡呢,现下现吃就赶趟,这些是特意给你留出来的。王俭又推让了几次,李二歪急得脸红脖子粗的,两口子都吭吭叽叽地说不出啥来,只是一个声地问,五叔,你不收,让我们这脸往哪搁啊?他们问得王俭也没法再推辞了,他说好吧,鸡蛋留下,人也留下,晌午都在这儿吃豆包,咱爷俩也挺长时间没一起喝酒了,今个好好地喝两盅。李二歪吓得连连摆手,说五叔,你就别寒碜我了。我就表示这点心意,再在这里吃饭,以后还想让我见人不?王俭一看这老实人较起真来,还真没治,便也没再深留,放他们走了。
送他们走出大门,王俭又叫住李二歪,说你现在家里又多出一张嘴来,以后你得比别人更操劳些了。国家号召计划生育,其实是个好事,是想让大伙都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孩子多了确实累人啊!你既然偷着把孩子生下来了,就得负起当爹的责任来。李二歪听后连连点头,说,五叔,你放心,我有的是力气,我白天去建筑工地干活,晚上回来再伺候庄稼。我都给你添不少麻烦了,以后绝不让你操心。
这天上午,王俭收到十几份生日礼物。有的是几瓶啤酒,有的是一只母鸡,有的是一筐青菜,还有的是几斤挂面。这些人都是打发孩子送来的。孩子进屋只说,我妈让我把这个给你家送来,说完就转身跑了。
到了晌午吃饭时,王俭打发大儿子各家叫一遍。大伙都说送这点东西,没别的意思,知道你们家啥都不缺,我们就是想告诉老队长,我们还记着你的生日呢。大伙的这些话,让王俭很不安,也很感动。他倒不是因为这点礼物,而是满足于大伙对他的认可。自打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后,他总感觉有一些失落,不用再管哪片地种啥了,不用再给社员分工了,不用再去给各家分配粮食了,他这个组长当得也没精打采的了。在他的感觉里,自己似乎成了个多余的人,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人。有时候他认为他拿的这份工资,是
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他总想为大伙做点事,哪怕是帮人家跑个腿学个舌的,他都觉得心里踏实些。
王俭这个生日过得还是很高兴的。中午他跟儿子喝了一斤多白酒,他还想再来点啤酒,见儿子喝多了,儿媳妇不让再喝了,这才作罢。儿子走后,他睡了一个下午,直到掌灯时分,才被老伴叫醒,草草地吃了一碗面条。
到了晚上,王俭失眠了。中午他老伴蒸的豆包,把炕烧得挺热,他躺在炕上,感觉心里烦得慌。他越是心烦。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心烦。十二点多钟时,他索性穿起衣服,来到当院。他家的厢房是三间平房,房檐头上放着一个梯子,房顶上放着一张凉席,每到夏季的晚上,王俭都要到房顶上躺一会。他愿意仰面躺在房上看星星,这个习惯他打小就有,并且坚持这么多年了。合庄的房子,不管正房还是厢房,人们都愿意盖成“人”字顶的那种,王俭把厢房盖成平顶的,在盖的时候他就说过,为了躺着舒坦。
王俭在房顶上躺了近一个小时,就觉得身上有些凉意,并有点湿乎乎的感觉,他知道是下露水了。他坐起来,把上衣披在身上。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发现房后小短垄那边有一丝光亮在晃动。
王俭起初没注意,以为是露水闪呢。他站起来,发现那光亮有些奇怪,忽左忽右地移动着,而且那条光线一直亮着。他揉一下眼睛,又辨别一下方向,确定那个有光亮的地方是前年打的那眼机井的位置。他想了想,今天应该没人浇地,前几天才下的雨,地里还不旱,白天都没人浇地,晚上更是不可能的。想到这儿,他感觉有些不对劲,便匆忙从房上下来了。
王俭没进屋,也没开大门,他怕吵醒老伴,也怕惊动左邻右舍。他把梯子移动到后院墙边,从墙头溜出院子。
小短垄离合庄也不过半里多地,顺着北道往前走,直接就能通到地头上。王俭走到地头时,就听见了动静,确实是有人,但并不是在井房这边,而是在地中间的变压器台跟前。
王俭没进地里,他蹲下来,在地头琢磨一会。他觉得偷变压器这样的活,肯定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他细致地辨别一下,听声音最少是四个人。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发现路上停着一辆农用三轮车。他从地上摸起一把土来,往车跟前扬去,没听到动静,他便确定车上没人,同时也确定这台车肯定是他们用来运输变压器的工具。
王俭摸到车跟前,刚才他在地头蹲着时,还在想自己人单势孤,怎么对付这几个贼呢?现在突然有了主意。他在黑暗中笑一下,心里说,你偷我的变压器,我偷你的车,这叫贼偷贼,越偷越肥。
王俭把三轮车推出田间的小路后,已经累得不行了。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湿透了,就连脚下的这双胶鞋里,也全是汗水,往前一使劲,脚在鞋里面打滑。他本想把车推回到庄子里,可实在是推不动。他刚才就是边推车边回头,他害怕那几个人把变压器抬到路上,发现车不见了,他们会顺着路撵上来。王俭左右看了一下,发现他所在的位置离西大沟不远。他绕到车头前,把车把向右转动一些。又来到车厢后,两只手推着车厢,直接向沟下移动。大约走了几十步,他感觉手上一下子轻快了,车子慢慢地顺着沟坡,自己向沟底下溜去。
三轮车迅速消失在他的视线里,紧接着听到咣的一声闷响。王俭知道应该是撞在树上了,这片沟坡子下边是葛连家的树林子。
三轮车撞树的动静挺大,在寂静的深夜里传得很远。这时,王俭已经没啥顾忌了。他顺着沟边的树林子,一路向庄子跑去。
跑到庄子西头,王俭从李伟家门前的柴垛上摸到一根镐把粗细的树棍子,照着李伟家的铁大门就砸开了。他刚砸两下,合庄的狗就集体叫起来。李伟家的灯是最先亮的,之后,周围人家的灯也跟着亮了。王俭手里的木棍子始终没有停下来,他一直砸着,直到李伟跑出来打开大门,他才瘫倒在大门边上。
李伟是打着手电跑出来的,他照了照,看清楚后,他大叫起来,说五叔,你这是咋的了?黑灯半夜的,你闹啥呢?说着就过来拉他。
王俭被李伟扶起来,坐到门口的石台上。他说,有人偷变压器。你快去找人。李伟听明白后,他又拿起那个树棍子,砸起他家的铁门。他比王俭劲大,再加上铁门打开后,三个侧面都悬在空中,声音比刚才大多了。他这一敲,整个庄子都惊动了,各家的灯光也由此及彼地都亮起来。跟前的几户人家大门有了响动,有几个老爷们打着手电出来了,往李伟家这边跑来。
这会儿,王俭歇过来点,气也喘得均匀了。他站起来,指挥着那些跑到跟前的人。他说你们这帮去小短笼,把变压器保护好;他又对后跑到他跟前的几个人说,你们这帮去葛连家的树林子,把那台三轮车看起来。说完他站起来,往他家里跑去,他说,我去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
二十分钟后,警车赶到现场时,王俭的大儿子用摩托车驮着王俭也赶到现场了。那台变压器在地当中扔着,那台三轮子在沟下翻着,前轱辘撞得掉下来了,作案的几个人早就没了踪影。
警察问过王俭具体情况后,把现场简单地看了一遍。警察说,这黑灯瞎火的也没法取证,等明天再说吧。你们留下几个人保护现场。王俭正想安排人员,李老疙瘩挤过来,说,五哥,这事就不用你操心了。你回家歇着吧,后半夜天凉,别感冒了。这儿就交给我吧,我找几个年轻人在这看着,绝对没问题。
王俭回到家里,坐在炕上抽支烟,便觉得浑身发冷。他让老伴给他找个被子披上,可还是不行。他大儿子把他送回来后,就一直没走。大儿子给他找体温计量了一下,三十八度二,发高烧,就给他找两片扑热息痛服上。他老伴又点火给他熬了碗姜汤,伺候他喝完。到了后半夜三点多钟,王俭才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镇政府就知道此事了。镇长亲自来看过现场,派出所的人取完证,找来一台吊车,把那台三轮子吊出来,拉到派出所去了。镇长打电话叫变电所的人把变压器安上,并亲自到家里来看望王俭。
镇长来时,王俭还没起炕。虽然不发烧了,但身上酸疼,一点气力都没有。镇长要打电话给他找大夫。王俭说没事,可能是受了点风,过两天就好了。镇长当即给葛秃子打了个电话,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了。葛秃子没用十分钟,也骑着摩托赶到了。他当着镇长的面,对王俭以往的工作给以充分的肯定,并当场承诺。村里一定要重奖王俭。
因为有这台三轮子做线索,案子破得很快。第三天,派出所就打来电话,说已经抓到其中的一个嫌疑人了,剩下的三个在逃。
四天后,村里通知开会。王俭赶到村委会时,所有美丽村的组长都到齐了。会场主席台上方,还用红纸写了一行大字——王俭英雄事迹表彰会。王俭刚迈进门,全场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葛秃子从主席台上奔下来,拉着王俭的手,把他领到主席台上,妇联主任把早就沏好的茶水端上来,放在王俭的跟前。
会议的第一项内容,葛秃子请王俭把他如何机智勇敢地保护公共财产的事迹介绍一下。王俭摆摆手,说没啥好说的,只是那天中午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出去溜达时碰巧赶上了。葛秃子对王俭这种说法,显然很不满意。他说老王这人哪样都好,就是有时过分谦虚。本来谦虚是件好事,这就和喝酒一样,少喝能舒筋活血,可喝多就耍酒疯,过分谦虚就跟喝
多了没啥区别。这怎么能说是碰巧赶上了呢?这分明是有责任感的表现嘛。全庄男女老少有好几百口子,谁半夜三更的不好好睡觉,出去赶这种事情?那不是有夜游症吗?接着他就代替王俭,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番。他讲得跟单田芳说评书似的,听得大伙都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着主席台上的王俭。
葛秃子介绍完王俭的英雄事迹后,就代表村委会宣布,奖励王俭一千块钱。他话语一出,在座的十三个组长眼睛都直了。大伙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老王,这回你可得请客了。还没等王俭回答,葛秃子清了清嗓子说,不过,村上暂时没钱,得等到秋后才能兑现。大伙听后很失望,纷纷把目光收回来了。
葛秃子接着又讲了几点有关变压器的防护措施,号召所有的村民,都必须向老王学习。他说尽管你们在打井的事情上表现得很好,那是老天爷在帮你们,你们知道不?人家老王不用老天爷的帮忙,人家敢于战天斗地,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啥叫英雄?这才叫英雄。你们打出水来不是英雄,如果把变压器丢了,浇不上地,这和没打出水来不是一样吗?所以,从现在起,哪个村子要是把变压器丢了,就由村民组长负责,这绝对不是开玩笑,这是一项制度,从今天起生效。说着他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跟老辈子县太爷拍惊堂木似的,吓得在座的人都赶紧抬起头来,冲着主席台上不住地点头。
散会前,葛秃子说为了给老王压惊,中午村委会请客,所有的组长作陪,今天可以开怀畅饮,不醉不归。葛秃子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又迸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这时,王俭站起来,他冲着大伙摆了摆手,掌声停下来了。他侧过身对葛秃子说,你们去吧,我中午得回去。今天李志平家的二丫头把对象领回来了,她爹妈让我去帮着把把关,早就说好了的。说完,也没跟大伙打招呼,直接出了会场。
葛秃子在身后叫起来,说老王,你别走啊,我都打电话通知饭店了。中午八菜一汤,还有小鸡炖蘑菇呢。那些村民组长一听说八个菜和小鸡炖蘑菇,也跟着一起喊起来,说老王,别走,别走啊,老王。王俭回头向大伙挥了挥手,骑上他那台破自行车,唏里哗啦地飞出村委会的大门。
葛秃子站在村委会的门口,搓着手说,这个老王,真是头犟驴。
王俭走后,其他组长围过来,问葛秃子,啥时候去饭店?葛秃子把手一挥,不耐烦地说,主角都走了,咱们还吃个狗屁呀?都回家吧!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