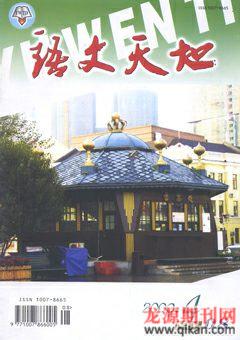患难见真情
褚忠厚
《聊斋志异》我已看过很多遍,从小学时的白话到现在的文言,感觉还是文言原著好,有些思想内容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就是那意会,那令人深深思考之后的无尽内涵,总有含英咀华之感,让人沉于文字,钻入作者所营造的凄美浪漫的故事中,去探寻无尽的宝藏。
《画皮》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影视作品也早已不遗余力地做过宣扬,但仅仅停留在蒲松龄的“明明妖也,而以为美”的层次,甚至有的影视作品毫无原著的影子。我认为很有必要探讨《画皮》的主题,以正本清源,还原著本色。蒲松龄在文末警谕世人说:“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寤耳。可哀也夫!”《聊斋志异》研究专家、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指出,《画皮》有更广阔的哲学意蕴:善良的人常受表面现象迷惑,不知道世界上不仅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更可能在美丽外表后隐藏致命杀机。本文试从另一视角对《画皮》的主题作一解读。
重读《画皮》,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蒲松龄对人物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在王生危难之际,妻子陈氏为了丈夫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体面尊严,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从而救活了丈夫,真是患难见真情。同时,为人夫者也应明确:真爱你的人是妻。
总体情节大家较熟,不再细述,只拣与王生妻陈氏有关的情节略述并作解读。王生将女鬼匿密室后,“微告妻。妻陈,疑为大家媵妾,劝遣之。生不听”,陈氏劝生送走女子,表现出了温柔体贴的一面;没有嫉妒,没有跳骂,反映的是封建社会里以夫为纲的伦理道德。但王生不听,为后文的情节发展做了铺垫,也为王生的命运埋下伏笔。王生发现女子是鬼后,因害怕鬼和妻子睡在一起,一更许,鬼来时,王生“自不敢窥也,使妻窥之”。王生的胆小,妻子陈氏的勇敢可见一斑。“生已死,腔血狼藉。陈骇涕不敢声。明日,使二弟奔告道士。”苏轼论张良有“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的话,用到陈氏身上恰如其分,丈夫亡故,大乱当前,不慌不忙,吩咐二弟去找道士,为夫报仇。
王生见鬼来时,早已吓破了胆,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只好吩咐自己的妻子去看。丈夫的弱点更能体现妻子的坚强。梁山伯虽然痴情,然而在婚姻受阻后却郁郁寡欢,终疾而亡,祝英台却毅然决然地冲破阻碍,举身赴荒冢,两人终成一对怨蝶。在表现女子的勇毅上,《画皮》与《梁山伯与祝英台》两文异曲同工。
纵观整部《聊斋志异》,蒲松龄怀着对女子的崇敬和喜爱之情,来表现中国柔弱女子的坚强和挚爱。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七次落榜,可谓郁闷终生,可他的妻子刘孺人一直以一个女性的坚韧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丈夫撰写《聊斋志异》。所以,蒲松龄对妻子的感激之情就诉诸笔端,诉诸在像王妻这样的几百个女性身上。
在二弟找来道士除鬼后,道士“乃欲离去。陈氏拜迎于门,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谢不能,陈益悲,伏地不起”。妻子对丈夫的深情由陈氏的“拜”“哭求”“益悲伏地”表现得淋漓尽致。陈去求乞人,乞人“鼻涕三尺,移不可进,陈膝行而前”。乞人戏弄她,她不恼怒,“固哀之”,乞人“怒以杖击陈。陈忍痛受之”。陈氏忍羞,忍痛,固哀之,妻子对丈夫的深情在考验面前表现更坚强。“乞人咯痰盈把,举向陈吻曰:‘食之!”“陈红涨于面,有难色”,“遂强啖焉”。为了丈夫,陈氏忍受了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肮脏,忍受了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屈辱,其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乞人消失,陈氏无望,回家,“欲展血敛尸,家人伫望,无敢近者,陈抱尺收肠,且理切哭。哭极声嘶,顿欲呕”。将一颗人心吐到亡夫胸腔中,“急以两手合腔,极力抱挤”,“裂缯帛急束之。以手抚尸,渐温……天明,竟活”。这部分描写陈的神志动作跃然纸上。面对王生的惨状,家人无敢近者,只有陈氏抱着尸体,收拾肠子,哭得声音嘶哑,到了吐的程度,可见她对丈夫之死的悲伤,也就见他对丈夫的爱之深,情之切。因此,才将乞人送的痰——人心吐出。你看她的神志动作,“急以两手合腔,极力抱挤”,“裂缯帛急束之。以手抚尸”,着急的神态,急急地处理伤口,唯恐来之不及,用手轻轻抚摸丈夫的身体,令人感动。王生何福,有陈氏这样的好妻?
看完与陈氏有关的情节,我们不难发现,患难之中见真情,对王生最好的人,最爱王生的人是陈氏。我想对天下为人夫者说:最爱你的人是妻。记着妻的情,记着妻的爱,千万不要把妻来忘怀。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不少有权有钱的丈夫渐渐不满于妻的衰老等特点,找情人,包二奶。殊不知,这些情人或二奶就如《画皮》中的女鬼,她有害人的目的,而妻只有对丈夫的关心和深情的爱。请读读《画皮》吧,王生的遭遇当成为天下找情人,包二奶者之鉴。读读《画皮》会知道,世上真正爱你的人是妻。
附:
画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独奔,甚艰于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丽。心相爱乐,问:“何夙夜踽踽独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生曰:“卿何愁忧?或可效力,不辞也。”女黯然曰:“父母贪赂,鬻妾朱门。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将远遁耳。”问:“何之?”曰:“在亡之人,乌有定所。”生言:“敝庐不远,即烦枉顾。”女喜,从之。生代携襆物,导与同归。女顾室无人,问:“君何无家口?”答云:“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怜妾而活之,须秘密,勿泄。”生诺之。乃与寝合。使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陈,疑为大家媵妾,劝遣之,生不听。
偶适市,遇一道士,顾生而愕。问:“何所遇?”答言:“无之。”道士曰:“君身邪气萦绕,何言无?”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生以其言异,颇疑女。转思明明丽人,何至为妖,意道士借魇禳以猎食者。无何,至斋门,门内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逾坦,则室门已闭。蹑迹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采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睹此状,大惧,兽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遍迹之,遇于野,长跪乞救。道士曰:“请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觅代者,予亦不忍伤其生。”乃以蝇拂授生,令挂寝门。临别,约会于青帝庙。
生归,不敢入斋,乃寝内室,悬拂焉。一更许,闻门外戢戢有声。自不敢窥也,使妻窥之。但见女子来,望拂子不敢进;立而切齿,良久乃去。少时,复来,骂曰:“道士吓我。终不然,宁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坏寝门而入。径登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而去。妻号。婢入烛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陈骇涕不敢声。
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怜之,鬼子乃敢尔!”即从生弟来。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远。”问:“南院谁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现在君所。”二郎愕然,以为未有。道士问曰:“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答曰:“仆早赴青帝庙,良不知,当归问之。”去,少顷而返,曰:“果有之,晨间一妪来,欲佣为仆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与俱往。仗木剑,立庭心,呼曰:“孽魅!偿我拂子来!”妪在室,惶遽无色,出门欲遁,道士逐击之。妪仆,人皮划然而脱;化为厉鬼,卧嗥如猪。道士以木剑枭其首:身变作浓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飀飀然如口吸气,瞬息烟尽。道士塞口入囊。共视人皮,眉目手足,无不备具。道士卷之,如卷画轴声,亦囊之,乃别欲去。陈氏拜迎于门,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谢不能。陈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术浅,诚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问:“何人?”曰:“市上有疯者,时卧粪土中。试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习知之,乃别道士,与嫂俱往。
见乞人颠歌道上,鼻涕三尺,秽不可近。陈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爱我乎?”陈告之故。又大笑曰:“人尽夫也,活之何为!”陈固哀之。乃曰:“异哉!人死而乞活于我。我阎摩耶?”怒以杖击陈,陈忍痛受之。市人渐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举向陈吻曰:“食之!”陈红涨于面,有难色;既思道士之嘱,遂强啖焉。觉入喉中,硬如团絮,格格而下,停结胸间。乞人大笑曰:“佳人爱我哉!”遂起,行已不顾。尾之,入于庙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后冥搜,殊无端兆,惭恨而归。既悼夫亡之惨,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愿即死。方欲展血敛尸,家人伫望,无敢近者。陈抱尸收肠,且理且哭。哭极声嘶,顿欲呕,觉鬲中结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惊而视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突犹跃,热气腾蒸如烟然。大异之。急以两手合腔,极力抱挤,少懈,则气氤氲自缝中出,乃裂缯帛急束之。以手抚尸,渐温。覆以衾裯。中夜启视,有鼻息矣。天明,竟活。为言:“恍惚若梦,但觉腹隐痛耳。”视破处,痂结如钱,寻愈。
异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寤耳。可哀也夫!
山东省利津县第二中学(257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