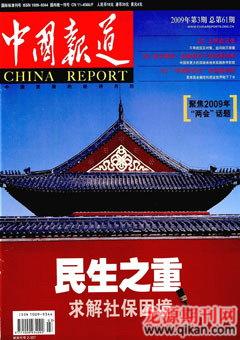《社会保险法》草案 未定型 未定性 未定局
郑秉文
草案缘何“授权”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从2D06年初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首次公开征求专家意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全文公布草案征求意见,大约经历了近3年时间。
从理想状态讲,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和基本目标在《宪法》中早已明确,例如《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法》的基本框架、基本要求和基本制度在《劳动法》里也单独设立了第九章“社会保险和福利”,并做出了七条五款的详细规定。所以,作为《宪法》和《劳动法》的下位法,《社会保险法》应该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这既是一般意义上社会保险法的本质要求,也是国际惯例。比如美国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规定十分详尽,以社保基金的运营为例,它写在第二章《联邦养老、遗属、残障保险待遇》的第一条《联邦养老、遗属保险信托基金与联邦残障保险信托基金》里,仅这一“条”的结构就非常复杂庞大,对美国联邦信托基金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投资策略等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其中下设“款”和“目”合计上百个。再例如,待遇支付问题非常重要,也是参保人最关心和全社会最容易监督的地方,第二条为《养老和遗属保险待遇支付》,它长达57页。
与前几次草稿相比,此次草案虽然做了最大努力,例如改变了之前按缴费和待遇等分列成章的体例,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个险种单列成章,各险种的规定更加集中和具体,但相对于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草案还是显得比较“空泛”和“原则”一些,比如,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显得原则性比较强,主管部门的“操作空间”比较大。而这是参保人最关心的所在,也是地方政府执行起来最容易“走样”和“变通”的地方。
与国外相比,此次《社会保险法》(草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追根溯源,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保制度正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很多问题难有定论。比如,本草案中,不包括“隐性”授权在内,仅明确授权的就至少有九处之多,其中四五个授权条款都是因为制度框架未确定的原因造成的,就是说,起草者无法落笔,难以决定,只能“推”给国务院“另行规定”。
在这么多难以落笔的“难点”中,除少数以外,几乎每一条授权的根源都可追溯到统筹层次上来。早在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就做出决定,“尚未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的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由目前的市、县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在此之后的几乎所有相关文件和政策中都提出提高统筹层次的要求。但是,18年过去了,统筹层次一动未动,就连辽宁省试点8年,还是维持在市、县级水平上。在目前制度下,这是一个难题,涉及到财政风险,提高到哪个层级,哪个层级的财政就容易陷入极大的风险之中。所以,目前的制度设计不适应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外部条件,统筹越低,效率越高;统筹越高,风险越大;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外部环境下,面对这样一个“既定的客观条件”,我们能够主动调整的只能是社保制度,让它适应这个国情,否则,“统筹困境”便成为一个“规律”。
利益集团博弈
《社会保险法》(草案)比较“空洞”,除了要避开许多制度问题,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些部门在一些协调和配合方面没有达成共识,僵持不下,只能回避或授权。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部立法,都是利益集团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公共选择的自然结局。比如,美国1974年通过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P.L.93-406),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1963年美国斯图特贝克汽车制造厂破产造成7000名工人失业导致其丧失所有企业年金的一个结果。《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在将近10年的立法过程中,同样充满了工会、雇主协会与政府多方博弈的唇枪舌剑和极大过滤,有些立法结果至今还令一些美国学者所惋惜。
我国《社会保险法》(草案)讨论过程中同样充满了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在授权性条款中,有多项是由于最终难以协调的结果,只能“授权”国务院,最明显的就是第五十七条,“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和征收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在3年草案的拟定过程中,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结果,部门博弈在2007年甚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目前,社保费的征缴是由税务部门和社保部门共同执行的,有些省份由社保部门征缴,有些省市是由税务部门征缴,从社保费征缴的数量来看,大约各占半壁江山。这个格局是早在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决定的,因为那时就已经形成了“双重征缴”的格局,当时在制定征缴《暂行条例》时也是难以协调,只能规定允许两个部门同时征缴、由地方省级人民政府自行决定。可以说,1999年条例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10年过去了,“双重征缴”体制已带来了许多混乱,但是,此次草案对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最后的说法,只能授权国务院,这样的规定等于没有规定,再一次回避了矛盾,又回到了10年前《暂行条例》的那个“原点”。而在草案中,这样“没有落定”的“不是规定的规定”,并不止这一处。
对类似部门利益的这样的矛盾,不应该再久拖不决。社保费征缴体制一拖就是10年,10年后的今天,建立《社会保险法》应该成为解决一些久拖不决问题的大好机会。像中国这样划疆而治的征缴体制,在世界各国是独一无二的,高层领导应高度重视《社会保险法》的制定,出面协调各方关系,借这次立法的机会彻底厘清和解决长期以来一些部门之间的责任和利益界限。
第三部“蹩脚”立法?
社保制度设计存在很多问题,应全面整理和反思。试想,1997年正式确立社保制度后,不到5年,即从2002年开始,农民工就开始退保,一直到今天难以遏止。为此,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于今年2月20日刚刚结束;2005年就开始不得不利用行政干预的手段连年上调养老金待遇,今年已是第5年,否则替代率就越来越低,北京已经降到40%;2005年个人账户比例不得不从11%缩小到8%,2006年和2007年在试点推广到11个省份时又不得不下降到3%或5%;做实账户的试点工作难以继续推广下去,因为已经做实的800亿元人民币投资问题解决不了,2008年11月,审计署公布的收益率只有2%,承受着年复一年的贬值风险和月复一月的通胀侵蚀。
在对社保制度简单回顾与归纳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社会保险法》征求意见草案中有那么多地方不得不回避,不得不简化,不得不授权。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问题和制度缺陷相互牵涉,不可能单兵突破,逐一解决,而根源是因为它不是一揽子设计,缺乏完整性和前瞻性,没有一
次性解决全部潜在问题,而是遇到一个问题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不断打补丁,结果造成补丁摞补丁,这样就给立法带来一系列困难:
小到参保人和单位的费率水平确定、个人待遇权益的明确预期、社保关系转续的细致规定等等,大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参保办法、农村居民养老方案,再到社保基金投资运营体制、实现省级统筹的时间和步骤,等等,上一个问题没解决,下一个问题也无法解决,结果是很多事情都难以决定下来,也不可能决定下来。2008年11月,全国网民热议延迟退休年龄还没完全结束,目前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又成为第二次热议高潮的焦点,每个补丁都会引起_定的社会震动,每一次震动都只能打上一个补丁了事,于是便形成一个碎片化制度。《社会保险法》(草案)第八十九条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按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对于这个模糊的表述,《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是否与本法规定完全一致?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社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很多很多,还处于制度未定型、未定性、未定局的阶段,一切都处在动态过程当中。制定《社会保险法》恰逢其时,正好是个机会,应借立法这个机会从制度结构上重新审视、完善这个制度,一次性地一揽子解决社保设计问题。否则,这部立法就可能成为第三部“蹩脚”立法。
全国统筹:社保“命运之钥”
在此次草案中,尽最大努力解决社保关系异地接续问题值得关注。草案规定,个人跨地区就业时,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退休时,基本养老金按照退休时各缴费地的基本养老金标准和缴费年限,由各缴费地分段计算、退休地统一支付,草案的这个规定是基于没有实现全国统筹水平的假定做出的。在这个“制度假定”下,只能这样,这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是欧盟推荐的所谓“集合与分配”(Aggregation andApportionment)。欧盟成员国之间劳动力流动和退休障碍取消之后,只能这样,比如,一个人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若干国家工作和缴费,如果在西班牙退休,就由西班牙负责对其一生工作过的国家的权益记录进行追溯和收集,这些国家将相应的缴费累计都转移到西班Xo欧盟有31个统筹单位,虽然他们是主权国家,但其成员国执行欧盟各项指令和法规条例的自觉性却是非常好的,比如,执行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对其财政赤字最高限额的要求就是一个例子。
相比之下,虽然我国几千年来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但唯独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却“统”不起来,中央政府制订的规则太简单,为次级政府留下了很大的“细节空间”,我国各地方次级政府令不行禁不止的“变通”很多,道德风险和本位主义充斥各个方面。况且,职工(尤其是农民工)在一生中,辗转十几个省市的个人缴费记录在30~40年后才由退休地去追溯和收集,道德风险的发生几率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参保人个人的道德风险、地方部门的“合谋”将防不胜防,长达一生记录的“识别成本”很高,难度很大,制度运转的交易成本极高,甚至高得足以导致无法顺利运转,财政风险很大。于2009年2月20日刚刚结束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个补丁,参保人在各个制度之间和异地跨省之间流动时需要办理复杂的转续关系,否则就衔接不上。我相信并肯定,这个“转续办法”即这个“碎片”出台之后,必将在各级政府出现更多的“暂行办法”,“制造”出很多地方性、存在较大差异的实施细则去补充它,于是,补丁摞补丁的规律便发挥作用了。
2008年夏天,广东东莞发放千元“小红包”,以缓和由于CPI提高形成的生活压力,发放对象是7类困难人员和低保边缘户,其中,身份界定和收入核准发生了极大的识别困难。结果,发放资金总额比预计多了一倍多,人数也多了三分之一多,甚至个别地方村民发生械斗,有的村怕遇到麻烦就干脆不报,有的村则采取拖延的办法甚至叫停。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制度成本”案例。
社保制度统一,这是一个大趋势。美国的基本养老制度是全国统一制度;欧盟则试图采取措施尽量整合各个成员国的社保制度,让他们尽量“趋同”,以适应大市场的需要。我认为,彻底解决转续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将统筹层次提高到全国水平,这就需要深化改革现有的制度,使其适应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