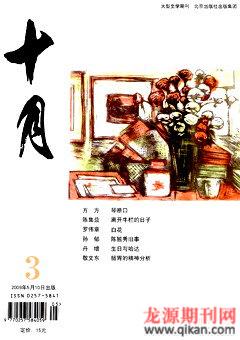白花
罗伟章
整个冬天没下过雪,可在冬春之交的时候,凤凰山上却落满白花。那天清早,空气干冷而透明,我站在清溪河北岸的厂房门口,朝南岸的凤凰山望。天地间什么也不剩了,只剩下触目惊心的白。我想那要是雪花就好了,如果是雪花,我会等天色再亮一些,领着妹妹,从晃晃悠悠的吊桥越过河流,去把雪花收集在干净的玻璃瓶里,带回家给母亲熬药。我母亲半年前得了一种怪病,镇上一个老中医说,用新鲜的雪花熬当归,喝上十天半月,病自然见好。然而雪一直不下,母亲的病也就一直长在她的身体里,吸她的血气,让她一天天枯萎。
那片白要是雪花就好了!
可我知道那不是雪花,而是普光镇洗选厂的几百号职工遗下的白瓷盆。
我父亲就在这家厂里上班。昨天晚上,他一夜没回家,母亲让我来看看。
厂房门没开。等了好长时间还是不开。
我大声喊父亲。
绿锈斑驳的铁门把我的声音堵在外面。
我又喊父亲的名字王建吉。
寒风吹来,把王建吉三个字带走,在远远的地方随手丢弃,像这三个字很不值钱。
王建吉是锅炉工,既烧开水,也烧洗澡水。他的上班时间分成两截儿,凌晨五点到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话虽如此,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的这段时间,他也有忙不完的活,他要负责把开水送到各个办公室门前的木桶里,负责把平板车拉来的煤铲成堆,之后又在锅炉房周围转悠,清扫掉任何一丝入眼的垃圾;实在没什么可清扫的,就用铁锨在煤堆上拍。在我眼里,无论怎样拍,那都是一个黑不溜秋的煤堆,可在王建吉眼里不是,他把小小的锅炉房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煤堆是这个王国里的黑珍珠。我五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妹妹,就生在家里,那时候母亲一点儿也不知羞耻,让我帮她把裤子拉下来,我看见母亲的两腿间吹出一个肥嘟嘟的亮泡。母亲热汗淋漓,说秋生,你愣着干啥呀,快去把你爸叫回来。我拔腿就跑。洗选厂在镇东,我家在镇北,并不远,二十分钟后,我跑到了王建吉上班的地方。那是下午四点左右,开水已送过,洗澡水暂时还不需要烧,因此王建吉能抽出闲暇拍煤堆。他对我的到来视而不见。拍上几锨,左右看看,上下看看,又继续拍。我说爸爸,不要拍了。他不理我,又拍了几下,才看着我笑。笑还没绽开,又觉得不该笑,把脸抹下来,厉声喝问:你来干啥?我说是妈叫我来的,妈都吹泡泡了。他听不明白,我就把妈怎样怪叫一声,然后扶着墙壁躺到床上,叫我拉下她的裤子,全告诉了他。他这才着了急,拖着锨围着煤堆转圈,说怎么办啊,这是上班时间呢!
他就像被一根链子拴住,拴在他的上班时间里。
但他夜里不上班,只是要经常开会。以往,哪怕开会开到半夜,会议结束他也回家,昨天晚上却没回来。昨天晚上我们等他吃饭,等到妹妹饿得哭,也听不见他那疲疲沓沓的脚步声。母亲心想又开会了,让我们先吃,她自己则去做第二天早晨吃的馒头。饭后,我跟妹妹就睡了。母亲也没能等住,把馒头蒸熟,就空着肚子躺下休息。凌晨四点过,母亲定时醒来,叫父亲起床,结果父亲根本没在床上。
门终于开了。守门的杨叔叔站在门口。我从他身边过,他一把将我拽住。
我说杨叔叔,放我进去,我要去看我爸爸。
他紧着脖子,弄出一口痰来,然后又把那口痰吞回去。不用看了,你爸爸今天也回去不了。他怜爱地摸着我的头,格外痛心的样子。你爸爸那人哪……他说,真不是个好东西。
最后半句话,他是咕哝出来的,但我还是听到了。
王建吉不是好东西,两年前,也就是我刚满六岁的时候,在镇上差不多就尽人皆知。
这与一个孩子有关。
那也是冬天,有天清早,王建吉烧上水,就到锅炉房外面抽烟。天地还没真正醒来,厂里静得深不见底,烟头把辛辣的寒雾,烧得知了一样叫。王建吉喜欢听这声音。这声音跟拍煤堆一样,能让他充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他接连抽了好几支烟,才回过身,打算去往炉孔里添煤。身体只转了半圈,他发现墙角堆着一团像煤炭那么黑的破棉絮。每天下班前,他都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这破棉絮是从哪里来的?厂里的工人,都来自镇上,中午在食堂吃饭,晚上都回镇上的家,只有守门的老杨宿在门卫室。当然还有一对工程师夫妇也睡在厂里,那对夫妇是从重庆下放来的,在王建吉眼里,他们高贵得很,神圣得很,绝不可能把破棉絮乱扔,更不会跑几十米远专门来扔到锅炉房外。这么看来,除老杨没有别人。门卫室离锅炉房近,再说老杨总跟王建吉过不去,好像王建吉惹了他,其实王建吉唯一惹他的地方就是上班早,五点之前就得叫醒他开门。王建吉有些怕老杨,他怕万一哪天老杨坚决不开门,让他该上班的时候却上不了班。
他没声张,弯了腰,准备把破棉絮捡拾到垃圾桶里去。
结果那不是破棉絮,而是穿着破棉袄的人。
王建吉吓了一跳,谁?
那人不回答,只把眼珠转了两下。
其实王建吉没必要问,这肯定是个讨口要饭的。很显然,他不是今天进来的,一定是昨天某个时候,趁老杨不注意时溜进了厂区,在某个角落躲着。这么冷的天,也不知他晚上是怎样熬过来的。
起来吧,王建吉说,到里面烤烤火。
他站了起来。感觉不是一个人站了起来,而是一件破棉袄站了起来。他的个子跟一米六的王建吉差不多高。王建吉说,分明知道我在里面生炉火,也不进来,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
屋子里灯光雪亮,王建吉却看不清他的脸。他脸上太脏。不过从脸部轮廓判断,他还是个孩子。
王建吉让他蹲到炉前,他没听见,只把眼睛钩子一样盯住灶台,嚅动着嘴唇。灶台上放着两个馒头。这是王建吉从家里带来的早餐。他喜欢把馒头放在灶台上烤,烤出金黄的锅巴再吃。
饿了?王建吉的喉头滚动了一下,对那孩子说,饿了就把馒头吃掉。
他扑向馒头。像馒头是活物,需要用这种姿势才能抓住。在他狼吞虎咽的时候,王建吉站在他身后,见他板结的头发无风自动,凑近了看,竟吊着成串的虱子!那些虱子忙忙碌碌地抢占地盘,一旦抢到,就屁股朝天,咬定不放。身上同样虱子成群。王建吉待他把馒头吃完,叫他把衣服脱掉。他不脱,王建吉就帮他脱。把那件破棉袄剥下后,王建吉扔到了灶台右边的大锅里。那口锅是装脏水的。从清溪河抽上来的水,开始几分钟总是又黄又脏,王建吉舍不得把脏水泼掉,就用这口闲置的锅盛起来,用于拖地。几眼灶孔间封得不严,旺盛的炉火,把那口锅也烧得几近沸腾,棉袄刚扔进去,就听到鞭炮一样的炸响。
都脱下来,王建吉说,我给你煮一煮,不然要不了两天,你就要被那些家伙咬得只剩骨头。
他还是不脱。王建吉说,脱呀,趁现在有热水,脱了去洗个澡。他站着不动。王建吉又去帮他脱。他直往后退。王建吉很感慨,人哪,在快被饿死快被咬死的时候,还不愿丢掉羞耻心。
他喜欢上了这孩子,说,你不愿意在这里脱,就到澡堂里去脱吧。
锅炉房里有道侧门,可直通澡堂。王建吉把他领进去。那时候的澡堂都是通栏,没有隔板,他背向王建吉,把衣裤脱了下来。王建吉怕
他不会用淋浴,把水给他开上,并调到一定的热度,再把衣裤拿出去扔进锅里。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炸响。
炸响停歇,王建吉把衣裤捞出来,架在炉前烘烤,之后坐下来抽烟,抽了半支,他想,那孩子身上黑成一饼,污垢不知有几寸厚呢,没人帮他抠一抠,肯定洗不干净。
于是他把烟灭掉,起身去了澡堂。
烟雾腾腾。王建吉并没征得孩子同意,就帮他抠背,抠出一槽一槽的黑泥。大概是吃了两个香喷喷的馒头又被热水冲洗,孩子酥心入骨,王建吉给他抠背的时候,他不仅没反对,还哼哼唧唧地叫。抠完了背,王建吉又给他抠前身。这次他有了抗拒,趔来趔去地躲闪。
王建吉说,你这娃娃,简直不识好歹,你以为我想给你抠啊?
他不再躲闪了,却把身体绷得紧紧的。
当王建吉去给他洗下身的时候,他的屁股猛地朝后一缩。
但王建吉还是摸到了。
天哪,是个女孩子!
王建吉呆在那里,有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呆了好一阵,他才想起应该离开。
怎么会是个女孩子呢,个子那么高,至少十四五岁,怎么没长乳房呢?
她身体板平,乳房的影儿也没有。
王建吉又坐下来,抽开始剩下的那半支烟。刚点上,老杨进来了。老杨是来接开水的。看见湿衣湿裤,他说老王,你这是……王建吉心神未定,红着脸说,一个讨口子的,身上的虱子比一个县的人还多。老杨很好奇,人呢?王建吉说,正洗澡呢。那边传来响亮的水声。老杨放了暖水瓶,要过去看。王建吉说你别去,是个女孩子。老杨张了一下嘴。意味深长地盯了王建吉一眼,大步朝澡堂走去。果然是个女孩子。老杨过来接上开水,一句话没说,走了。
上班不久,有人来把王建吉带走了。
带走王建吉的同时,也把那女孩赶出了厂门。
那时候她的衣服刚刚烤干,刚刚把王建吉脱给她的棉袄换下来,把自己的衣服穿上。
当天下午我就听人说,我父亲王建吉是流氓。
流氓自然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的王建吉被打了一顿,打得眼泡皮肿,还停发了一个月工资。
至于那个女孩,是一个多星期后被人发现的。那时候她已经死了。洗选厂与镇子之间,有个顶部平坦的土丘,从春到秋,镇上的居民去那丘上种些蔬菜,冬天没什么菜种,就让它荒着。不知道那女孩为什么要跑到荒地里去。女孩的死让我们这些小孩特别恐惧,再不敢爬上土丘去玩。直到今天,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没再上过那个土丘。——当然,它现在不是土丘了,它现在成了镇子的一部分,到处被水泥路面覆盖,路面之上,耸立着商场、酒楼和夜总会,成为镇上最热闹的去处。
难道我父亲又耍流氓了?杨叔叔既不告诉我,也不让我进去。那时候的我很不争气,动不动就掉眼泪,现在我的眼泪又下来了。自从父亲成了流氓,我自然就是流氓的儿子,我母亲就是流氓的老婆。我本人并没受到多少冲击,去年的某一天,我的同学申华(他爸爸在镇供销社卖布匹)下课后唱歌一样叫喊:王秋生的爸爸是流氓!为这句话,老师把申华叫进办公室,让他站了两节课的时间,之后,垂头丧气的申华跟随老师走上教室的讲台,当着全班同学给我道歉。从那以后,就没人敢这么骂我了。可怜的是我母亲。她本是那么孱弱的人,自从出了那件事,一旦走出家门,她就风风火火,说话做事,都显出高兴和激昂的样子。她把姿态做给人看,却快速地耗损着自己的精力。
正在我跟杨叔叔僵持不下的时候,那个从重庆来的女工程师站在远处朝这边张望。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单知道她姓江,她丈夫姓董。我也只是偶尔来厂的时候看见过他们,因为俩人虽干着工程师的活,却是被管制的“分子”,不许出厂门,上街买菜也不许。他们的菜都是厂里指定一个靠近菜场的电工帮忙买的。然而,对这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妇,我比对邻居还熟悉,都是从父亲王建吉口里熟悉起来的。王建吉崇拜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王建吉自己没上过什么学,这个世界呈现给他、让他会认也会写的文字,大概只有王、建、吉,可他迷醉于知识的香气,不仅自己迷醉,还经常把那对夫妇的事拿回家里来说。去年夏天的时候,江工程师望着漫天翻卷的金色云团,感叹一声:多么壮丽啊!王建吉听见了,问壮丽是什么意思,江解释过后,王建吉牢牢记住,回家后又兴奋地给我解释了一遍,他说秋生啊,我儿啊,我们只知道那些云是云,不知道它是壮丽,现在你知道了吗?我说我知道了。他有滋有味地咂摸着嘴,像“壮丽”这个词是可以吃的。更让王建吉震惊的是,有次董、江二人边散步边讨论问题,走到锅炉房旁边,王建吉听见董说,负数……什么?数字也有“副”的?以前,王建吉只知道党委书记和厂长有正副,从没听说过数字也有正副!他觉得自己的脑袋上被铁榔头敲开了一扇天窗,回家后对我说,秋生啊,我儿啊,既然数字都有正副,证明锅碗瓢盆也同样有正副,以前我们哪里知道呢?说不定,我跟你妈端了副碗,却让你小子占便宜端了正碗!说到这里,王建吉快乐地笑起来,嘿!嘿嘿!笑过后,他变得很严肃:儿子,你一定要好生读书,将来像董爷爷和江婆婆一样,做个明白人!这时候我母亲说话了:再是明白人又怎样呢,还不是遭整!王建吉沉默了。在芸芸众生里,他只是一个“副”数,无力改变别人的命运,唯一能做的,就是家里偶尔称两斤肉,他总是割下一点,用纸盒装了,上早班时偷偷放到工程师夫妇住的平房门前。他们不知道这是谁送的,因此带着慈爱和感激之心,面对厂里的每一个职工。
江工程师并不认识我,她看见的,只是一个流泪的孩子,于是朝这个流泪的孩子走过来。
她的个子小小的,走路的步幅也小,且如尺子量过一样均匀,肩膀微微地斜着,脖子端得很正。从大城市下放到这荒山野河的偏僻小镇,还接受管制,她却能保持如此的优雅,至今想来也是奇迹。
走到我身边,她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她的声音像少女的声音。
杨叔叔说,王建吉家的。
杨叔叔的口气里带着怜悯,好像我做了王建吉的儿子,是一件多么值得同情的事。
她说,哦,王……师傅家的呀。
杨叔叔的眼神厉害地暗了一下。
过后我才知道,杨叔叔认为王建吉已是罪人,江工程师不该再称他师傅。
我说江婆婆,我爸爸怎么啦?
她的眼里放出亮光,你怎么知道我姓江?
我说我听别人说的。
我没说是听父亲王建吉说的,我怕把王建吉的名字跟她联系在一起,让她感到屈辱。
她纤细的手在我脏不拉叽的头上揉了两下,说没事,你爸爸没事。
接着江工程师给我讲了王建吉的事。还没讲完,杨叔叔就黑着脸呵斥:该回去了,这是厂房重地,别在这里捣乱!这话是对我说的,也是对江工程师说的。在他看来,既然江工程师是被管制的对象,那么凡是正派人都有权呵斥她;没直接把她呵斥,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江工程师当然明白,但她的神情一点也没改变,轻声对我说,小家伙,回去吧。
我父亲王建吉这次又丢了一回脸。
不是跟女孩子的瓜葛,而是跟凤凰山上的
那些白瓷盆。
昨天吃过午饭不久,凤凰山突然起火。山上并不茂密的林木丛中,隐着一大片墓地,镇上的人死了,都葬到那里去。山火大概正是某人去墓地祭奠时引起的,长久不下雨,又不下雪,空气干燥,火借风势,迅速蔓延。镇上便于组织的大单位,只有洗选厂,于是政府通知洗选厂领导。让全体职工上山救火。山上有口堰塘,最好的救火工具就是盆子。几百号人跑回家,拿上家家户户都有的白瓷盆,冲过吊桥,扑趴连天地往山上爬。洗选厂唯一没上山的,就是守门的老杨——也就是说,工程师夫妇也得到了这份殊荣。当厂长在广播里通知了这件事,夫妇俩不约而同,先后跑到领导办公室请战。领导很着难,可又一想,镇上说的是“全体职工”,这两口子虽是戴罪之身,可眼下也有职工的身份。厂长准备再请示一下,书记摇了摇头;书记以前在县城当过码头工人,说话很粗,他边摇头边说,算球了,十万火急的,还请示啥呀,让那两口子去吧,看住就是!
开始,每个人从堰塘里舀了水,再跑将近五十米泼到火海里去,可很快发现这不行,一盆下去。只要不是紧跟着泼下第二盆、第三盆,火势又红彤彤地旺起来。董工程师提议,让大家站成若干列,将水传递过去。以往,董工程师和江工程师的意见,都要经厂领导批准才能实施,今天厂领导还没发话,大家就照他的意见做了。这办法很见效,经过两个小时奋战,火被扑灭了。
可问题也出来了。
人们再也认不出自家的瓷盆!
几百个瓷盆不仅颜色相同,大小、样式也几乎没什么区别,排放在一起,就像一棵树上的叶子。
当然也有能认出来的,比如哪里脱了块瓷,哪里冒了个泡,哪里凹进去哪里凸出来,这些简单的记号,来自家庭,与家里的某个成员有关,与某次争吵和笑闹有关,总之织进了家庭的岁月,浸透了家庭的气息,嗅一嗅就能认出来的。可大家都没动手去拿,自己也不好去拿了。
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觉悟。
最后,书记发话:我看这样啊,既然分不出彼此。就一个也别拿走。今天救火,大伙儿表现得都还像个人样,把瓷盆留在山上,也差不多算是给大伙儿树碑立传了。现在就下山,但下山后不要回家,直接去厂里,今天,我们不仅要把没上完的班上完,还要加班两个钟头。上山救火,是干革命,干革命是为啥?为促生产。要是干了革命却丢了生产。那还要得个卵!
王建吉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身上的补疤棉袄,救火时都没脱下来,这时候却脱下来了,裹成一团抱在怀里。他抱着这件棉袄比救火还累,因为他得花许多心思,尽量抱得好看些。
可再怎么努力,怀里的东西都不合他的心意,不是块头太大,就是棱角太分明。
——那里面藏着一个瓷盆!
好在一个队伍里,大家都在冒汗,脱掉外衣的不在少数,王建吉把棉袄抱在手上,并不显得突兀,因此没人去注意他那棉袄团起来的块头和棱角。下到山脚,过了吊桥,王建吉混杂到了队伍中间,这样镇上人也注意不到他了。距厂门大约两三百米的地方,有排歪歪斜斜的石梯通向河流,队伍开到这里,厂长让大家到河边去洗把脸。也确实需要洗洗,脸上不仅有汗,大多数人还被焦煳的柴灰弄得分不出鼻子眼睛。本来,在山上就该让大家去堰塘里洗的,但书记希望带着黑面孔下山,好让镇上人(特别是镇上的领导)切实感受一下洗选厂的英雄们,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才把火扑灭。
王建吉那时候如果冷静,大大方方地跟随队伍下河,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王建吉没法冷静,他觉得自己不是“拿”回了一个瓷盆,而是“偷”回了一个。他站在路边上,迟疑起来。后面一个焊工说,走哇建吉,为啥不走?另一个说,这家伙肯定想回去用热水洗。焊工平时喜欢跟王建吉开玩笑,说那不行,凭啥我们洗河水你洗热水?那是国家的热水!说罢将王建吉的棉袄一扯。
这一扯不打紧,棉袄里的瓷盆露出来了!
王建吉像搂着一块烙铁,手不是松开,而是猛地朝地上一掼。
瓷盆迫不及待地从棉袄里逃出,高高兴兴地在路上滚了半圈,才铿的一声平稳下来。
四周很静,只有河水溪沟一样淙淙流淌。
静默了许久,书记说,王建吉,哼,龟儿子王建吉!
这不是偶然的!厂长跟了一句。
王建吉如果保持沉默,或者马上低头认错,事情恐怕也不会那么严重。
可是他既没保持沉默,更没低头认错。
他说,我拿去的是个双料盆儿,拿回来的是单料盆儿。
(双料厚,经用;单料薄,容易损坏。)
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明明错了,却不认错。
回到厂里,大家没有“促生产”,而是继续“干革命”。革命的对象就是王建吉。王建吉的骨子里扎着一块毒根,如果不把它挖出来,不仅害了他本人,还会传染给别的职工。厂里在篮球场上开大会,搬出一口长条形木箱做了台子。王建吉被押到那台子上。刚站上去的那一刻,他感到身上涌过一阵暖流。这股暖流是工程师夫妇传递给他的。自从二人来到这里,每次开类似的大会,都要搬出这口木箱,他们都自觉地站到木箱上去。王建吉学夫妇俩的样,佝腰低头,双臂鞭子一样垂着。与工程师夫妇不同的是,他们站上来,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而王建吉的头上,戴的是那个被他“偷”回来的白瓷盆。主持会议的是办公室主任,他让王建吉自己先挖那块毒根。
这是通常的程序,以前对工程师夫妇,也是这么做的。
王建吉平时在单位上少言寡语,都以为他放不出几个响屁,哪知他口若悬河,说了好长一串!
不过,他没说几句,台下就发出了笑声。
他说的那些话,全是工程师夫妇以往说过的,他背下来了,背得滚瓜烂熟。
两年前对一个讨口要饭的女子如何偷偷摸摸耍流氓,今天又如何偷了瓷盆,他竟一个字也没提!
主持人严肃地制止了大家的笑声,之后狠狠地瞥了工程师夫妇一眼。夫妇俩今天没站台子,但也没资格坐,肩并肩地立在台下一侧。他们的腰弯得很深,坐在台下的人,也只能看见两颗白得晃眼的头,看不清他们的脸。主持人瞥了他们一眼,并没对他们说什么话。他早就厌烦了自己说的那一套,只希望快些完成任务,好让自己松口气。现在,可说任务已完成一半(另一半是整理材料)——一个锅炉工,一个文盲,偏把自己标榜成反动学术权威,这比偷盗严重得多的罪名,可不是别人加的,是你王建吉自己加上的,那么好,他就可以简便地以这样的罪名给王建吉定性;至少,他是中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流毒。
晚上,王建吉被关在堆放杂物的库房里,等候发落。
材料很快整理出来,送到了书记和厂长的手里。书记去问厂长,你看呢?厂长没回话。书记说,分明就是个文盲,却说成反动学术权威,报到上面去,不是闹鸡巴笑话吗?
其实厂长也是这意思。两人一合计。把材料压下了。
但王建吉并非没付出代价。他被关了两天才放回家,工资也降了一级。
王建吉的工资是我们家唯一的果树,渴了饿了,都只能望着它;我和妹妹上学,还有给母亲治病,也必须靠它。他的工资本来就那么少,
少得要用那笔钱来安排一家人的生活,比挣下那笔钱本身还难。现在降了一级,我们家的日子,只能一圈一圈地拧紧螺丝。母亲是怎样拖着病体,阻止螺丝继续拧紧以防滴水不漏的?我不知道,那时候也从没去想过。偶尔,母亲从菜场回来,还从包里掏出两颗糖,是那种用花花绿绿的纸包着的薄荷糖,给我和妹妹一人一颗。我们先把糖纸舔得寡淡,再把糖果小心翼翼地放在舌尖上。这时候,母亲神态安详,根本看不出她有病。她像一架固执的弹簧,随时准备承受生活之重——可她的那颗心,却在被迅速蚀空。
她的丈夫、我们的父亲王建吉,实在太不争气了。上次跟那个女孩子的事,她打心眼里是相信王建吉的,这从她从没因此跟王建吉吵过,甚至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可以得到证明。听说那个女孩死在了土丘上,她还红了眼圈,嘴唇张开,急促地呼吸。她之所以不惜体力在人前风风火火,把激昂的样子做给人看,不是不相信自己丈夫,只是她相信丈夫,却更相信集体的力量。那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她想以自己的方式与那种力量对抗(其实,在本质上是对那种力量的顺从,只是母亲自己认识不到);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取得了成功,至少让那些希望在她身上表现自己怜悯心的人,说不出话来。可这次就不同了,王建吉明明偷了一个瓷盆一在母亲的观念中,王建吉的行为同样是“偷”而不是“拿”——几百双眼睛盯住的,她还能在人前把高兴的样子做出来吗?
真要那么做,就是不知羞耻。
家里穷,这是事实,但另一个更大的事实在于,不是天底下所有的穷人都去偷;自古以来,偷窃都是可耻的,不仅打自己的脸,还打祖宗八代的脸。母亲抬不起头。当我和妹妹不注意的时候,她常以怜惜到骨髓里去的目光看我们。我和妹妹黯淡的前景,在她眼里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
她跟丈夫说话的时候明显减少。
王建吉去问她病情,她总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反正都这样儿了。
随后背过脸去。
她背过脸去的时候,王建吉就把头低下了。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头发变得那么少,像被拔过几遍的菜地,能轻易瞧见地皮的亮光。他比我母亲大了差不多十岁,但现在也才刚上四十,头发不该掉得这么厉害。
单位上同样很少有人跟王建吉说话。不过这没什么奇怪的,他守着锅炉房,守着煤堆,以前跟他说话的就不多。只是现在变得更少。没把他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论处,厂里无一人去追究。大家都知道他不够格。要说反动,他是够格的,一切与集体意识背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反动的,这没什么好说;但权威他就不够格了,何况是学术权威。那时候学术不是个好东西,知识也不是个好东西,但奇怪的是,要是谁比别人多认几个字,却很喜欢拿出来炫耀。可以炫耀于人的,王建吉沾不了边,他只会耍流氓,只会偷瓷盆。
尽管放王建吉回家之前,山上的瓷盆就一个也不剩了,但没有人去过问。
有什么好过问的?你又去过问谁?记住王建吉是小偷就行了。
王建吉处在集体的蔑视里,可他似乎并不因此而不悲伤,依然准点上班,空闲下来,依然专心致志地拍煤堆,远远地望见工程师夫妇,依然深怀景仰。
只在夫妇俩从他视线里消失之后,惆怅才泛上他的心头。他坐下来,想抽支烟,伸手去兜里掏,掏了衣兜又掏裤兜,却掏不出一支烟来。自从降了工资,他就不再买烟了。
他把头低下去,露出亮光光的头皮,自言自语:我拿去的是个双料盆儿,拿回来的是单料盆儿……
不悲伤,或者说不做出悲伤的样子,既是他的尊严,同时也是跟工程师夫妇学的,可这时候他也犯糊涂了:当那夫妇俩离开人群之后,也从来没为自己悲伤过吗?他们都还没上六十岁,头发却自得那么干净彻底,白得像蚕丝一样,难道不能泄露一点他们心里的秘密吗?
有天中午,工程师夫妇饭后散步,走到锅炉房外,见王建吉在拍煤堆,两人对视一眼,又对视一眼。之后,江工程师喊他了:王师傅。
王建吉停下手。
江工程师问:你儿子呢?
王建吉受宠若惊,江工程师竟问起他儿子!
他乐呵呵地说,我儿子在学堂里。
江工程师说,晤……你儿子,真乖!
那天下班后,王建吉是跑回家的。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江工程师表扬他儿子的话,说给他儿子听。
可就在这一天,我母亲死了。
母亲死后没几天,就下起了雪。
雪片扯天扯地,把清溪河都下白了。只一会儿工夫,积雪就从凤凰山奔跑下来,舒舒坦坦地横躺在街面上。这时候春天已走了很远的路,谁也没想到会下这么大的雪。
多年以后,我利用春节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我的归期,从清早就坐在门口迎接我,直到下午三点过才把我接住。这时候的父亲王建吉,已老得不成样子了,头发自然更少,灰扑扑的,干枯而凌乱;从凳子上起身,也要扶着门框,腰再也站不直。
哪怕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动作,也被岁月没收,不再属于他了。
他的这种老态,浓缩了他的全部生活。
母亲死后,父亲没再续弦。尽管有几个寡妇都愿意跟他过日子,他却一个也没答应。他害怕将来的继母对我和妹妹不好;不是打我们骂我们克扣我们吃穿的那种不好,而是不让我和妹妹读书。家里穷得一片多余的纸也没有,还读什么书呢?关键是读书有什么用呢?这是最通常的也是当时最合情合理的逻辑,但锅炉工王建吉却不按这逻辑行事。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工程师夫妇回了重庆,听说是得到解放了,王建吉让我们读书的劲头也就更大。妹妹上高中那年,王建吉退休,他的退休金无法把儿女的学业支撑起来(那时我是大一学生),便跟随民工潮南下广东,在建筑工地上推斗车。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已基本上不包分配,找工作的难度也在逐年增加,新的读书无用论,已不是在暗流里涌动,而是被许多人接受了。知识虽不再反动,却也说不上有多少益处:读书不就是为了挣钱吗,现在打工也能挣钱,等你又花钱又误光阴地念完大学,却成为待业青年,结果还比不上一个打工仔!每当有人拿这样的话去劝王建吉,王建吉都笑眯眯地摇头,那样子仿佛是说:你们不懂!他在广东一直干到妹妹读大三,我一再表示我有能力把妹妹供毕业,他才肯回到镇上的家里……
往年的除夕,都是我一家人,妹妹一家人,围着父亲团团转,今年就冷清了,只我一个人回来。我儿子下半年中考,寒假要补课,他妈妈也就动不了身;妹妹半月前随一个科研队去了巴基斯坦,妹夫便没心思带着孩子往乡下跑。父亲明显很失落。抓住这机会,我再一次说:爸,你去跟我住,或者跟妹妹住,省得一个人寂寞。他照旧不同意,说我在这里住惯了。你去城里待一段时间,同样能习惯。他低头不语,过一阵说,你们妈在这里,总不能撂下她不管,总得留个人守住她。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母亲埋在凤凰山上。
中午,做好年饭,我跟父亲去给母亲上坟。我们的午饭做得晚,别的人家都来墓地给自己亲人上过坟了,山上有种凛然的清寒。我把酒肉放在母亲墓碑前,点上鱼蜡柏香,烧过纸钱,磕几个头,上坟的仪式就算结束了。天上飘着
雪花,风又很大,我怕父亲冻着,就去搀他回去。
父亲坐在母亲墓前干净的枯草上,说不急,再坐一会儿。
事实上,我也希望多陪陪母亲,就坐在迎风的一面,把风为父亲挡住。
我没想到父亲是要在这里给我谈一件事的。不仅给我谈,也给母亲谈。
事情关乎几十年前的那个白瓷盆。
父亲说,我拿回那个盆儿,不是给我自己的,是想给你董爷爷和江婆婆的。
我像被扎了一刀。你……
父亲挥手不让我打断他,清了清嗓子,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有天清早,他给工程师夫妇送肉去,见里面亮着灯,听见夫妇俩都起了床,就好奇地往门缝里瞧。那间平房的门龇牙咧嘴,里面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江工程师洗了脸,又往盆里添了热水,递给丈夫说,你身上那么痛,烫个脚吧。董工程师接过盆儿,把脚伸了进去。那屋子里只有一个盆儿,看来他们不仅用它洗脸洗脚,还用它洗菜。现在盆儿留在山上了,今后怎么办?让老张(帮工程师夫妇买菜的电工)帮忙买么,那可不放心!他买的菜报价很高,其实全是趁散市的时候去捡黄叶子,不知贪了两个好人多少钱。真要让他买盆儿,他很可能只从家里拿个旧的去;说不定把钱贪下后,连旧的也不拿呢,反正他知道工程师夫妇又不敢去追问他。
父亲说完了,说得很平静。
我用力地扯着地上的枯草。这些事,你为什么当时不说出来?
哪能说呀!父亲惊诧地看着我,要是说了,那些人就会冤枉你董爷爷和江婆婆,说我偷盆儿是受了他们的指使,那就把他们害了,我就丧天良了。我给你妈也不能说!
我继续扯着地上的枯草。草根牢牢地生长在大地上,宁可断掉,也不愿被连根拔起。
父亲伸手抚摸着母亲浅灰色的墓碑,又说话了,声音很低,低得像耳语。
你妈跟了我,受一辈子苦……要不是我,她死不了那么早。
几十年来,我也是这样想的。
此刻,我知道父亲很难过,但我心里乱纷纷的,不知道怎样安慰他。
一阵大风刮来,父亲别过脸,把风让过去,之后认真地问我:秋生,你知道什么是壮丽吗?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数字也有正负吗?
我说我知道。我还知道得更多。
父亲异常严肃地盯住我:你敢说。你比董爷爷和江婆婆知道得还多?
是的爸爸,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女儿,肯定都比他们知道得多,多很多!
父亲缓缓地把头扬起。雪花飘在他脸上,被泪水烧化。倏然融进密布的皱纹里。
责任编辑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