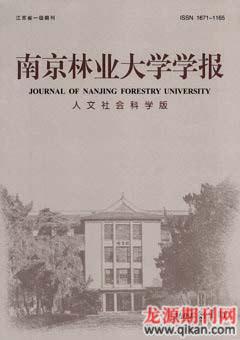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德哲学审思
陈爱华
摘要:施密特在阐释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过程中,揭示了自然的社会伦理本质,生成了一系列自然与社会之互维性的问题式,其中包括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自然概念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质;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机制。这一思想不仅为我们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奠定了道德哲学基础,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伦理观的生成奠定了学理基础。
关键词:自然;社会;中介;施密特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1001911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左派代表人物,施密特在阐释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过程中,有其独到的理论视角即试图从马克思中期与成熟期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和1857-1859年的“手稿”入手,并据此对当时西欧流行的具有存在主义与神学色彩的种种倾向,即想把马克思的学说还原成(在结果上)以非历史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的“巴黎手稿”)的异化问题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倾向提出挑战,因而极具战斗性,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更重要的是,施密特在阐释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过程中,揭示了自然的社会伦理本质,生成了一系列自然与社会之互维性的问题式,其中包括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理论前提: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人与自然的互维性:自然是人类实践的要素,自然的社会中介性。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互动机制:“自然的人化”和“人被自然化”,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进而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德哲学基础。
一、自然的社会—历史性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的序言中阐发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规定性,进而揭示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理论前提。他指出: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
(一)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历史生成
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生成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与黑格尔的自然概念的影响。
首先,施密特考察了费尔巴哈与黑格尔自然概念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从自然概念开始的。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然对理念来说是一个派生的东西,“自然在时间上是最先有的东西,但绝对先在的东西却是理念;这种绝对先在的东西是终极的东西,是真正的开端,起点就是终点”[1]10。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可以理解为关于他在形式中的理念科学。在自然中,理念以尚未纯化为概念的直接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它是处于无概念性中所设置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自然不是在其自身中自我规定的存在,而是呈抽象的一般形式的理念为复归其作为纯粹精神的自我所必须经过的外化阶段。黑格尔还认为,在自然逐渐摆脱其外在性而产生心灵的时候,能从自然推衍出一般自然的非物质性,一切物质的东西都被在自然中起作用的自在的精神所扬弃,由于这种扬弃是在心灵中完成的,因此,心灵就体现为一切物质的东西的观念性、一切非物质性。与此不同,费尔巴哈概括了其“否定一切讲坛哲学”纲领:“哲学家必须把人还没进行过哲学探讨的东西,也就是同哲学相对立的东西,把反对抽象思维的东西,从而把在黑格尔体系中一切被贬低到注释地位的东西,提升为哲学的正文。”[1]11-12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哲学必须不是从自身开始,而是从它的对立方面、从非哲学方面开始。
其次,施密特阐述了费尔巴哈与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异同。一是费尔巴哈上述关于哲学必须不是从自身开始,而是从它的对立方面、从非哲学方面开始的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曾说过:“一切科学都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一门科学在它不能找到自己的自然基础之前,只不过是一种假说。”[1]12二是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尽管费尔巴哈深刻地指出,“所谓实在,或者所谓理性的主体,仅仅是人。是人在思维,既不是自我在思维,也不是理性在思维”[1]13,他还认为,“实在的东西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而只能以片段的形态表现在思维中”[1]14。然而,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和人类以前的自然密切相关;自然作为整体,是非历史的匀质的基质,因而是一成不变的原始自然,自然具有原始直接性。与费尔巴哈相比,马克思则前进了一大步。因为马克思不仅把感性直观,而且还把整个人类实践导入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构成环节,把自然消融于主客体的辩证法,将自然看作人类实践的要素,又看作存在万物的主体,从而既克服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抽象性,又克服了费尔巴哈自然观的直观性,生成了非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再者,施密特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提出非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其批判黑格尔的自然观和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密切相关。黑格尔把存在于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这个第一自然,说成是一种盲目的无概念性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当人的世界在国家﹑法律﹑社会与经济中形成的时候,是“第二自然”②,是理性和客观精神的体现。马克思的看法与之相反: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本身具有适用于第一自然的概念,应把它作为无概念性的领域来叙述,在这无概念性领域里,盲目的必然性和盲目的偶然性相一致;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本身仍是第一自然,人类终究不会超脱出自然历史。③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对一切直接事物的中介性思想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在把主体和客体都看作“自然”的范围内,坚持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一元论。同时,“马克思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由此克服了这种一元论的抽象的本体论性质。因为,人作为中介的主体,作为从有限时空上规定了的人,他们本身也是那以他们为中介的实在事物的组成部分,所以关于直接事物的中介事物的特点”。由此,施密特风趣地说,在马克思的版本中不会导致唯心主义。须指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自然直接性和费尔巴哈所说的相反,它是打上社会烙印的,并且对于人及其意识来说,它仍然保持着其在产生上的优先性。因而,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在于从世界自身来说明世界”[2]365。 这种自然概念在下述意义上是“独断的”[2]18,即它从理论构成中,排除掉任何被马克思称之为神秘主义或意识形态的东西。但同时又有宽宏大量地非独断性,因为它防止自然受到形而上学的神化,或者使之免于僵化成终极的本体论原则。这种自然是认识的唯一对象。一方面它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同时,它又依附于这些形态而出现于思想和现实之中。人们总是以他们和自然斗争的形式为模式,从其形形色色的文化领域来理解世界,因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样,把一切关于超自然存在的领域的概念,都看作是对生活的否定结构的反映:历史的运动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一种相互关系。
(二)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
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理论前提。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就是说,他把自然看成从最初就是和人的活动相关联的。他有关自然的其他一切言论,都是思辨的、认识论的或自然科学的,都已是以人对自然进行工艺学的、经济的占有之方式总体为前提的,即以社会的实践为前提的”[1]2-3。施密特指出,马克思在分析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现状时发现,人与社会如同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在用来对付自然的生产力方面,人依旧没有成为主人,这些生产力难以作为固定的形式,作为同它的创造者自己的本质相对立的“第二自然”被无法理解的社会组织起来。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认为人与社会如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人所把握、支配了的社会过程,依然是一种自然关系,因为在生产力的一切形态中,人的劳动力“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3]15。以此为切入点,施密特从“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关系中,阐述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首先,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自然的各种形态彼此合乎规律地产生是不证自明的。它们并不从所谓先于人的总体意义的概念出发。而黑格尔和18世纪一般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看成是互不关心的存在物之物质分离状态,在他那里,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史并不存在:“思维的考虑必须放弃那类模糊不清的﹑根本上属于感性的概念,例如,尤其是所谓植物产生于水,尔后较高级动物的组织产生于较低级动物的组织等等观念。”[4]施密特指出,黑格尔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他以抽象的唯心主义考察自然。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构成形式逻辑与反思哲学的特征。尽管黑格尔在自然的图像中得到了概念的具体化,但是其逆论又使自然概念的一个抽象物,自然受到拙劣的报复。[1]36注 与之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正如不存在那种必须从“精神史”来探究的、采取观念衍生形态的纯粹内在一样,也不存在作为自然科学认识对象的完全不受历史影响的纯粹自然。作为合规律的、一般领域的自然,无论从其范围还是性质来看,总是同被社会组织起来的人在一定历史结构中产生的目标相联系。[1]45人的历史实践及其肉体活动是连接这两个明显分离的领域的愈趋有效的环节。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迄今的人类社会历史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来看待[5]12,它首先具有这样的批判意义:“经济学规律,在一切……无计划生产中作为人对它们没有支配力的客观规律,采取自然规律的形态与人们对立。”[6]马克思认为,尽管人从漫长的史前史中获得了经验,即取得一切技术上的胜利,但最终获胜的依然是自然,而不是人。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那样,一切技术上的胜利,是一种作为社会控制不了的﹑“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部机器,只不过是把自己撕成碎片的痛苦的自然”[7]。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自然与社会的绝对分离,因而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不存在根本方法的不同。例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合人类史,但这两方面史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合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①“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8]44是意识形态学家们制造出来的,这是由于他们从历史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的生产的关系。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时说,自然和历史不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8]49。在人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8]49。
这里须明确一下马克思关于“历史”内涵。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不断地重新开始的各个个别过程的连续,它只有依靠关于世界片断的哲学才能把握,而这种哲学有意识地放弃了仅从一个原理出发去进行完整无缺的演绎这一要求。理解了以往人类历史的人,决不应据此以为理解了世界的意义。施密特以马克思对特定社会,即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分析,阐述马克思“历史”概念的特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达尔文的学说一样,它并不是对总体的说明,倒是根据事实来把握历史过程,而不诉诸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正象……种变说所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高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再者,施密特指出,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十分关注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社会规律的特殊性。马克思尤其注意到他的理论与达尔文的关系:“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5]409-410(注)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因而不允许人们像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那样,把大自然规律简单地搬到社会关系中去。马克思在致库克曼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批判了F•A•朗格企图以抽象的自然科学公式,忽视人类历史的丰富内容:“朗格先生……由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玈truggle Forlife即‘生存竞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或者更确切一些,人口过剩规律。”
二、自然与社会的互维性
如前所述,施密特认为,马克思不仅把感性直观,而且还把整个人类实践导入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构成环节,把自然消融于主客体的辩证法,将自然看作人类实践的要素,又看作存在万物的主体;不仅揭示了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十分关注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社会规律的特殊性。从而既克服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抽象性,又克服了费尔巴哈自然观的直观性,还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由于将自然看作人类实践的要素,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既独立于人又以人和社会为中介,这样,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便结成了一定的伦理关系。自然的伦理意蕴即表现为,自然与(人)社会之互维性的问题式便由此生成。
(一)自然是人类实践的要素
首先,在施密特看来,自然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关注,在于它是人类实践的要素。这是自然与(人)社会之互维性的问题式生成的前提。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只要自然界在尚未被加工时,它在经济上就是毫无价值的,“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于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不过是物化劳动”[9]337。马克思在批驳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时,他抨击自然无需人的中介而自在存在的观念;在批驳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整个德意志唯心主义的主观概念时,他批判了使意识及其机能独立于人的观念,认为进行中介作用的主体不只是精神,也包括作为生产力的人;最后,他在黑格尔的绝对、即实体与主观的统一之上,看到了这两个因素所结成的统一不是具体的、历史地产生的,而是“被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统一。正如自然不可能脱离人那样,反过来,人和他的各种精神活动也不可能脱离自然,人的思维能力是一种自然史的产物。因此,马克思说,思维过程就是自然过程:“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①
其次,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自然与(人)社会之互维性的问题式不仅体现在与人相关的自然,而且还渗透在先于人类和社会的自然的存在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先于人类和社会的自然的存在的问题不是“抽象地”提出来的,它们总是已经以对自然作理论的和实践的把握之一定阶段为前提的。因此,在被称之为绝对第一的基质之中,一切都已经同在理论的、实践的活动中产生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所以它们绝不是绝对第一的东西。施密特援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问题时的论述,进一步证明这一思想。马克思说,尽管“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23-24。但是,在人所创造的社会史之类的对象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即使有种种形式上的不同,实质上依然是相互吻合的。与此相反,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去对自然进行解释,这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对自然的漠视。因此,关于人和自然的“生成”[5]84的问题,与其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历史的社会的问题:由于在马克思看来,“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类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5]84-85。既然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于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复次,自然与(人)社会之互维性的问题式表明,人对于自然的关系是以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前提的,所以劳动过程作为自然过程,它的辩证法把自己扩展成为一般人类史的辩证法。[1]58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一切自然存在总是已经从经济上加过工的,从而是被把握了的自然存在;另一方面,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自然科学上,自然的概念都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而对自然起作用。由于自然产生出作为意识活动之主体的人,自然才成为辩证法的,人作为“自然力”[5]202是和自然本身对立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人那里相互发生关系,自然是劳动的主体——客体。由于人逐渐地消除外部自然界的疏远性和外在性,使之和人自身相作用,为自己而有目的地改造它,自然辩证法才存在于人变革自然的活动中。① 在劳动中,人把自己对象化,但并非用劳动去“设定”自然的对象性本身,对于马克思来说,中介不同于设定。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被设定的,正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来的,所以它就通过对象而被设定。所以,在设定的活动中,它不是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跌进创造对象的活动,而不过是证明把对象的产品作为该对象的活动、作为对象的自然本质的运动而已”②。
再者,正如劳动是形式的“价值创造者”一样,自然物质是实质的“价值创造者”[1]63。因此,自然与(人)社会之互维性的问题式蕴涵于劳动的性质中。自然物质与劳动的分离绝不可能是绝对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设法把劳动、因而把来自活动的人的东西,同由自然赋予的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基质”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可是,如果说到感性世界的整体,那么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实践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劳动产品的完成,我们一般地并不能断定人与自然物质在量与质上占有怎样的比例。说这种关系在形式上并不能断定,是因为这些因素的作用过程成为辩证法的过程。[8]48-49如同还未被人所渗透的自然物质,在其原始的直接性上和人对立一样,劳动产品、劳动加工自然物质而构成的使用价值的世界——人化的自然——一旦作为客观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就和人相对立。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的以及实践的东西,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被人加工过的自然物质,依然是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事物”[5]87。
最后,在作为劳动结果的已完成的事物中,以劳动为中介的运动消失了,但自然与(人)社会之互维性,依然通过作为其结果的事物,在进入下一个劳动过程的时候,再次被降低为劳动这个中介运动的单纯要素中显现出来。在一个生产阶段中是直接的东西,在另一个生产过程中是被中介的东西。“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推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个使用价值,以前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5]20
(二)自然的社会中介性
施密特指出,马克思一开始就承认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以笔者之见,这正是自然与(人)社会之互维性的问题式的核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不是理论关系而是实践关系,无论从自然科学的考定范围还是从它的方法论,甚至从它的往往称之为事物的内容而言,它都是由社会所规定的;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从直观唯物主义转变为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强调感性世界是工业和实践的产物,但这个以社会为中介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在历史上先于一切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世界,因而,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即马克思又坚持了自然界及其规律对于社会中介要因的先在性。作为自然与(人)社会之互维性的问题式的核心的自然的社会中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施密特认为,自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中介的东西。为此他援引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论述:“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秘密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自然科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甚至连最可靠的感性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与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会看来,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8]49-50与此同时,这个以社会为中介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在历史上先于一切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世界。因此,尽管承认了社会要因,“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8]50。但是,这种区别(即人类社会以前的自然与社会中介过的自然间的区别),只有在人被看成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在施密特看来,“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1]2。由此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的理论(即“相互中介论”)。他认为,马克思的中介理论是批判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等人的自然观的产物,是新唯物主义自然观区别于其他自然观的一个本质特征。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把整个人类实践导入认识过程,将人和自然看作实践的辨证要素,才使自然观达到具体性。虽然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样讲“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但他批判地保留了这种优先地位只能存在于中介之中的一切说法。马克思不是从本体论、无中介的纯客观意义上来理解自然的,他将自然既看作存在着的万物的总体,又看作人的实践要素,在工业中,人与自然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达到统一。
其次,施密特指出,现实中出现的一切目标和目的,都可追溯到适应境况变化而采取行动的人,离开了人就没有任何意义。[1]26只有黑格尔的精神之类的主观扩大到无限世界去时,它的目的才能同时也成为世界自身的目的。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有限目的论的观点”是受到限制的,应在绝对精神的理论中遭到扬弃。与此相反,马克思不知道在这世界里除了人所规定的目的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因此,世界包含的意义无非就是人通过调节自己各种生活条件而达到目的,除此别无他义。“历史能够从一个较恶的社会到达一个较善的社会,历史在其进程中还可能达到一个更善的社会,这是一个事实。然而,历史的道路是在充满了个人的痛苦和悲惨中前进的,这又是另一个事实。在这两个事实之间有一系列解释上的联系,但没有任何辩解的意义。”[1]92因此,甚至一个更好的社会到来的时候,也没有理由替达到这个社会所经历的充满人类痛苦的过程去辩解。在此基础上,施密特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的中介理论是马克思对唯心主义中所包含的真理的批判性的吸取。马克思并不像费尔巴哈那样抽象地责难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是看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下所包含的“世界以主体为中介”的合理性成分。马克思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生活过程联系起来,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自然主义一元论的抽象性;马克思坚持作为中介主体的人是实在的组成部分。所以,他关于直接事物的中介性观点并不导致唯心主义。
三、人与自然和谐的互动机制
施密特认为,要理解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重要的是阐明关于在每时每刻形态中的物的存在的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具体辩证法”[1]64。他着重从马克思的后期成熟著作《资本论》及其几个准备性的手稿来展开马克思的中介理论的内容,进而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互动机制:一是“自然的人化”和“人被自然化”;二是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性。
(一)“自然的人化”和“人被自然化”
施密特揭示了马克思关于以“自然的人化”和“人被自然化”为内容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实际上,这一思想是关于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互动机制的深刻揭示。
首先,施密特分析和阐述了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由于受费尔巴哈和浪漫派的影响而提出的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自然的人化”和“人被自然化”的思想。马克思还提出了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这样一个公式。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马克思曾作了这样的概括,自然作为“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0]49,自然作为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10]49。在有生命的自然中,同化过程一般使无机的东西转化成有机的东西;同样,在劳动中,人使上述的“无机的身体”和自己同化,使自然越来越成为自己自身的“有机的”构成要素。 “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0]49但是,这只有在人自身直接属于下述的自然时才是可能的:这种自然绝非仅仅是和他自己的内在性对立的外部世界。
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还将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动物在自己占有的对象世界中,被束缚在自己所属类的生物特性中,因而也被束缚在这一世界的一定领域中;相反,人的普遍性的特征在于至少能够占有整个自然,人既然进行劳动,就使“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0]49。自然作为劳动的成果以及出发点,是一个“无机的东西”,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生产时和动物相反,能够“自由的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10]50,这是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为了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0]50-51因而,说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句话不只是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尤其具有社会意义,人的生物的类生活依靠社会生活过程才开始成为可能。
其次,施密特还解读了马克思后期成熟的经济学著作,在他看来,“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概念就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10]78。物质变换概念是“马克思对自然整体内部与社会相互渗透关系的确切的最好表达”[10]79。因为马克思认识到,自然和人的斗争可以改变,但不能废除。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非思辨的、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物质变换”这一唯物主义概念来对此加以论证。因为这里“物质变换”以“自然的人化”和“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一方面,由于人把自然物中“沉睡的潜力”解放出来,就拯救了它,把死的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延长了依据自然史产生的自然对象的系列,使之在质的最高阶段上延续。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造过程。这种变革的实际不只具有“社会的”意义,而且具有“宇宙的”意义。[1]76另一方面,正如不依赖于人的自然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能量的转换一样,人的生产也不能置诸自然的关联之外,自然和社会并不是僵死对立的。在马克思看来,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的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活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所以,人使他的本质力量和被加工的自然物同在,这就是人被自然化。[1]77
(二)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
“自然的人化”和“人被自然化”作为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互动机制直接体现,还深深地蕴涵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互动之中,主要表现为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
首先,施密特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独特地发现了物化在商品形式中的历史关系,并力求从现实经济外观去发现隐藏在其中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这实际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互动的机制的本体维度。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关系以自然为中介,反之亦然。这些关系总是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1]66。而在《资本论》的草稿中,马克思则“更多地使用哲学范畴,使得自然存在的独立于人和依存于人的关系这个难题得以展开”[1]69。他指出,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社会作为整个现实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马克思把“一切自然存在”都看作人的劳动加工过的、滤过的,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强调人和自然以实际为中介的高度统一。自然是社会范畴,反过来社会也是自然范畴,自然和人、自然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因而,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具有“社会历史性质”。从这种立场出发,施密特既批判恩格斯,又批判卢卡奇。他说恩格斯试图把辩证法扩展到人类以外的自然界,这有巨大的影响,但恩格斯将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使他们成为两个分离的领域,背离了马克思的自然理论,倒退到独断的形而上学;而卢卡奇首先要求把辩证法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正确地指出自然及一切对自然的意识受历史的制约,这是他的功绩,但他把自然消融到社会历史中,就陷入新黑格尔主义的“现代”观点中去了。
无论在《资本论》的“草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讲到可被占有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和本体论有细微差别的术语。例如。他在“草稿”中把土地称作“实验场”[9]491、“原始的工具”[9]500、“原始生产条件”[9]492,在《资本论》中称作“原始的食物仓”、“原始的劳动资料库”[5]203。与此相关联,“巴黎手稿”中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主题,在“草稿”中也以相当注目的具体形式再次表现出来。而且出现在对财产的发生史进行分析中:“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的非经济起源(他这里讲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那种东西,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象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的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9]487
其次,施密特反复强调,既然一切自然都是实践的产物,那么,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去看待自然。这体现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互动的机制的实践维度。虽然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仍然保留着唯物主义的优先地位,但这种优先地位也只能存在于人的实践及人的意识对自然的“中介”之中。人和自然都是实践的要素,随着工业的发展,自然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不断降低,它的客观性“逐渐纳入主观性之中”,凡是能被认识的东西,都是主体所创造的东西,因此,唯物主义才不应该以抽象的物质,而应以实践的具体性作为自己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就生产而言,总是社会的,它总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①,那时,每个人直接际遇到的是各自互不关心地从事自己的私人劳动:他们生产出来的物的使用价值,是无交换地在 “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的”[5]100。与此相反,互不相关地从事的私人劳动,其社会性质乃是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中、即在社会的总过程中才是明显的。
再者,施密特还发挥了马克思关于自然史和社会史统一的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互动的机制历史维度。他说,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是从严格的必然性来看待历史过程的,是与先验构成和心理解释无涉的。当然,马克思承认社会规律的特殊性,他和恩格斯一样认为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人创造的,前者则不然,“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史和人类史则是在差别中构成统一的,他既没有把人类史溶解在纯粹的自然史之中,也没有把自然史溶解在人类史之中”[5]38。因此,一方面要看到社会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自然史过程和社会史过程之间的种种差异。“总之,只有在有意识的主体创造的人类历史为前提的时候,才能谈论历史,自然史是人类史溯望的延长。”[5]39从这种立场出发,施密特批评考茨基,赞扬科尔施,认为前者的《唯物史观》一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而后者则是为数不多的正确理解了自然和历史的复杂辩证法的作者之一。施密特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关系当作自然和历史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加以考察。他批评自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以来的将这两种科学割裂开来的做法,认为这种割裂是以把实在分成自然和历史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作为前提,而马克思坚持自然和历史的统一,说在人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自然和历史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学家制造出来的。因此,马克思坚持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统一,认为只有一门科学即(包含自然史和人类史),“属于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科学”“都将成为一门科学”。
总之,施密特通过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阐释,揭示了自然的社会伦理本质,其中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德哲学维度:自然概念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质;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互动机制: “自然的人化”和“人被自然化”,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揭示了自然与历史是相互渗透和相互中介的;自然与社会、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没有离开人、社会或历史的纯粹客观性的自然,自然是被人或社会所滤过的,它是实践的要素又是实践的产物。
参考文献:
[1]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欧力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薛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9(注释).
[5]马克思.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08.
[7]霍克海默尔•W•阿多诺.启蒙德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42.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马克思.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37.
[10]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 お
(责任编辑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