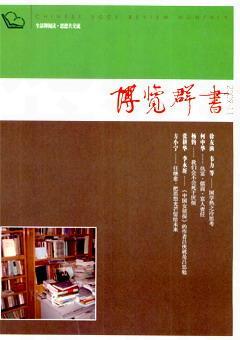父亲郑振铎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尔康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我父亲郑振铎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完成的作品。这是继他的世界文学史巨著《文学大纲》(1927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的又一部弘篇巨著。在这部书里,他首次把历来不为文人雅士们所重视的弹词、宝卷、小说、戏曲等不能登入文学殿堂的所谓“俗文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进去,以他独到的见解,为“俗文学”正了名,为“俗文学”争得了文学殿堂中的应有席位,堪称为“前无古人”之壮举。书一经问世,便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父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便已开始。当时他已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中世纪第三篇上册”(1930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由于编辑工作杂务太多,况且那时的《小说月报》其实很长时间都只是他一人唱“独角戏”,后来才来了徐调孚做他的助手,所以他几乎很少有业余时间来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因此,他非常希望能换一个好一些的环境,可以潜下心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研究和写作,特别是完成他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事有凑巧,恰好此时,大约是1931年的七八月,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老友郭绍虞来信请他去北平,担任燕京、清华两所大学的合聘教授;而此时,又因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他作为编译所的职工代表,与总经理王云五的矛盾日益尖锐,于是,他便辞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携家带口回到了他求学时代的北平。
关于他要“北上教书”的消息和他写《中国文学史》的宏大计划,在他将要离开上海前就在朋友间不胫而走。当时“左联”的外围报纸《文艺新闻》和其他一些报刊,曾多次报道“郑振铎赴燕大授课。并搜集中国文学史料”等有关他的消息。可见当时上海的文化界密切关注着他。
从1931年秋新的学年开始不久,到1935年春的这段时间里,在北平西郊的燕园和“水木清华”,人们常可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着一身旧西装、手里总是提着一个塞得鼓鼓的旧公文包的中年汉子,在两校间,迈着骆驼般的大步,往返奔波着。他就是学生们所景仰的“西谛先生”。
未名湖的湖光、塔影、石舫,未名湖的春花、秋月、夏荷、冬雪,都颇能使人增添文思。父亲在湖的一隅,茂林修竹掩映下的曲径通幽处,有了一所田园式的别墅——天河厂1号。这真是一个只有王维和陶渊明的诗中才有的佳境啊!终于,父亲在完成繁重的教课以外,有了一个他盼望已久的良好环境,来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了。
万事总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正当父亲备好材料,并请了一位助手,开始他的“中国文学史”的巨大工程时,日本在上海挑起了淞沪战事,商务印书馆遭到了惨重破坏,而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中世纪第三篇上册”的纸型,也被日寇炮火烧毁殆尽!听到噩耗,他无比愤怒,几乎想放弃他的计划。但是,在他的辞典里,是从没有“气馁”二字的,他是那种只要一确定目标,就一往无前,遇到任何艰难挫折都决不回头的一条硬汉。在冷静下来后,他对原计划作了一番调整,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写作工程。除了授课外,他不分昼夜地奋笔疾书,谢绝了一切应酬,连最爱去的几家旧书店,也不见了他的身影。一位书店老板陈先生以为他病了,特意从城里赶到燕园去看他,见他正埋头在故纸堆里。母亲向陈先生示意,陈先生才恍然大悟,于是未敢惊动他,便向母亲默默地告辞了。但几天后,北平的一些报纸就纷纷披露:“文学大师郑西谛在燕园闭门著书,预测不久将有弘篇巨著问世……”
父亲在写作方面堪称一把“快手”,这是朋友们所公认的。他曾跟一位老友讲过:“只要材料备好了,一天写五千字是不成问题的。”果然,他的工作效率是“神速”的,大概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洋洋80万字的皇皇巨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册)于1932年12月,由北平朴社出版了。也许是从小受了“绣像小说”的影响,他总是喜欢给他的著作加上些插图。《文学大纲》如此,这次他又在这部书里,精选了一百几十幅与中国文学有关的十分精美而珍贵的古代木刻画、名家绘画等作为插图,故而,他为这部“文学史”冠以了“插图本”三个字。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问世前后,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反响。1932年10月10日北平图书馆的《读书月刊》就发表了王以中推荐此书的文章,肯定此书是“中国文化界和史学界上很大的贡献”,并认为此书既是“历史的”又是“批评的”,读后不但对中国文学的源流变迁可以知道得比较详细,而且对于各家的文艺的研究也可得相当的门径。赵景深在《我与文学》一书中,也赞扬此书材料新颖广博,叙述美丽流畅,尤其在小说、戏曲等方面,论述了别人从未曾见过的作品。1935年的《人间世》杂志在学术界与读者界发起推荐“五十年来百部佳作”的评选活动,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如叶圣陶、夏丐尊、赵景深、陆侃如、冯沅君、章锡琛、王伯祥、徐调孚、周一鸿等人,都热情地推荐了此书。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在1933年3月的《书志学》杂志上介绍了此书,称赞作者对中国戏曲、小说“特别有研究”,并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著名学者王国维。长泽还认为日本汉学家写的《中国文学史》,与此书“不可同日而语,差得太远了”。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也惊动了鲁迅。他看到报上的“征订简章”后。便委托许广平到开明书店去预订此书。但当在《晨报》上读到作者为该书撰写的《例言》,在《小说月刊》上读到父亲写的《(三国演义)的演化》和《(水浒传)的演化》等几篇长文后,他便对该书产生了一些误解。如他在当年8月15日写给台静农的信中提及该书时,便有“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持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以及“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预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资料长编,非‘史也”等含有贬义的文字。然而在他读到了作者赠给他的这套书后,方知是自己误会了,于是在1932年2月给曹靖华的信中,他向曹靖华推荐的五种文学史著作中,便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足见鲁迅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一部书的好、坏、成、败,是要经受时间考验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问世迄今,已经历了70余个风风雨雨。这期间,由于连年战乱以及新中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它也经受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有些人贬得一文不值,以致它的重新再版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如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它还是先后由北京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相继重印。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印数已超过20万部。以一部学术专著能达此印数,充分说明了它在读者心目中所占的位置。
远在天国的父亲,您的成就是永远不会被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