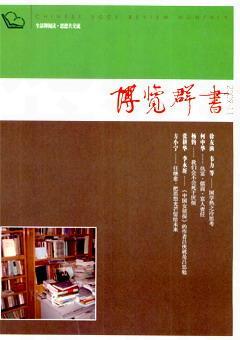屋上三尺有芳邻
陈书旦
《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是我的邻居马思猛的回忆之作,我是此书的第一个阅读者,同时也是它成书的见证者。马衡何许人也——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郭沫若语)、北大国学门煊赫一时“五马”之一、曾任故宫博物院19年院长和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并被故宫现任院长郑欣淼称为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方面均有所立的先贤人物。
这一串头衔说下来,不免气短。先贤德行高尚渺远,我辈只能耳闻而无法亲见,体会不够切近。那么就让我从住我屋上三尺的忘年交思猛先生谈起吧。
当年,我与思猛先生的交往缘于毫不起眼的鱼事。一日我要离京,不忍生灵涂炭,便托一小缸和数尾小鱼敲开先生家门。先生家中摆设简洁平常,四壁雪白,老伴出身农家质朴热情,而先生每日上楼下楼低调而和善,我猜想他们一定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果然。先生一口应承,数日后我回京发现,鱼儿们不但完好如初,似乎还有了比先前更自在的遨游兴致。于是我开始经常拜访,并向马先生请教养鱼技巧。先生闲来也到我家畅谈,忆古论今纵横睥睨却也怡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思猛先生谈到一些大是大非和利益得失时,给我留下令人吃惊的淡定和豁达,以及对名利宠辱的不扰于心,总觉得此人非常人也,但没人知道底细,先生自己也绝口不提。
谜底的揭开,是2004年春节后的一天。那日思猛先生激动地跑到楼下敲门,并告诉我,正在热播的《国宝》电视剧中刘文治饰演的故宫院长的原型,正是他的爷爷马衡。言语动情处掩饰不住的颤抖,让我体会到先生对爷爷深埋心底的感情。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位行事甚为低调平易近人的马先生出自名门,其爷叔父祖,包括母系各支,四代之内皆是有成就有故事之人。
此后,得益于我的毫不相关的身份,思猛先生渐渐打开记忆的闸门。家世、国事、兴亡事,那历史中无数尘封的故事鲜活起来,勾连起来,携带着百年中国史卷的沉郁和滂沱的气势,携带着至今百变未离三昧的滚滚红尘向我走来。我觉得先生的家世不必比作现代版的《红楼梦》,至少也不亚于另一部《家春秋》,就说先生您写吧,不写烂在肚里可惜了。先生只一笑,说:《红楼梦》和《家春秋》我是不爱看的,更不要说写。我想这就好比《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马先生是从大宅门里走出来的,大家族的故事正是他一辈子都要逃出去的罗网,他不愿意返回,自有其历史和人情的道理。往事前尘怕回首,哪怕只是记忆之旅。
2005年夏天,故宫举办纪念建院80周年暨马衡逝世50周年系列活动,并在景仁宫举办了马衡捐献展。思猛先生应邀参加并写了发言稿请当时在广播学院上学的侄女代读。我所知的是,所有这一切源自先辈的荣耀并没有扰乱先生一贯的生活步调和清净无为之心。思猛先生见我喜爱书法碑帖,一天,抱来一大卷影印版的马衡捐献册,上面虽只刊出了马衡捐献藏品的极少部分,却看得我目瞪口呆流连忘返。要知道,那从碑帖、青铜到甲骨的件件藏品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它们经过马衡先生的研究和注释尤显珍贵。对比思猛先生的家境,我不无调侃地对先生说:若是当年少捐个一件两件,您的处境就是另一副样子了吧?
先生淡然答道:“捐献全部私藏是爷爷的遗愿,去世后由父亲马彦祥主持完成,我至今非常赞成。因为对这些国家级文物的保存和研究,相信也只有像故宫这样的国家级博物馆才可以完成。而只有使这些珍贵的文物得到从善处理,爷爷才能含笑九泉。”话语朴素而感人至深。
那时,据说有位浙江的学者在写马衡传,书稿交给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社转请马先生提意见,这大约是个导火索。同时,两位五十年交情的友人万伯翱和乔宗淮也力劝先生撰写不亚于《家春秋》的家事。因为家人的回忆和学者的整理完全不同,前者留存血脉,后者注重史实,前者务求亲切,后者要求见地。那时的先生尚犹豫,不愿打扰先人的宁静,更不愿打乱自己的晚年生活;再者先生还有眼疾,一目几近失明,仅一目可视视力又弱,那时来我家聊天每每都要携带眼药。
事情在2005、2006年之交有了转机。2005年5月,在郑欣淼院长的倡议和推动下,故宫整理出版了《马衡捐献卷》,11月又出版《马衡日记》影印本,转年春天又出排印本的《马衡日记、诗抄》。日记中不绝如缕的祖孙亲情像是一种召唤,遂令先生拿起笔。我也得益于这头上三尺的近便,每日捧读那些狷介中正的蝇头小楷,想象着百年前先贤的生活。2003年10月,北大校长许智宏曾在北大图书馆举办的“五马”纪念展上的发言为那个时代的学人全貌提供了有力注脚。他说:“倘若你有意去翻阅中国知识分子家族的几千年变迁历史,就不难注意到,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曾经降生了一批这样的人物:他们是古代最末一批封建士大夫,也是中国第一批近代知识者,他们身上似乎跨越了两个时代,两重历史和两种文化,他们分割着历史的时间,同时又在空间上将其连结起来,承受着新旧转换的时代桥梁。无疑,这是一代具有特殊意义的知识者。我想马氏兄弟马裕藻、马衡、马鑑、马准和马廉,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一
马家何以能出5位北大教授,而且个个有所成就?一系列的疑问和探索的欲望让我决定以马衡先生为原点,从他身上去溯源这份辉煌了一个世纪并且至今在马家后代身上得到继承的沉着大气。我头脑中的问题依次展开:
1、马衡收藏如此宏富,背后的资金支持从何而来?
2、马衡没有傲人的教育资历,如此渊博的知识和见识又是从何而来?他又是如何踏上北大讲台和故宫任职的?
3、是怎样坚如磐石的意志促使他在做“海上寓公”、“叶氏董事”的十五年食俸无忧的奢华日子里毫不沉沦,并在36岁的盛年只身北上,来成就他一生的学术梦想?
4、马衡与吴昌硕是忘年交又同是西泠印社的早期会员,马衡出道时吴昌硕已经享有盛名,而马衡也是目前唯一可见到敢于对吴氏风格不以为然的学者。是狂妄还是学术的耿直?
5、易案风波之后,马衡在风口浪尖赴任故宫院长,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裁员减人,致使连素来对他敬佩有加的部下也不能理解。原因何在。气魄何来?
6、周作人称马衡“既衡且平”,从1934年故宫文物南迁到随护文物避祸西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大后方的马衡是什么状态?他的性格中是否只有“既衡且平”的一面?爱孙马思猛的名字从何而来?深意何在?
7、作为学者的马衡至死恪守君子不党,不二色的格言。“君子不党”是否意味着对政治时事的漠不关心?马衡的诗和诗中忧国忧民的情怀透露了怎样敏锐的全局观和史家敏感?
8、关键的抉择: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北平围城时日记中折射的心路历程。
9、二十年前的“易案”旧账如何曲直面目,借助政治,在新生的政权下轰轰烈烈续
演?以三反运动为背景的故宫大规模审查和隔离背后,矛头所指到底是谁?
10、在离开故宫的日子里,病魔缠身,马衡是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度,端定“勿以个人荣辱为影响”的态度,反而开始静心整理他收集了一辈子的汉石经,并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
2006年6月,思猛先生以飞快的速度完成一稿,经由友人方继孝引荐,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签约。此后直至2009年4月一版印成的3年间,思猛先生数易其稿,更有多种前所未见的资料机缘巧合地齐聚先生面前,冥冥中促进并激励着先生来完成并完整这本书,使《金石梦故宫情》在许多历史片段的解读中呈现自己独特的面貌。
先说2005年5月,方继孝的《旧墨记》首册出版,使诸多秘史文献得见天日。其中就记有他在潘家园偶得的一册马衡著《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封三还附马衡1950年亲笔附识,开宗明义此文为易案而作。这份材料的出现有如天意,尤为珍贵。由此,这篇1936年写就、当年以纪念张菊生(元济)七十寿辰为名刊出的论文,在14年后的1950年澄清了它最初的写作初衷——“此文(实际)为易案而作”。孙郁在序《旧墨记》中评价道:此文系为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翻案之文,写得百转千回,有浩然之气。那么,此文的刊出为何要隐曲其衷?答案就在马衡的附识之中:
……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平生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漩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
看来马衡并没有真的不问易案,只是迫于时势,“以学术论文的形式为易氏洗冤,实在难得”(方继孝语)。
既然已属十几年陈年旧案,马衡为何要在改朝换代后的1950年对其追加注解?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玄机?我在思猛先生的《金石梦故宫情》中看到了答案。
《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及《著者附识》,实为爷爷于1950年2月4日委托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先生,转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答吴瀛告马衡的自辩书。
另外思猛先生还援引《马衡日记》二则,是这样说的:
1949年,10月24日(星一)晴。霜降节。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因请冶秋转达董老,请拔冗延见,以便面谈,并希望以原书见示,俾可逐条答复。……
1949年,10月27日(星四)。晴。……昨冶秋电话以吴瀛上书,董老不愿于此时出以示人,因其足以刺激人之情绪,允俟将来见示。……
再来看另一版本的回忆:2005年,故宫出版了吴瀛的《故宫尘梦录》。此书原名《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书中,吴先生用二十万言陈述了种种对故宫人事的猜忌和不满,并公开将故宫人分为“政府官员系”和“北大系”,坦言若他真做故宫秘书长,“那些北大先生们又要同盟罢工亦未可知”。在这里,我要向吴瀛这份“君子的坦荡”鞠躬致意,没有他这种“小人物”记述的“小历史”,我们对历史全貌的把握怕要有所缺失。
要知道当年“易案”并列的三名被告:易培基、李宗侗、吴瀛,是以这样的关联呈现在故宫的“尘梦”里,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所提携重用的秘书长是自己的女婿,还是民国元老李石曾的侄子。名列秘书长之下但待遇相同的“简任秘书”吴瀛,和易培基是昔日两湖书院的同窗好友,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他是北洋政府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的亲外甥。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就难怪北大派的先生们对这些显宦亲属和易院长私友不服了。(转引自书鱼小知《关于故宫的话题》)
如果说截止到书写《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时,吴瀛还只是表达了对北大系和易培基继任者马衡的不满,那么在1950年,吴瀛为什么就能将他的不满和怨愤升级为一纸诉状,言辞凿凿地把马衡告到董必武和毛泽东那里去呢?想要继续探究的朋友只能去追问九泉下的吴瀛先生了。
且看1981年11月,吴祖光在《怀念父亲》一文中,针对此事的叙述: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一往情深,至死不渝……
真是打成一锅粥!我只能说有些魅影,比如争权夺利、沽名钓誉这些亘古不死的鬼魂精魄,随时像魔咒一样准备去吸附适合的躯体。人要想做到三不朽,单单“立德”一项就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二
随着《国宝》电视剧的热播以及后续诸多关于故宫热门话题记录节目的面世,许多名人的后代们纷纷走出来,为埋没了几十年的先辈争一份后世的荣耀,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困惑的是我们这些普通的观众,我本人就分别看过徐森玉版、李济版以及吴瀛版的国宝南迁记录,其中述说到人物时除这些主人公外,不见别人,仿佛那一万九千箱的国家重器只是由他们个人一力维护下来,才免遭日本荼毒。更有甚者,因为吴先生只参加了国宝南迁而因故缺席更为重要的国宝西迁,所以吴版对西迁干脆只字不提,他的后人在叙述中更是将这动用了故宫所有工作人员、学者以及警察、军队,运输和沿途百姓无私帮助的浩大的世纪迁移说成是吴某一人的力挽狂澜。呜呼!如果认真读一下马衡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9月3日,在北平广播电台发表的题为《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广播演讲,就能清晰体会到道德高下。
何谓学者?何谓狷介?何谓不朽?郭沫若《凡将斋金石丛稿》序言中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文物,即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他关心的不是那纷乱的人事,而是四川无处不在的硕鼠、白蚁,如何防鼠、防盗、防火、防蚁,以及在敌机轰炸之前拥有必要的灵感,使好不容易运到后方的文物免遭灭顶之灾。
1951年,亲临国庆两周年庆典的马衡在日记中难掩喜悦之情,他详细记录了观礼的全过程,并感慨万分道:“我国有如此强大之武力,国防不足忧矣。”一个世纪老人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继“三反运动祸起萧墙”一章之后,思猛先生将爷爷生前的最后一章命名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认为它清晰地反映了马衡一贯的“勿以个人荣辱所影响”的大度,以及在受到不公待遇时依旧不减的可叹的大家风范。
1952年6月,赋闲在家听候三反运动结论的马衡被通知去文整会上班,从此离开了他毕生珍视如目的故宫,“爷爷开始重新走进凡将斋,整理校点跋著《汉石经集存》,续写他那因接办故宫而中断的金石之梦”。此后,“小雅宝胡同四十八号冷清了许多,日记所记内容明显减少”。其实,如果从学术的角度看,1952年6月以后马衡日记的内容不是减少,而是更丰富,你很难想象一个七十多岁癌病缠身的老人能在他最后的三年里干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紧凑、务实、庄严的一份工作记录。这中间唯一缺少的,是类似于吴瀛《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中那样的满腹牢骚文字。
爷爷坚持记日记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爷爷得到了组织的关照,他在忍受疾病的痛苦中,仍然关注着人民共和国的成长;仍然搜寻着汉石经新的发现,每当有新的收获,竟如孩童一般的兴奋自语“殊可乐也!”
让思猛先生欣慰的是,爷爷这段最后的日子,是自己陪伴一起走完的。1955年3月25日,“我目视爷爷上车远去,这次他真的要远去了”。
我觉得《金石梦故宫情》一书难能可贵的,是它平实的语言,和不矫情、不哀怨、不偏不倚的历史态度,这和热极一时的很多书籍形成了鲜明对比。记得《金石梦故宫情》成书期间,曾经有多方人士辗转找来,试图启发思猛先生将祖父在三反运动中含冤一节多加渲染以飨读者,但都被思猛先生婉拒。思猛先生抱定的是跟先辈一样的先国家后个人的态度。他说:爷爷当年都没有一句怨言,他看到更多的是祖国的变化,民族的复兴,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现在,思猛先生家的白墙上终于挂上了故宫的青年一辈集体前往香山福田公墓拜祭马衡时所写的祭文。我楼上三尺的地方住着祖孙两代芳邻,我是如此幸运,感谢上天冥冥的安排。